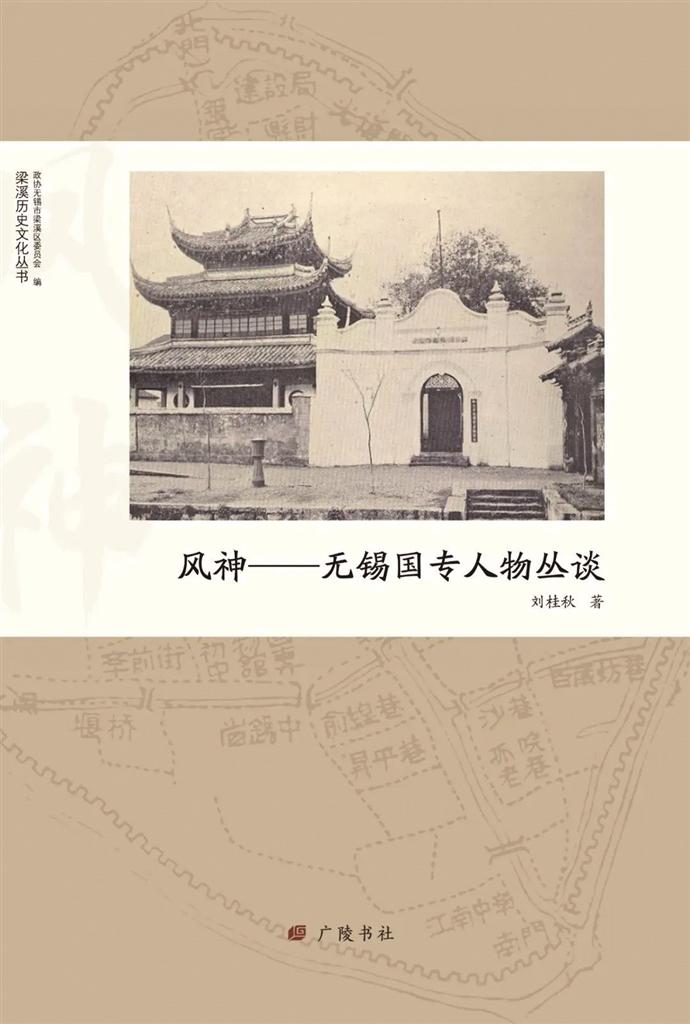□陈永跃
案头置放的这部《风神——无锡国专人物丛谈》专著,是江南大学刘桂秋教授无锡国专系列问题研究中的人物传记。书中所述是无锡国专1921年肇始直至1950年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期间颇为杰出的师生行谊与学术大端。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求学问道,以儒为教,今天我们目之为知识分子,于历史上则为士,且为“四民”之首。士作为引领国家民族前进的学术思想群体,一直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士子为首就是最好的力证。但从1900年到1911年间,清廷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官方与非官方的行动者共同推动的这些改革,对中国社会可谓影响深远,余音不绝。其中关键之一就是教育改革。在建立新式学堂制度时,改革者更是带来了思想上的扭转,即挟带着对传统士子的批判。清末的教育改革,可说是一种以传统反传统、以士大夫反士大夫的改革方式。据徐兆安先生考证,曾是清末状元的张謇在1900年提出一组概念,主张社会需要的是有生产力的“生利者”,而不是追求做官、榨取社会生产力的“分利者”。张謇进一步指责当时的传统读书人“自命为儒”,不屑于从事实业,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利益。在教育界与媒体的推动下,这种新观念逐渐成为主流。
1919年,迅猛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使得西风东渐,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向来以为“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的唐文治,在1920年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后不久,即迁居无锡,与施肇曾、陆勤之等人一道筹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唐文治出任馆长。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开列“躬行、孝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和挽救世风”十项规定,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检束身心、砥砺品行”。
有别于传统科举制通过考试服务于国家权力机构,现代教育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活动集中在学校内部,他们的目标亦转向未来,寄希望于通过人才培养服务于时代,导引社会风气。此一种精英意识是士子始终保持的本色。而透过无锡国专办学宗旨“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当时西学正炽之际逆风前进的胸襟与胆识。“一是注重和强调励学必先敦品,学和行要合一;二是强调读古籍原著;三是高度重视学生的写作实践;四是坚持自身特色顺应时代潮流;五是注重培养学生国学研修的自我学习、自我组织、自我实践的能力。”无锡国专上述五点既继承了传统中国书院精神的精髓,亦顺应现代教育制度的必须。“学生之成就,系于老师之学养。”三十年间办学规模不大的无锡国专,先后培养出两千余学生,造就了国内文史哲等领域的众多人才。逆流而上的士子们终于玉汝于成。
曾文正有言:“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信哉斯言,在刘桂秋教授的这部《风神——无锡国专人物丛谈》教师篇中,我们看到了“掌门人”唐文治“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逆流向上的特立独行士子人格;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一生劬学不辍、著述不止的宏大魄力与坚定毅力;史学大家童书业终生追求唯有学问的纯粹与坚韧。而在学生篇中,看到了“藏山付托不须辞”的蒋天枢;“浩荡巨川研红学”的冯其庸;“八百卷文章寿世”的钱仲联等,真可谓唯吴有材,于斯为盛。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无锡国专在特定历史时空逆势而上本身,恰恰是传统中国读书人“士子”在此时间空间中所做出的一种引导社会风俗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说:“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每一个时代应该有它一个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学术,干出理想所需要的事业,来领导此社会,此社会才有进步。”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虽然在成就了无锡国专辉煌一页后,又消解了它,但它在特定时间空间里培育出的人才,却自此散入国内大大小小的高校。秉承精神、崇尚信仰的国专士子们,置身于校园一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前赴后继,焚膏继晷,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传承这种人格力量与道德品质,传新薪而续旧火,击磐石而出新声,孜孜于杏林春暖,兢兢使弦歌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