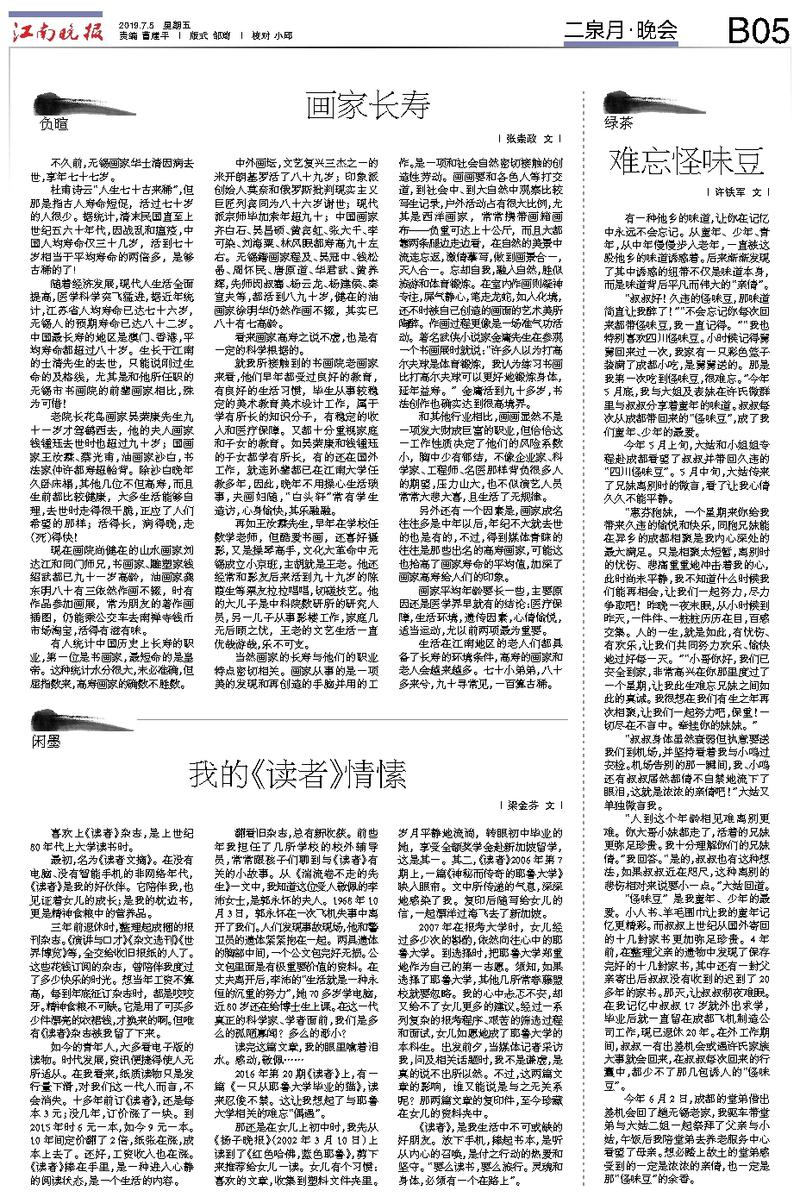| 梁金芬 文 |
喜欢上《读者》杂志,是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读书时。
最初,名为《读者文摘》。在没有电脑、没有智能手机的非网络年代,《读者》是我的好伙伴。它陪伴我,也见证着女儿的成长;是我的枕边书,更是精神食粮中的营养品。
三年前退休时,整理起成捆的报刊杂志。《演讲与口才》《杂文选刊》《世界博览》等,全交给收旧报纸的人了。这些花钱订阅的杂志,曾陪伴我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想当年工资不算高,每到年底征订杂志时,都是咬咬牙。精神食粮不可缺。它是用了可买多少件漂亮的衣裙钱,才换来的啊。但唯有《读者》杂志被我留了下来。
如今的青年人,大多看电子版的读物。时代发展,资讯便捷得使人无所适从。在我看来,纸质读物只是发行量下滑,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不会消失。十多年前订《读者》,还是每本3元;没几年,订价涨了一块。到2015年时6元一本,如今9元一本。10年间定价翻了2倍,纸张在涨,成本上去了。还好,工资收入也在涨。《读者》捧在手里,是一种进入心静的阅读状态,是一个生活的内容。
翻看旧杂志,总有新收获。前些年我担任了几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常跟孩子们聊到与《读者》有关的小故事。从《湍流卷不走的先生》一文中,我知道这位受人敬佩的李沛女士,是郭永怀的夫人。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离开了我们。人们发现事故现场,他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两具遗体的胸部中间,一个公文包完好无损。公文包里面是有极重要价值的资料。在丈夫离开后,李沛的“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在这一代真正的科学家、学者面前,我们是多么的孤陋寡闻?多么的渺小?
读完这篇文章,我的眼里噙着泪水。感动,敬佩……
2016年第20期《读者》上,有一篇《一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猫》,读来忍俊不禁。这让我想起了与耶鲁大学相关的难忘“偶遇”。
那还是在女儿上初中时,我先从《扬子晚报》(2002年3月10日)上读到了《红色哈佛,蓝色耶鲁》,剪下来推荐给女儿一读。女儿有个习惯:喜欢的文章,收集到塑料文件夹里。岁月平静地流淌,转眼初中毕业的她,享受全额奖学金赴新加坡留学,这是其一。其二,《读者》2006年第7期上,一篇《神秘而传奇的耶鲁大学》映入眼帘。文中所传递的气息,深深地感染了我。复印后随写给女儿的信,一起漂洋过海飞去了新加坡。
2007年在报考大学时,女儿经过多少次的斟酌,依然向往心中的耶鲁大学。到选择时,把耶鲁大学郑重地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须知,如果选择了耶鲁大学,其他几所常春藤盟校就要忽略。我的心中忐忑不安,却又给不了女儿更多的建议。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报考程序、艰苦的筛选过程和面试,女儿如愿地成了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出发前夕,当媒体记者采访我,问及相关话题时,我不是谦虚,是真的说不出所以然。不过,这两篇文章的影响,谁又能说是与之无关系呢?那两篇文章的复印件,至今珍藏在女儿的资料夹中。
《读者》,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朋友。放下手机,捧起书本,是听从内心的召唤,是付之行动的热爱和坚守。“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