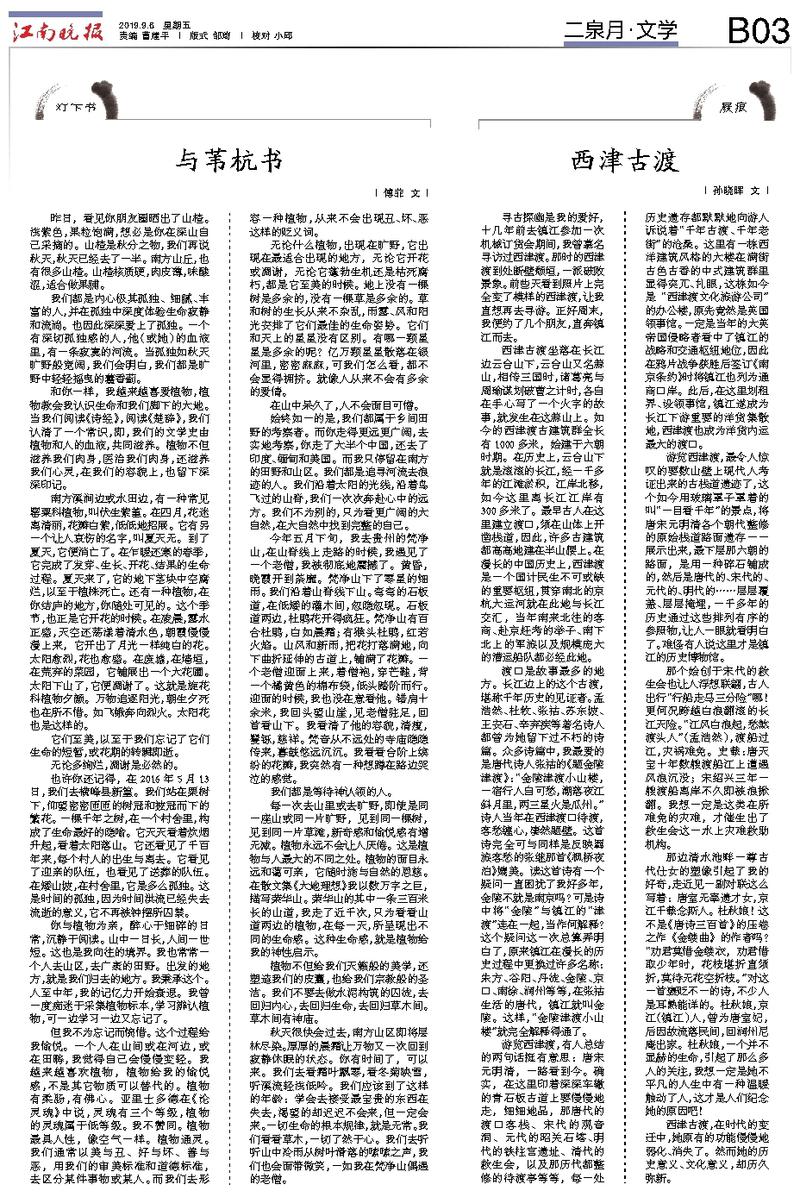| 傅菲 文 |
昨日,看见你朋友圈晒出了山楂。浅紫色,果粒饱满,想必是你在深山自己采摘的。山楂是秋分之物,我们再说秋天,秋天已经去了一半。南方山丘,也有很多山楂。山楂核质硬,肉皮薄,味酸涩,适合做果脯。
我们都是内心极其孤独、细腻、丰富的人,并在孤独中深度体验生命寂静和流淌。也因此深深爱上了孤独。一个有深切孤独感的人,他(或她)的血液里,有一条寂寞的河流。当孤独如秋天旷野般宽阔,我们会明白,我们都是旷野中轻轻摇曳的藿香蓟。
和你一样,我越来越喜爱植物,植物教会我认识生命和我们脚下的大地。当我们阅读《诗经》,阅读《楚辞》,我们认清了一个常识,即,我们的文学史由植物和人的血液,共同滋养。植物不但滋养我们肉身,医治我们肉身,还滋养我们心灵,在我们的容貌上,也留下深深印记。
南方溪涧边或水田边,有一种常见罂粟科植物,叫伏生紫堇。在四月,花迷离清丽,花瓣白紫,低低地招展。它有另一个让人哀伤的名字,叫夏天无。到了夏天,它便消亡了。在乍暖还寒的春季,它完成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生命过程。夏天来了,它的地下茎块中空腐烂,以至于植株死亡。还有一种植物,在你结庐的地方,你随处可见的。这个季节,也正是它开花的时候。在凌晨,露水正盛,天空还荡漾着清水色,朝霞慢慢漫上来,它开出了月光一样纯白的花。太阳愈烈,花也愈盛。在废墟,在墙垣,在荒弃的菜园,它铺展出一个大花圃。太阳下山了,它便凋谢了。这就是旋花科植物夕颜。万物追逐阳光,朝生夕死也在所不惜。如飞蛾奔向烈火。太阳花也是这样的。
它们至美,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或花期的转瞬即逝。
无论多绚烂,凋谢是必然的。
也许你还记得,在2016年5月13日,我们去横峰县新篁。我们站在栗树下,仰望密密匝匝的树冠和披冠而下的繁花。一棵千年之树,在一个村舍里,构成了生命最好的隐喻。它天天看着炊烟升起,看着太阳落山。它还看见了千百年来,每个村人的出生与离去。它看见了迎亲的队伍,也看见了送葬的队伍。在矮山坡,在村舍里,它是多么孤独。这是时间的孤独,因为时间洪流已经失去流逝的意义,它不再被钟摆所囚禁。
你与植物为亲,醉心于细碎的日常,沉静于阅读。山中一日长,人间一世短。这也是我向往的境界。我也常常一个人去山区,去广袤的田野。出发的地方,就是我们归去的地方。我秉承这个。人至中年,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我曾一度痴迷于采集植物标本,学习辨认植物,可一边学习一边又忘记了。
但我不为忘记而惋惜。这个过程给我愉悦。一个人在山间或在河边,或在田畴,我觉得自己会慢慢变轻。我越来越喜欢植物,植物给我的愉悦感,不是其它物质可以替代的。植物有柔肠,有佛心。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说,灵魂有三个等级,植物的灵魂属于低等级。我不赞同。植物最具人性,像空气一样。植物通灵。我们通常以美与丑、好与坏、善与恶,用我们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去区分某件事物或某人。而我们去形容一种植物,从来不会出现丑、坏、恶这样的贬义词。
无论什么植物,出现在旷野,它出现在最适合出现的地方,无论它开花或凋谢,无论它蓬勃生机还是枯死腐朽,都是它至美的时候。地上没有一棵树是多余的,没有一棵草是多余的。草和树的生长从来不杂乱,雨露、风和阳光安排了它们最佳的生命姿势。它们和天上的星星没有区别。有哪一颗星星是多余的呢?亿万颗星星散落在银河里,密密麻麻,可我们怎么看,都不会显得拥挤。就像人从来不会有多余的爱情。
在山中呆久了,人不会面目可憎。
始终如一的是,我们都属于乡间田野的考察者。而你走得更远更广阔,去实地考察,你走了大半个中国,还去了印度、缅甸和美国。而我只停留在南方的田野和山区。我们都是追寻河流去浪迹的人。我们沿着太阳的光线,沿着鸟飞过的山脊,我们一次次奔赴心中的远方。我们不为别的,只为看更广阔的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找到完整的自己。
今年五月下旬,我去贵州的梵净山,在山脊线上走路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老僧,我被彻底地震撼了。黄昏,晚霞开到荼靡。梵净山下了零星的细雨。我们沿着山脊线下山。弯弯的石板道,在低矮的灌木间,忽隐忽现。石板道两边,杜鹃花开得疯狂。梵净山有百合杜鹃,白如晨霜;有猴头杜鹃,红若火焰。山风和新雨,把花打落满地,向下曲折延伸的古道上,铺满了花瓣。一个老僧迎面上来,着僧袍,穿芒鞋,背一个橘黄色的棉布袋,低头踏阶而行。迎面的时候,我也没在意看他。错肩十余米,我回头望山崖,见老僧驻足,回首看山下。我看清了他的容貌,清瘦,矍铄,慈祥。梵音从不远处的寺庙隐隐传来,暮鼓悠远沉沉。我看看台阶上缤纷的花瓣,我突然有一种想蹲在路边哭泣的感觉。
我们都是等待神认领的人。
每一次去山里或去旷野,即使是同一座山或同一片旷野,见到同一棵树,见到同一片草滩,新奇感和愉悦感有增无减。植物永远不会让人厌倦。这是植物与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植物的面目永远和蔼可亲,它随时施与自然的恩慈。在散文集《大地理想》我以数万字之巨,描写荣华山。荣华山的其中一条三百米长的山道,我走了近千次,只为看看山道两边的植物,在每一天,所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感。这种生命感,就是植物给我的神性启示。
植物不但给我们天籁般的美学,还塑造我们的皮囊,也给我们宗教般的圣洁。我们不要去做水泥构筑的囚徒,去回归内心,去回归生命,去回归草木间。草木间有神庙。
秋天很快会过去,南方山区即将层林尽染。厚厚的晨霜让万物又一次回到寂静休眠的状态。你有时间了,可以来。我们去看霜叶飘零,看冬菊映雪,听溪流轻浅低吟。我们应该到了这样的年龄:学会去接受最宝贵的东西在失去,渴望的却迟迟不会来,但一定会来。一切生命的根本规律,就是无常。我们看看草木,一切了然于心。我们去听听山中冷雨从树叶滑落的嗦嗦之声,我们也会面带微笑,一如我在梵净山偶遇的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