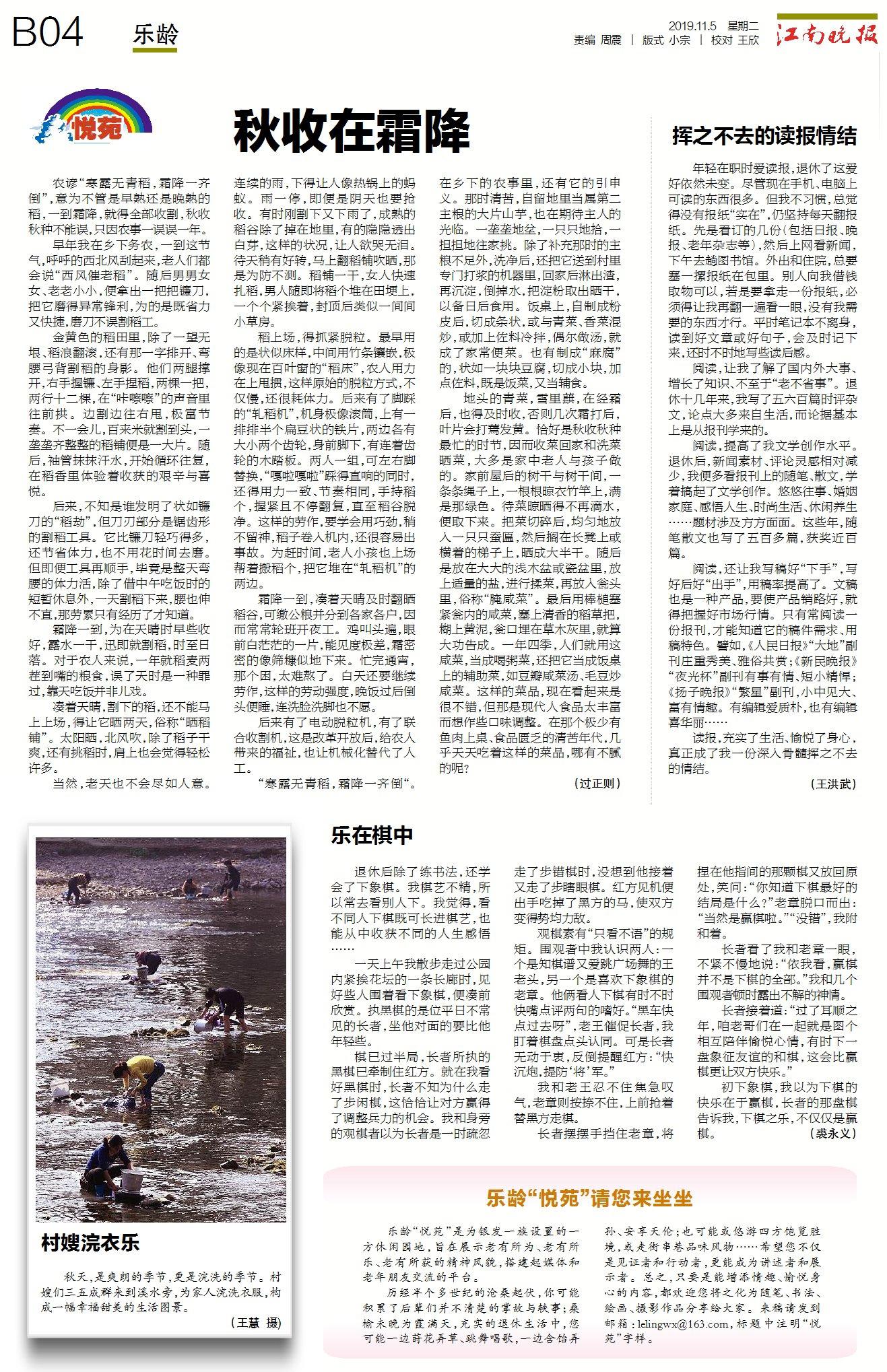农谚“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意为不管是早熟还是晚熟的稻,一到霜降,就得全部收割,秋收秋种不能误,只因农事一误误一年。
早年我在乡下务农,一到这节气,呼呼的西北风刮起来,老人们都会说“西风催老稻”。随后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便拿出一把把镰刀,把它磨得异常锋利,为的是既省力又快捷,磨刀不误割稻工。
金黄色的稻田里,除了一望无垠、稻浪翻滚,还有那一字排开、弯腰弓背割稻的身影。他们两腿撑开,右手握镰、左手捏稻,两棵一把,两行十二棵,在“咔嚓嚓”的声音里往前拱。边割边往右甩,极富节奏。不一会儿,百来米就割到头,一垄垄齐整整的稻铺便是一大片。随后,袖管抹抹汗水,开始循环往复,在稻香里体验着收获的艰辛与喜悦。
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状如镰刀的“稻劫”,但刀刃部分是锯齿形的割稻工具。它比镰刀轻巧得多,还节省体力,也不用花时间去磨。但即便工具再顺手,毕竟是整天弯腰的体力活,除了借中午吃饭时的短暂休息外,一天割稻下来,腰也伸不直,那劳累只有经历了才知道。
霜降一到,为在天晴时早些收好,露水一干,迅即就割稻,时至日落。对于农人来说,一年就稻麦两茬到嘴的粮食,误了天时是一种罪过,靠天吃饭并非儿戏。
凑着天晴,割下的稻,还不能马上上场,得让它晒两天,俗称“晒稻铺”。太阳晒,北风吹,除了稻子干爽,还有挑稻时,肩上也会觉得轻松许多。
当然,老天也不会尽如人意。连续的雨,下得让人像热锅上的蚂蚁。雨一停,即便是阴天也要抢收。有时刚割下又下雨了,成熟的稻谷除了掉在地里,有的隐隐透出白芽,这样的状况,让人欲哭无泪。待天稍有好转,马上翻稻铺吹晒,那是为防不测。稻铺一干,女人快速扎稻,男人随即将稻个堆在田埂上,一个个紧挨着,封顶后类似一间间小草房。
稻上场,得抓紧脱粒。最早用的是状似床样,中间用竹条镶嵌,极像现在百叶窗的“稻床”,农人用力在上甩掼,这样原始的脱粒方式,不仅慢,还很耗体力。后来有了脚踩的“轧稻机”,机身极像滚筒,上有一排排半个扁豆状的铁片,两边各有大小两个齿轮,身前脚下,有连着齿轮的木踏板。两人一组,可左右脚替换,“嘎啦嘎啦”踩得直响的同时,还得用力一致、节奏相同,手持稻个,握紧且不停翻复,直至稻谷脱净。这样的劳作,要学会用巧劲,稍不留神,稻子卷入机内,还很容易出事故。为赶时间,老人小孩也上场帮着搬稻个,把它堆在“轧稻机”的两边。
霜降一到,凑着天晴及时翻晒稻谷,可缴公粮并分到各家各户,因而常常轮班开夜工。鸡叫头遍,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能见度极差,霜密密的像筛糠似地下来。忙完通宵,那个困,太难熬了。白天还要继续劳作,这样的劳动强度,晚饭过后倒头便睡,连洗脸洗脚也不愿。
后来有了电动脱粒机,有了联合收割机,这是改革开放后,给农人带来的福祉,也让机械化替代了人工。
“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在乡下的农事里,还有它的引申义。那时清苦,自留地里当属第二主粮的大片山芋,也在期待主人的光临。一垄垄地坌,一只只地拾,一担担地往家挑。除了补充那时的主粮不足外,洗净后,还把它送到村里专门打浆的机器里,回家后淋出渣,再沉淀,倒掉水,把淀粉取出晒干,以备日后食用。饭桌上,自制成粉皮后,切成条状,或与青菜、香菜混炒,或加上佐料冷拌,偶尔做汤,就成了家常便菜。也有制成“麻腐”的,状如一块块豆腐,切成小块,加点佐料,既是饭菜,又当辅食。
地头的青菜,雪里蕻,在经霜后,也得及时收,否则几次霜打后,叶片会打蔫发黄。恰好是秋收秋种最忙的时节,因而收菜回家和洗菜晒菜,大多是家中老人与孩子做的。家前屋后的树干与树干间,一条条绳子上,一根根晾衣竹竿上,满是那绿色。待菜晾晒得不再滴水,便取下来。把菜切碎后,均匀地放入一只只蚕匾,然后搁在长凳上或横着的梯子上,晒成大半干。随后是放在大大的浅木盆或瓷盆里,放上适量的盐,进行揉菜,再放入瓮头里,俗称“腌咸菜”。最后用棒槌塞紧瓮内的咸菜,塞上清香的稻草把,糊上黄泥,瓮口埋在草木灰里,就算大功告成。一年四季,人们就用这咸菜,当成喝粥菜,还把它当成饭桌上的辅助菜,如豆瓣咸菜汤、毛豆炒咸菜。这样的菜品,现在看起来是很不错,但那是现代人食品太丰富而想作些口味调整。在那个极少有鱼肉上桌、食品匮乏的清苦年代,几乎天天吃着这样的菜品,哪有不腻的呢?
(过正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