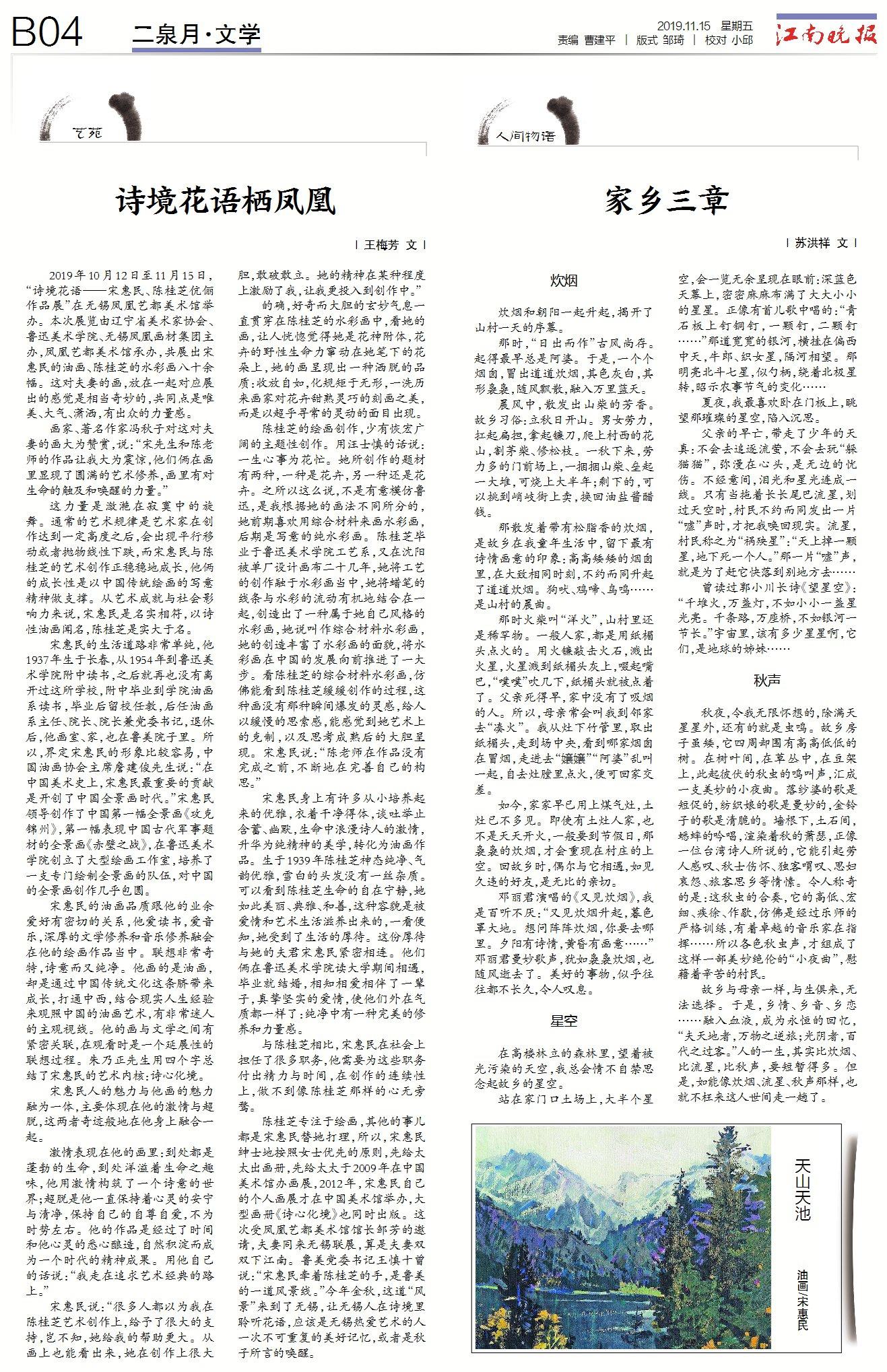| 苏洪祥 文 |
炊烟
炊烟和朝阳一起升起,揭开了山村一天的序幕。
那时,“日出而作”古风尚存。起得最早总是阿婆。于是,一个个烟囱,冒出道道炊烟,其色灰白,其形袅袅,随风飘散,融入万里蓝天。
晨风中,散发出山柴的芳香。故乡习俗:立秋日开山。男女劳力,扛起扁担,拿起镰刀,爬上村西的花山,割茅柴、修松枝。一秋下来,劳力多的门前场上,一捆捆山柴、垒起一大堆,可烧上大半年;剩下的,可以挑到峭岐街上卖,换回油盐酱醋钱。
那散发着带有松脂香的炊烟,是故乡在我童年生活中,留下最有诗情画意的印象:高高矮矮的烟囱里,在大致相同时刻,不约而同升起了道道炊烟。狗吠、鸡啼、鸟鸣……是山村的晨曲。
那时火柴叫“洋火”,山村里还是稀罕物。一般人家,都是用纸楣头点火的。用火镰敲击火石,溅出火星,火星溅到纸楣头灰上,啜起嘴巴,“噗噗”吹几下,纸楣头就被点着了。父亲死得早,家中没有了吸烟的人。所以,母亲常会叫我到邻家去“凑火”。我从灶下竹管里,取出纸楣头,走到场中央,看到哪家烟囱在冒烟,走进去“嬢嬢”“阿婆”乱叫一起,自去灶膛里点火,便可回家交差。
如今,家家早已用上煤气灶,土灶已不多见。即使有土灶人家,也不是天天开火,一般要到节假日,那袅袅的炊烟,才会重现在村庄的上空。回故乡时,偶尔与它相遇,如见久违的好友,是无比的亲切。
邓丽君演唱的《又见炊烟》,我是百听不厌:“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邓丽君曼妙歌声,犹如袅袅炊烟,也随风逝去了。美好的事物,似乎往往都不长久,令人叹息。
星空
在高楼林立的森林里,望着被光污染的天空,我总会情不自禁思念起故乡的星空。
站在家门口土场上,大半个星空,会一览无余呈现在眼前:深蓝色天幕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正像有首儿歌中唱的:“青石板上钉铜钉,一颗钉,二颗钉……”那道宽宽的银河,横挂在偏西中天,牛郎、织女星,隔河相望。那明亮北斗七星,似勺柄,绕着北极星转,昭示农事节气的变化……
夏夜,我最喜欢卧在门板上,眺望那璀璨的星空,陷入沉思。
父亲的早亡,带走了少年的天真:不会去追逐流萤,不会去玩“躲猫猫”,弥漫在心头,是无边的忧伤。不经意间,泪光和星光连成一线。只有当拖着长长尾巴流星,划过天空时,村民不约而同发出一片“嘘”声时,才把我唤回现实。流星,村民称之为“祸殃星”:“天上掉一颗星,地下死一个人。”那一片“嘘”声,就是为了赶它快落到别地方去……
曾读过郭小川长诗《望星空》:“千堆火,万盏灯,不如小小一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宇宙里,该有多少星星啊,它们,是地球的姊妹……
秋声
秋夜,令我无限怀想的,除满天星星外,还有的就是虫鸣。故乡房子虽矮,它四周却围有高高低低的树。在树叶间,在草丛中,在豆架上,此起彼伏的秋虫的鸣叫声,汇成一支美妙的小夜曲。落纱婆的歌是短促的,纺织娘的歌是曼妙的,金铃子的歌是清脆的。墙根下,土石间,蟋蟀的吟唱,渲染着秋的萧瑟,正像一位台湾诗人所说的,它能引起劳人感叹、秋士伤怀、独客喟叹、思妇哀怨、旅客思乡等情愫。令人称奇的是:这秋虫的合奏,它的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是经过乐师的严格训练,有着卓越的音乐家在指挥……所以各色秋虫声,才组成了这样一部美妙绝伦的“小夜曲”,慰藉着辛苦的村民。
故乡与母亲一样,与生俱来,无法选择。于是,乡情、乡音、乡恋……融入血液,成为永恒的回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人的一生,其实比炊烟、比流星,比秋声,要短暂得多。但是,如能像炊烟、流星、秋声那样,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