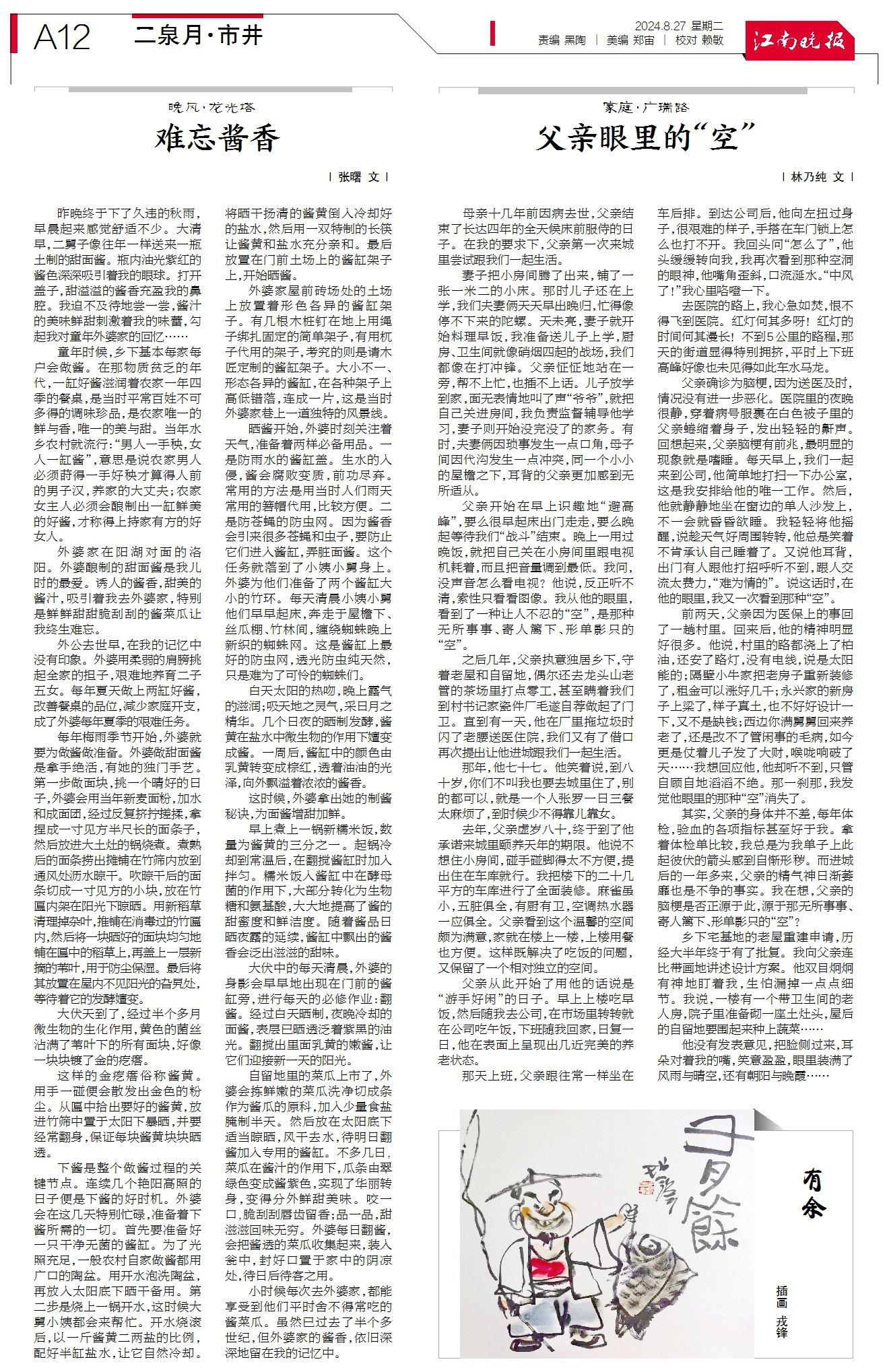| 张曙 文 |
昨晚终于下了久违的秋雨,早晨起来感觉舒适不少。大清早,二舅子像往年一样送来一瓶土制的甜面酱。瓶内油光紫红的酱色深深吸引着我的眼球。打开盖子,甜溢溢的酱香充盈我的鼻腔。我迫不及待地尝一尝,酱汁的美味鲜甜刺激着我的味蕾,勾起我对童年外婆家的回忆……
童年时候,乡下基本每家每户会做酱。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一缸好酱滋润着农家一年四季的餐桌,是当时平常百姓不可多得的调味珍品,是农家唯一的鲜与香,唯一的美与甜。当年水乡农村就流行:“男人一手秧,女人一缸酱”,意思是说农家男人必须莳得一手好秧才算得人前的男子汉,养家的大丈夫;农家女主人必须会酿制出一缸鲜美的好酱,才称得上持家有方的好女人。
外婆家在阳湖对面的洛阳。外婆酿制的甜面酱是我儿时的最爱。诱人的酱香,甜美的酱汁,吸引着我去外婆家,特别是鲜鲜甜甜脆刮刮的酱菜瓜让我终生难忘。
外公去世早,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印象。外婆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全家的担子,艰难地养育二子五女。每年夏天做上两缸好酱,改善餐桌的品位,减少家庭开支,成了外婆每年夏季的艰难任务。
每年梅雨季节开始,外婆就要为做酱做准备。外婆做甜面酱是拿手绝活,有她的独门手艺。第一步做面块,挑一个晴好的日子,外婆会用当年新麦面粉,加水和成面团,经过反复挤拧搓揉,拿捏成一寸见方半尺长的面条子,然后放进大土灶的锅烧煮。煮熟后的面条捞出摊铺在竹筛内放到通风处沥水晾干。吹晾干后的面条切成一寸见方的小块,放在竹匾内架在阳光下晾晒。用新稻草清理掉杂叶,推铺在消毒过的竹匾内,然后将一块晒好的面块均匀地铺在匾中的稻草上,再盖上一层新摘的苇叶,用于防尘保湿。最后将其放置在屋内不见阳光的旮旯处,等待着它的发酵嬗变。
大伏天到了,经过半个多月微生物的生化作用,黄色的菌丝沾满了苇叶下的所有面块,好像一块块镀了金的疙瘩。
这样的金疙瘩俗称酱黄。用手一碰便会散发出金色的粉尘。从匾中拾出要好的酱黄,放进竹筛中置于太阳下暴晒,并要经常翻身,保证每块酱黄块块晒透。
下酱是整个做酱过程的关键节点。连续几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便是下酱的好时机。外婆会在这几天特别忙碌,准备着下酱所需的一切。首先要准备好一只干净无菌的酱缸。为了光照充足,一般农村自家做酱都用广口的陶盆。用开水泡洗陶盆,再放入太阳底下晒干备用。第二步是烧上一锅开水,这时候大舅小姨都会来帮忙。开水烧滚后,以一斤酱黄二两盐的比例,配好半缸盐水,让它自然冷却。将晒干扬清的酱黄倒入冷却好的盐水,然后用一双特制的长筷让酱黄和盐水充分亲和。最后放置在门前土场上的酱缸架子上,开始晒酱。
外婆家屋前砖场处的土场上放置着形色各异的酱缸架子。有几根木桩钉在地上用绳子绑扎固定的简单架子,有用杌子代用的架子,考究的则是请木匠定制的酱缸架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酱缸,在各种架子上高低错落,连成一片,这是当时外婆家巷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晒酱开始,外婆时刻关注着天气,准备着两样必备用品。一是防雨水的酱缸盖。生水的入侵,酱会腐败变质,前功尽弃。常用的方法是用当时人们雨天常用的箬帽代用,比较方便。二是防苍蝇的防虫网。因为酱香会引来很多苍蝇和虫子,要防止它们进入酱缸,弄脏面酱。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小姨小舅身上。外婆为他们准备了两个酱缸大小的竹环。每天清晨小姨小舅他们早早起床,奔走于屋檐下、丝瓜棚、竹林间,缠绕蜘蛛晚上新织的蜘蛛网。这是酱缸上最好的防虫网,透光防虫纯天然,只是难为了可怜的蜘蛛们。
白天太阳的热吻,晚上露气的滋润;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几个日夜的晒制发酵,酱黄在盐水中微生物的作用下嬗变成酱。一周后,酱缸中的颜色由乳黄转变成棕红,透着油油的光泽,向外飘溢着浓浓的酱香。
这时候,外婆拿出她的制酱秘诀,为面酱增甜加鲜。
早上煮上一锅新糯米饭,数量为酱黄的三分之一。起锅冷却到常温后,在翻搅酱缸时加入拌匀。糯米饭入酱缸中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大部分转化为生物糖和氨基酸,大大地提高了酱的甜蜜度和鲜洁度。随着酱品日晒夜露的延续,酱缸中飘出的酱香会泛出滋滋的甜味。
大伏中的每天清晨,外婆的身影会早早地出现在门前的酱缸旁,进行每天的必修作业:翻酱。经过白天晒制,夜晚冷却的面酱,表层已晒透泛着紫黑的油光。翻搅出里面乳黄的嫩酱,让它们迎接新一天的阳光。
自留地里的菜瓜上市了,外婆会拣鲜嫩的菜瓜洗净切成条作为酱瓜的原科,加入少量食盐腌制半天。然后放在太阳底下适当晾晒,风干去水,待明日翻酱加入专用的酱缸。不多几日,菜瓜在酱汁的作用下,瓜条由翠绿色变成酱紫色,实现了华丽转身,变得分外鲜甜美味。咬一口,脆刮刮唇齿留香;品一品,甜滋滋回味无穷。外婆每日翻酱,会把酱透的菜瓜收集起来,装入瓮中,封好口置于家中的阴凉处,待日后待客之用。
小时候每次去外婆家,都能享受到他们平时舍不得常吃的酱菜瓜。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外婆家的酱香,依旧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