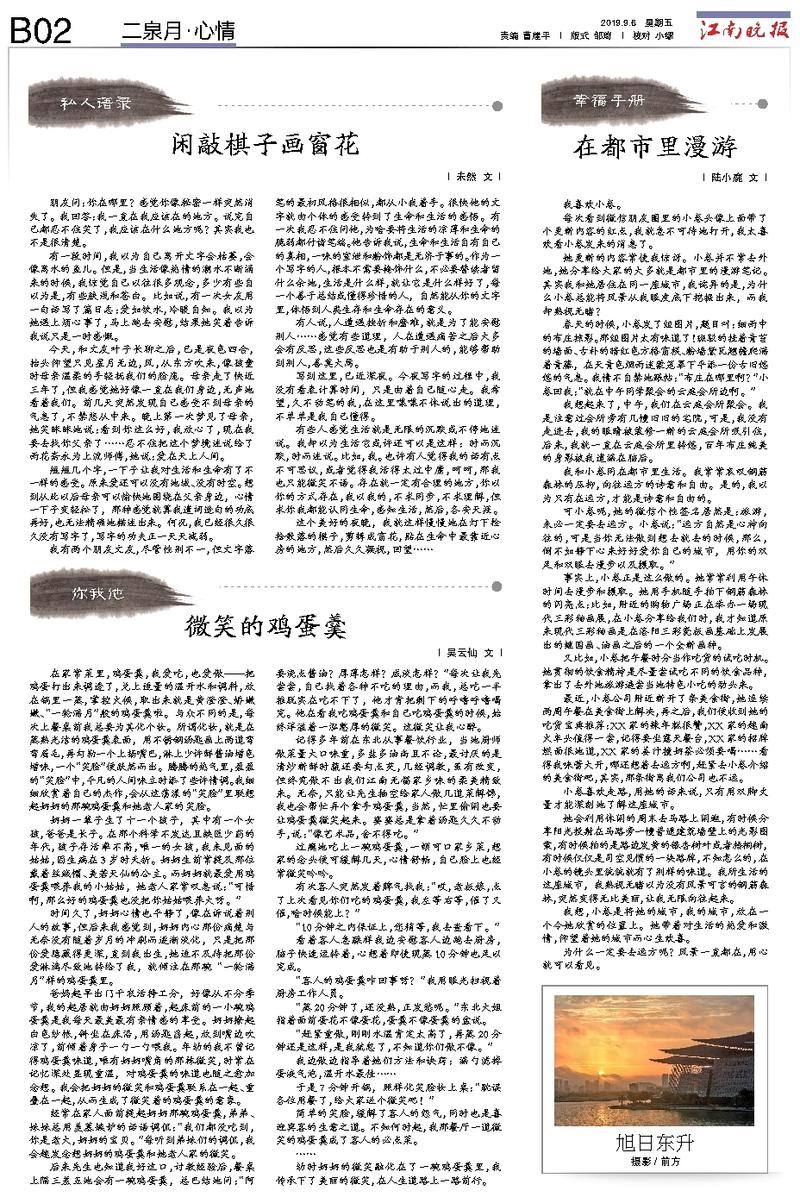| 吴云仙 文 |
在家常菜里,鸡蛋羹,我爱吃,也爱做——把鸡蛋打出来调透了,兑上适量的温开水和调料,放在锅里一蒸,掌控火候,取出来就是黄澄澄、娇嫩嫩、“一轮满月”般的鸡蛋羹啦。与众不同的是,每次上餐桌前我总要为其化个妆。所谓化妆,就是在蒸熟光洁的鸡蛋羹表面,用不锈钢汤匙画上两道弯弯眉毛,再勾勒一个上扬嘴巴,淋上少许鲜酱油增色增味,一个“笑脸”便跃然而出。腾腾的热气里,盈盈的“笑脸”中,平凡的人间味立时添了些许情调。我细细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会从这荡漾的“笑脸”里联想起奶奶的那碗鸡蛋羹和她老人家的笑脸。
奶奶一辈子生了十一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女孩,爸爸是长子。在那个科学不发达且缺医少药的年代,孩子存活率不高,唯一的女孩,我未见面的姑姑,因生病在3岁时夭折。奶奶生前常提及那位戴着丝绒帽、美若天仙的公主。而奶奶就最爱用鸡蛋羹喂养我的小姑姑,她老人家常叹息说:“可惜啊,那么好的鸡蛋羹也没把你姑姑喂养大呀。”
时间久了,奶奶心情也平静了,像在诉说着别人的故事,但后来我感觉到,奶奶内心那份痛楚与无奈没有随着岁月的冲刷而逐渐淡化,只是把那份爱隐藏得更深,直到我出生,她迫不及待把那份爱淋漓尽致地转给了我,就倾注在那碗“一轮满月”样的鸡蛋羹里。
爸妈起早出门干农活挣工分,好像从不分季节,我的起居就由奶奶照顾着,起床前的一小碗鸡蛋羹是我每天最美最有亲情感的享受。奶奶撩起白色纱帐,斜坐在床沿,用汤匙舀起,放到嘴边吹凉了,前倾着身子一勺一勺喂我。年幼的我不曾记得鸡蛋羹味道,唯有奶奶嘴角的那抹微笑,时常在记忆深处显现重温,对鸡蛋羹的味道也随之愈加念想。我会把奶奶的微笑和鸡蛋羹联系在一起、重叠在一起,从而生成了微笑着的鸡蛋羹的意象。
经常在家人面前提起奶奶那碗鸡蛋羹,弟弟、妹妹总用羡慕嫉妒的话语调侃:“我们都没吃到,你是老大,奶奶的宝贝。”每听到弟妹们的调侃,我会越发念想奶奶的鸡蛋羹和她老人家的微笑。
后来先生也知道我好这口,讨教经验后,餐桌上隔三差五地会有一碗鸡蛋羹,总巴结地问:“阿要浇点酱油?厚薄怎样?咸淡怎样?”每次让我先尝尝,自己找着各种不吃的理由,而我,总吃一半推脱实在吃不下了,他才肯把剩下的呼噜呼噜喝完。他在看我吃鸡蛋羹和自己吃鸡蛋羹的时候,始终洋溢着一泓憨厚的微笑。这微笑让我心醉。
记得多年前在东北从事餐饮行业,当地厨师做菜量大口味重,多盐多油尚且不论,最讨厌的是清炒新鲜时蔬还要勾点芡,几经调教,虽有改变,但终究做不出我们江南无锡家乡味的柔美精致来。无奈,只能让先生抽空给家人做几道菜解馋,我也会帮忙弄个拿手鸡蛋羹,当然,忙里偷闲也要让鸡蛋羹微笑起来。婆婆总是拿着汤匙久久不动手,说:“像艺术品,舍不得吃。”
过瘾地吃上一碗鸡蛋羹,一顿可口家乡菜,想家的念头便可缓解几天,心情舒畅,自己脸上也经常微笑吟吟。
有次客人突然发着脾气找我:“哎,老板娘,点了上次看见你们吃的鸡蛋羹,我左等右等,催了又催,啥时候能上?”
“10分钟之内保证上,您稍等,我去查看下。”
看着客人急躁样我边安慰客人边跑去厨房,脑子快速运转着,心想着即使现蒸10分钟也足以完成。
“客人的鸡蛋羹咋回事呀?”我用眼光扫视着厨房工作人员。
“蒸20分钟了,还没熟,正发愁呢。”东北大姐指着面前蛋花不像蛋花,蛋羹不像蛋羹的盆说。
“赶紧重做,刚刚水温肯定太高了,再蒸20分钟还是这样,是我疏忽了,不知道你们做不像。”
我边做边指导着她们方法和诀窍:漏勺滤掉蛋液气泡,温开水最佳……
于是7分钟开锅,照样化笑脸妆上桌:“耽误各位用餐了,给大家送个微笑吧!”
简单的笑脸,缓解了客人的怨气,同时也是喜迎宾客的生意之道。不知何时起,我那餐厅一道微笑的鸡蛋羹成了客人的必点菜。
……
幼时奶奶的微笑融化在了一碗鸡蛋羹里,我传承下了美丽的微笑,在人生道路上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