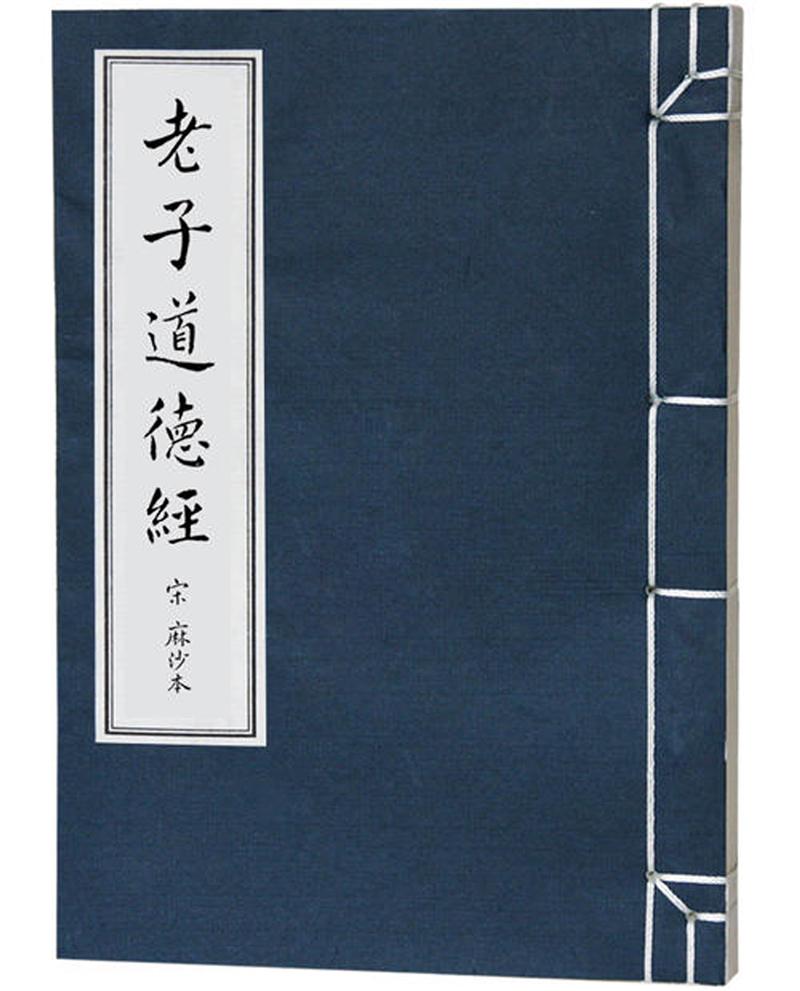| 肖向东 文 |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吴文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作为区域文化,它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比肩而立,和谐共生,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一步步从历史中走出,不仅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而且培育出了独立的文化精神,打造出独异的文化特色,成为中华文化系统的一道亮丽风景。
吴文化“开放”与“包孕” 的哲学基础——“和”
三
文化创新,是一种文化葆有其文化青春的重要要素,但文化创新不是凭空臆造的,创新的标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原生新颖性,二是社会历史性,三是开放包容性。三个方面都离不开文化哲学的支撑。或者说,作为主观意识层面的东西,创新意识及其致思方向与人的哲学思想有着十分重要而密切的精神联系。
吴文化的创新意识,从哲学形态上审视,明显具有东方哲学性征。
其一、就其“原生新颖性”看,老子的“无”“有”之论与“不争”“贵柔”学说,对于吴文化的形成与吴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理论铺垫作用。吴文化的生成相对于先其存在的中原文化等先进文化,其初始阶段是为老子所谓之“无”,“无”在老子思想里是天地初始状态,表现在文化上,则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起始状态。“有”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源,创新之基础。没有“有”,即一种新的文化承传与承转的基础,任何新形态文化的出现都无从谈起。历史上吴文化的不断自新,哲学上,即是在这样的“玄之又玄”的哲学演变与奥妙中,从一种形态走向另一种形态。“不争”与“贵柔”,反映的是吴文化的另一哲学特性。老子的“不争”,本指向“功名”“利禄”。“贵柔”,是“守雌”“崇柔”。但吴文化的“不争”却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转化为文化的“超然”与对社会“和平”的追求。吴人的“贵柔”,亦在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基础上养成一种厚德载物、外柔内刚、崇文重教的文化性格与诗性智慧。当吴越之争的历史烟云淡去,三国时代的呐喊厮杀消退,吴地与整个江南便长期处于远离战乱的社会稳定发展时期,正如老子所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社会经济长期休养生息与和睦稳定发展,使得“长三角”与江南成为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与商业崛起的领先之地,经济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交互作用,也以“新颖”的文化模式催生了吴文化新的生成机制与文化生态。
其二、就其“社会历史性”看,儒家“尚德”“尚贤”以及“和文化”的哲学思想,对于吴地形成聚贤崇文、厚德载物、里仁为美、和谐和合的社会风尚,无疑起到了文化导引的作用。因为“尚德”,礼义之风得以在吴中普及,里仁之美得以在吴境形成,和谐和合得以在吴地实现,从而创造了“和济天下”的吴地文明。因为“尚贤”,吴地才能广纳和聚集各方精英与社会贤才,形成自身的人才高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创出新的业绩。
其三、就其“开放包容性”而论,历史上吴越之争后形成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也由此奠定了太湖文化“包孕吴越”和承接“八面来风”的文化气度。之后,历经三国时期吴国的独立发展、东晋“永嘉之乱”三次移民带来的北方文明的注入、宋室南迁形成的南北文化融合、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繁盛发展以及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吹拂、改革开放以来濒临东海率先接纳现代西方先进科技的特殊条件,皆使吴文化得风气之先,与“长三角”经济体一起,以超前的开放性、强大的包容性,始终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列,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
当前,在中国三大都市圈,由华东15城构成的“长三角文化经济圈”可谓最具个性与优势,15城中,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嘉兴等10城均属吴文化区域。从历史上的纷争裂变到和平整合,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到现代工商文明,从封闭的农耕文化到开放的科技文化,标志着吴文化以创新方式和变革精神在现代社会完成了一次“涅槃式”革命与转型,吴文化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更高形式,然而其文化个性和哲学精神却是永恒而不变的!
吴文化“生成”与“创新”的重要元素——“水”
一
说起吴文化,一般意义上,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泰伯奔吴,饭稻羹鱼,小桥流水,吴侬软语。然而先吴古国,酋邦之地,只能代表它的过去;江南古陆,稻作之源,仅表其地域特点。锡铜采掘,陶瓷工艺,不过指其独特的物产。小桥流水,稻桑渔猎,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吴侬软语,里仁为美,指向的是一种民情与民性养成。上述文化特点,的确是吴文化的显性标识,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和他者文化的特质性东西,然而从文化本源性征说,解读一种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文化系统,实应从文化的内面因素与凝聚其灵魂的文化因子去探寻,由此,我们想到了吴地最为丰富的一种物质——“水”!
地域上,吴文化的历史形成与长江文化密切相关。长江文化因其巨大的流程派生了上游巴蜀文化、中游楚文化和下游吴越文化三大支系。地处上游的巴蜀文化自不缺水,但以“山”凸显其特征;楚文化兼有“山之魂”与“水之灵”,然其内陆型特点决定了其文化视野的狭隘,加之“重巫祈鬼”,培养了其崇尚“浪漫”而忽略实际的民性。吴文化也以“水”为标识,源源而来的长江水,浩渺的太湖水,沟通南北的运河水以及吴地纵横交叉的水道河床,构成了吴文化生成和赖以生存的水乡泽国。与水结缘,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文化,以捕鱼为生的渔文化,临水而居的住居文化,以船为马的行为文化,皆为吴地注入了江南水乡特性,而长期与水相处并借水而兴的吴人,由此亦培养了“水”的性格与“至柔”的文化意识。
水是世界最富有活力的一种物质,其生命特性一如其生命形态,延绵不断又滋润渗透,柔和韧性又刚毅有力,看似“无形”,实则“有形”,看似无变,而又常变。此得益于水之特性和水的因缘,即:随遇而变,因物赋形。故老子曰:“上善若水”,民间所谓“上善若水任方圆”,讲的亦是这个道理,正因为这一道理,使得吴文化有了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情而变的内生机制,同时也铸就了吴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变革的创新意识,而地理形貌之因素,于吴文化创新养成上,更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长江上游,地势因西高东低,水奔涌不息,难以常蓄。至中下游冲积平原,则水势缓冲,漶漫纵横,水形任意,变幻无穷,尤其当滚滚长江汇入浩瀚大海,又极显水之无限张力。“水”的启示,在创新意识上,无疑给予吴人重要灵感。社会变革、生活创造、生产力发展以及科技革命等,皆让吴人以“水”为媒,从中悟出了大道理、大思想,进而产生了大变革、大举措、大动力。常动不息,因情而变,创新吸纳,百川归海,和而不同,合而为一,诸种条件的变化与力量的叠加,促成了事物与万象的裂变,这大概就是吴地以及“长三角”地区得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发展龙头之地的重要主因。
吴文化“演绎”与“发展”的内生机制——“变”
二
水看似无形而变化无穷,外形柔弱而柔韧有力,吴地因多水而养成吴人“柔性”性格,然“柔”并非“软”与“弱”。“柔”能屈能伸,可张可弛,富有韧性与张力,其内在的品质在于“变”。《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纵的历史时间与横向的地理文化互动看,泰伯奔吴创建先吴古国,是吴文化接受中原文化开启吴地文明的肇始,此乃最初之变。楚人伍子胥入吴,范蠡、文种等楚地才学在吴越大地的活动,带来了吴、越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亦表明吴文化在其历史形成中,突破了一般文化“封闭”“单向”的路向与思维,而独以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拿来的”姿态,对他者文化因子采取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与此同时,以吴越之争而形成的异质文化的交融以及相互融合、整合以及以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质加以消化利用,吐故纳新,对于形成“新形态的吴文化”起了重要的催生作用。至于其后汉代至东晋“永嘉之乱”三次移民带来的北方文明的再度注入,宋室南迁形成的南北文化的融合,显然又为明清时代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及至近代当西方“海洋文明”向东方渗透之时,濒临东海特殊地理位置,又使吴文化得风气之先,率先承受与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这种来自纵、横两个文化向度的多重文化因子的作用,皆形成了吴文化不可夺的文化优势,使之从生成、发展到成熟,都在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文化机制中以不断接纳与创新的方式运演变化,在不断演变中积淀自身的优质因素,在扩大优质文化因素的张力中发展自己,进而在不断“创造”中将吴文化引向新的发展领域。
由此可见,“变”是吴文化绵延演绎、创新发展的内生机制。历史上越灭吴后,越文化一度覆盖了吴文化,以致21世纪初在无锡鸿山发掘的古墓文物几乎全是“越文化”,然吴文化的土壤与根系、空气与水系没有变,勾吴古国的血脉精神,吴地子民的勤劳智慧没有变,因此,当越文化的异质因子突入进来,吴文化反而以“包孕吴越”的文化气度,毅然拥抱、勇敢接纳,适时吸收,大胆改造,将“吴越文化”合二为一,变身为一种全新的“吴文化”,同时在这种“新变”中不断求新求异,进取超越,萃取凝练为成熟而精致的新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