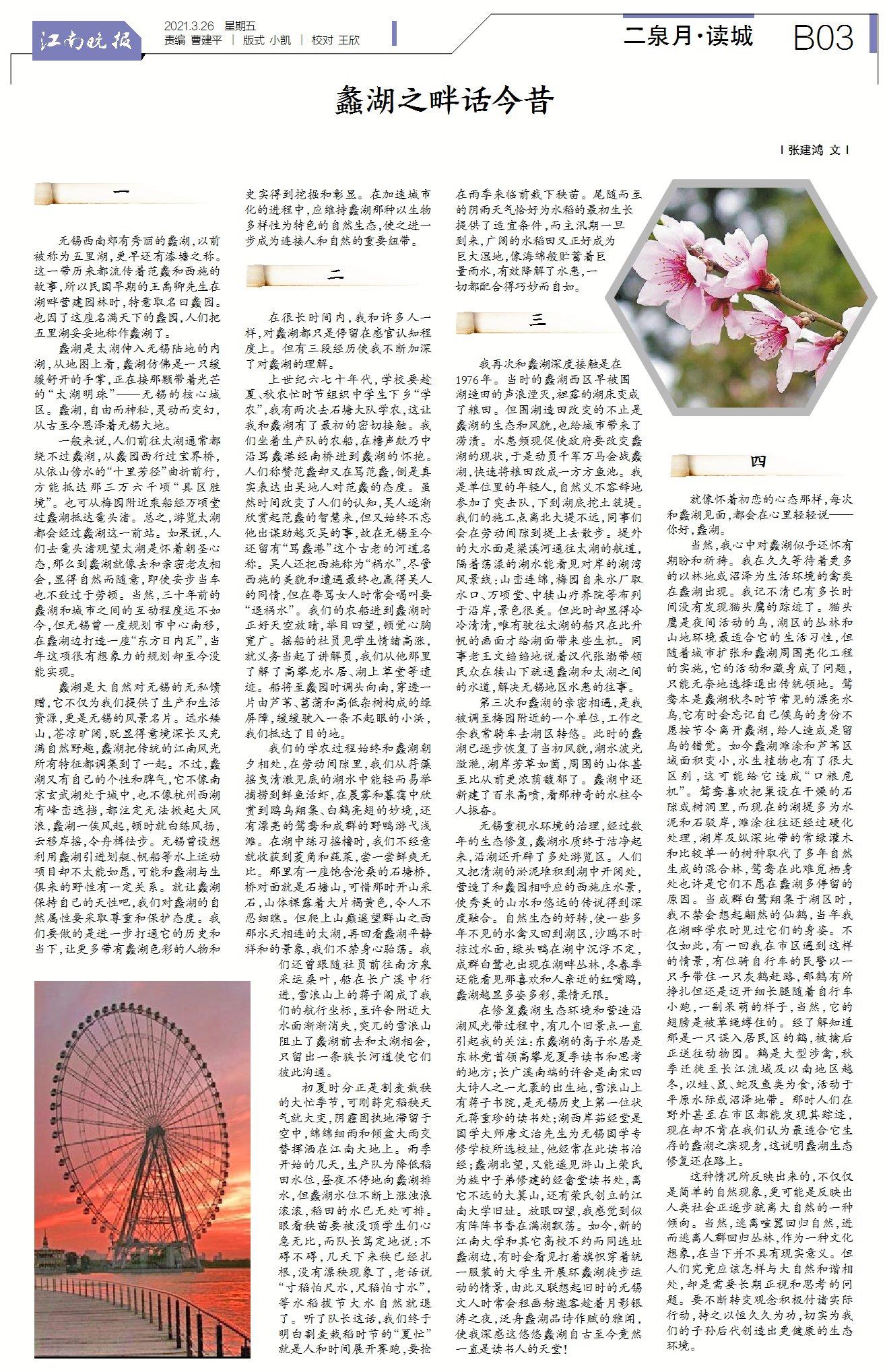|张建鸿 文|
一
无锡西南郊有秀丽的蠡湖,以前被称为五里湖,更早还有漆塘之称。这一带历来都流传着范蠡和西施的故事,所以民国早期的王禹卿先生在湖畔营建园林时,特意取名曰蠡园。也因了这座名满天下的蠡园,人们把五里湖妥妥地称作蠡湖了。
蠡湖是太湖伸入无锡陆地的内湖,从地图上看,蠡湖仿佛是一只缓缓舒开的手掌,正在接那颗带着光芒的“太湖明珠”——无锡的核心城区。蠡湖,自由而神秘,灵动而变幻,从古至今恩泽着无锡大地。
一般来说,人们前往太湖通常都绕不过蠡湖,从蠡园西行过宝界桥,从依山傍水的“十里芳径”曲折前行,方能抵达那三万六千顷“具区胜境”。也可从梅园附近乘船经万顷堂过蠡湖抵达鼋头渚。总之,游览太湖都会经过蠡湖这一前站。如果说,人们去鼋头渚观望太湖是怀着朝圣心态,那么到蠡湖就像去和亲密老友相会,显得自然而随意,即使安步当车也不致过于劳顿。当然,三十年前的蠡湖和城市之间的互动程度远不如今,但无锡曾一度规划市中心南移,在蠡湖边打造一座“东方日内瓦”,当年这项很有想象力的规划却至今没能实现。
蠡湖是大自然对无锡的无私馈赠,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生产和生活资源,更是无锡的风景名片。远水矮山,苍凉旷阔,既显得意境深长又充满自然野趣,蠡湖把传统的江南风光所有特征都调集到了一起。不过,蠡湖又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它不像南京玄武湖处于城中,也不像杭州西湖有峰峦遮挡,都注定无法掀起大风浪,蠡湖一俟风起,顿时就白练风扬,云移岸摇,令舟楫怯步。无锡曾设想利用蠡湖引进划艇、帆船等水上运动项目却不太能如愿,可能和蠡湖与生俱来的野性有一定关系。就让蠡湖保持自己的天性吧,我们对蠡湖的自然属性要采取尊重和保护态度。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打通它的历史和当下,让更多带有蠡湖色彩的人物和史实得到挖掘和彰显。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应维持蠡湖那种以生物多样性为特色的自然生态,使之进一步成为连接人和自然的重要纽带。
二
在很长时间内,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蠡湖都只是停留在感官认知程度上。但有三段经历使我不断加深了对蠡湖的理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要趁夏、秋农忙时节组织中学生下乡“学农”,我有两次去石塘大队学农,这让我和蠡湖有了最初的密切接触。我们坐着生产队的农船,在橹声欸乃中沿骂蠡港经南桥进到蠡湖的怀抱。人们称赞范蠡却又在骂范蠡,倒是真实表达出吴地人对范蠡的态度。虽然时间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吴人逐渐欣赏起范蠡的智慧来,但又始终不忘他出谋助越灭吴的事,故在无锡至今还留有“骂蠡港”这个古老的河道名称。吴人还把西施称为“祸水”,尽管西施的美貌和遭遇最终也赢得吴人的同情,但在辱骂女人时常会喝叫要“退祸水”。我们的农船进到蠡湖时正好天空放晴,举目四望,顿觉心胸宽广。摇船的社员见学生情绪高涨,就义务当起了讲解员,我们从他那里了解了高攀龙水居、湖上草堂等遗迹。船将至蠡园时调头向南,穿透一片由芦苇、菖蒲和高低杂树构成的绿屏障,缓缓驶入一条不起眼的小浜,我们抵达了目的地。
我们的学农过程始终和蠡湖朝夕相处,在劳动间隙里,我们从荇藻摇曳清澈见底的湖水中能轻而易举捕捞到鲜鱼活虾,在晨雾和暮霭中欣赏到鸥鸟翔集、白鹤亮翅的妙境,还有漂亮的鸳鸯和成群的野鸭游弋浅滩。在湖中练习摇橹时,我们不经意就收获到菱角和莼菜,尝一尝鲜爽无比。那里有一座饱含沧桑的石塘桥,桥对面就是石塘山,可惜那时开山采石,山体裸露着大片褐黄色,令人不忍细瞧。但爬上山巅遥望群山之西那水天相连的太湖,再回看蠡湖平静祥和的景象,我们不禁身心骀荡。我们还曾跟随社员前往南方泉采运桑叶,船在长广溪中行进,雪浪山上的蒋子阁成了我们的航行坐标,至许舍附近大水面渐渐消失,突兀的雪浪山阻止了蠡湖前去和太湖相会,只留出一条狭长河道使它们彼此沟通。
初夏时分正是割麦栽秧的大忙季节,可刚莳完稻秧天气就大变,阴霾固执地滞留于空中,绵绵细雨和倾盆大雨交替挥洒在江南大地上。雨季开始的几天,生产队为降低稻田水位,昼夜不停地向蠡湖排水,但蠡湖水位不断上涨浊浪滚滚,稻田的水已无处可排。眼看秧苗要被没顶学生们心急无比,而队长笃定地说:不碍不碍,几天下来秧已经扎根,没有漂秧现象了,老话说“寸稻怕尺水,尺稻怕寸水”,等水稻拔节大水自然就退了。听了队长这话,我们终于明白割麦栽稻时节的“夏忙”就是人和时间展开赛跑,要抢在雨季来临前栽下秧苗。尾随而至的阴雨天气恰好为水稻的最初生长提供了适宜条件,而主汛期一旦到来,广阔的水稻田又正好成为巨大湿地,像海绵般贮蓄着巨量雨水,有效降解了水患,一切都配合得巧妙而自如。
三
我再次和蠡湖深度接触是在1976年。当时的蠡湖西区早被围湖造田的声浪湮灭,袒露的湖床变成了粮田。但围湖造田改变的不止是蠡湖的生态和风貌,也给城市带来了涝渍。水患频现促使政府要改变蠡湖的现状,于是动员千军万马会战蠡湖,快速将粮田改成一方方鱼池。我是单位里的年轻人,自然义不容辞地参加了突击队,下到湖底挖土筑堤。我们的施工点离北大堤不远,同事们会在劳动间隙到堤上去散步。堤外的大水面是梁溪河通往太湖的航道,隔着荡漾的湖水能看见对岸的湖湾风景线:山峦连绵,梅园自来水厂取水口、万顷堂、中犊山疗养院等布列于沿岸,景色很美。但此时却显得冷冷清清,唯有驶往太湖的船只在此升帆的画面才给湖面带来些生机。同事老王文绉绉地说着汉代张渤带领民众在犊山下疏通蠡湖和太湖之间的水道,解决无锡地区水患的往事。
第三次和蠡湖的亲密相遇,是我被调至梅园附近的一个单位,工作之余我常骑车去湖区转悠。此时的蠡湖已逐步恢复了当初风貌,湖水波光潋滟,湖岸芳草如茵,周围的山体甚至比从前更浓荫馥郁了。蠡湖中还新建了百米高喷,看那神奇的水柱令人振奋。
无锡重视水环境的治理,经过数年的生态修复,蠡湖水质终于洁净起来,沿湖还开辟了多处游览区。人们又把清湖的淤泥堆积到湖中开阔处,营造了和蠡园相呼应的西施庄水景,使秀美的山水和悠远的传说得到深度融合。自然生态的好转,使一些多年不见的水禽又回到湖区,沙鸥不时掠过水面,绿头鸭在湖中沉浮不定,成群白鹭也出现在湖畔丛林,冬春季还能看见那喜欢和人亲近的红嘴鸥,蠡湖越显多姿多彩,柔情无限。
在修复蠡湖生态环境和营造沿湖风光带过程中,有几个旧景点一直引起我的关注:东蠡湖的高子水居是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夏季读书和思考的地方;长广溪南端的许舍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尤袤的出生地,雪浪山上有蒋子书院,是无锡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蒋重珍的读书处;湖西岸茹经堂是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所选校址,他经常在此读书治经;蠡湖北望,又能遥见浒山上荣氏为族中子弟修建的经畬堂读书处,离它不远的大箕山,还有荣氏创立的江南大学旧址。放眼四望,我感觉到似有阵阵书香在满湖飘荡。如今,新的江南大学和其它高校不约而同选址蠡湖边,有时会看见打着旗帜穿着统一服装的大学生开展环蠡湖徒步运动的情景,由此又联想起旧时的无锡文人时常会租画舫邀客趁着月影银涛之夜,泛舟蠡湖品诗作赋的雅闻,使我深感这悠悠蠡湖自古至今竟然一直是读书人的天堂!
四
就像怀着初恋的心态那样,每次和蠡湖见面,都会在心里轻轻说——你好,蠡湖。
当然,我心中对蠡湖似乎还怀有期盼和祈祷。我在久久等待着更多的以林地或沼泽为生活环境的禽类在蠡湖出现。我记不清已有多长时间没有发现猫头鹰的踪迹了。猫头鹰是夜间活动的鸟,湖区的丛林和山地环境最适合它的生活习性,但随着城市扩张和蠡湖周围亮化工程的实施,它的活动和藏身成了问题,只能无奈地选择退出传统领地。鸳鸯本是蠡湖秋冬时节常见的漂亮水鸟,它有时会忘记自己候鸟的身份不愿按节令离开蠡湖,给人造成是留鸟的错觉。如今蠡湖滩涂和芦苇区域面积变小,水生植物也有了很大区别,这可能给它造成“口粮危机”。鸳鸯喜欢把巢设在干燥的石隙或树洞里,而现在的湖堤多为水泥和石驳岸,滩涂往往还经过硬化处理,湖岸及纵深地带的常绿灌木和比较单一的树种取代了多年自然生成的混合林,鸳鸯在此难觅栖身处也许是它们不愿在蠡湖多停留的原因。当成群白鹭翔集于湖区时,我不禁会想起翩然的仙鹤,当年我在湖畔学农时见过它们的身姿。不仅如此,有一回我在市区遇到这样的情景,有位骑自行车的民警以一只手带住一只灰鹤赶路,那鹤有所挣扎但还是迈开细长腿随着自行车小跑,一副呆萌的样子,当然,它的翅膀是被草绳缚住的。经了解知道那是一只误入居民区的鹤,被擒后正送往动物园。鹤是大型涉禽,秋季迁徙至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越冬,以蛙、鼠、蛇及鱼类为食,活动于平原水际或沼泽地带。那时人们在野外甚至在市区都能发现其踪迹,现在却不肯在我们认为最适合它生存的蠡湖之滨现身,这说明蠡湖生态修复还在路上。
这种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现象,更可能是反映出人类社会正逐步疏离大自然的一种倾向。当然,逃离喧嚣回归自然,进而逃离人群回归丛林,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在当下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但人们究竟应该怎样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却是需要长期正视和思考的问题。要不断转变观念积极付诸实际行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切实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出更健康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