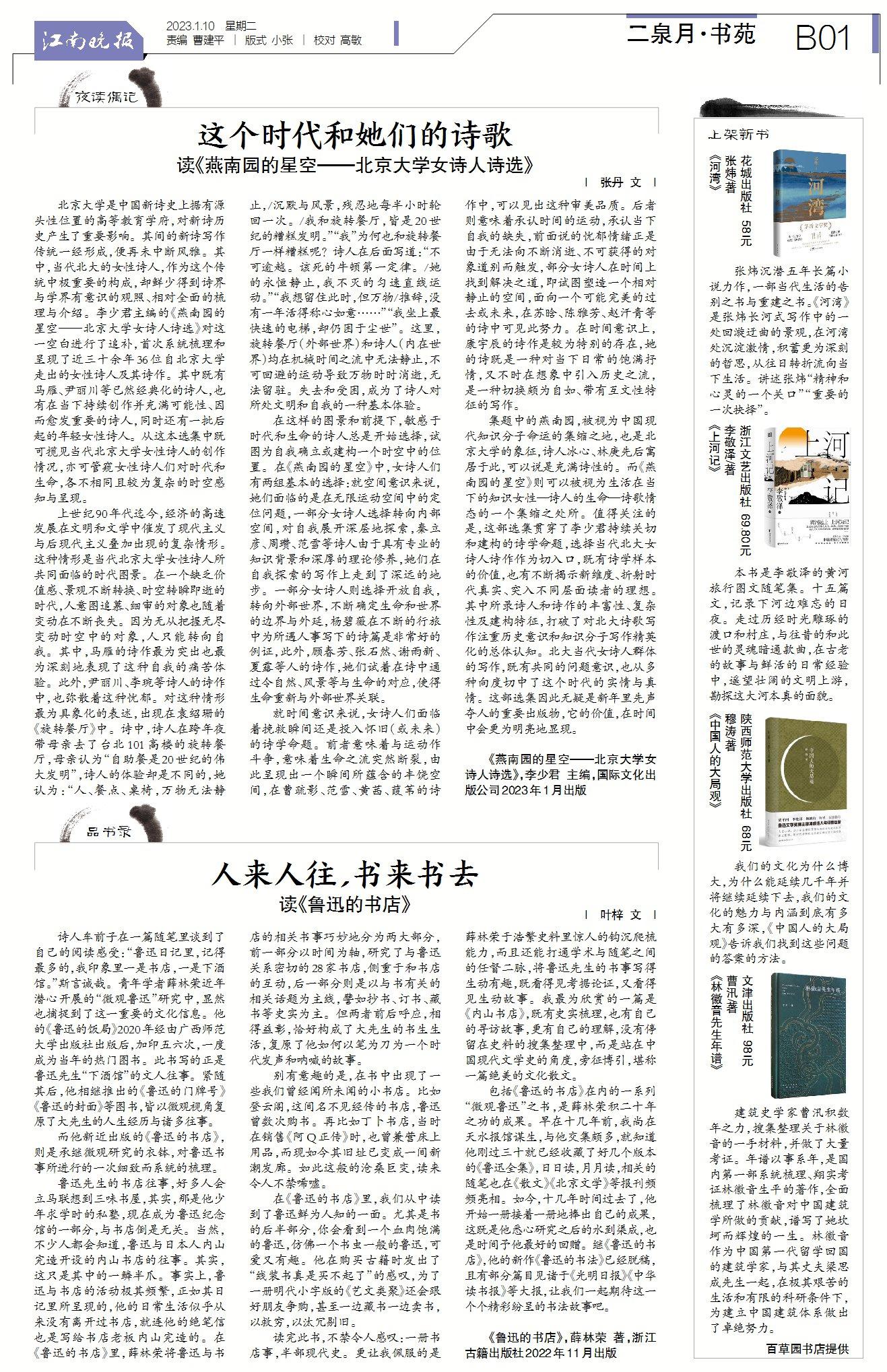| 张丹 文 |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诗史上据有源头性位置的高等教育学府,对新诗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间的新诗写作传统一经形成,便再未中断风雅。其中,当代北大的女性诗人,作为这个传统中极重要的构成,却鲜少得到诗界与学界有意识的观照、相对全面的梳理与介绍。李少君主编的《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对这一空白进行了追补,首次系统梳理和呈现了近三十余年36位自北京大学走出的女性诗人及其诗作。其中既有马雁、尹丽川等已然经典化的诗人,也有在当下持续创作并充满可能性、因而愈发重要的诗人,同时还有一批后起的年轻女性诗人。从这本选集中既可揽见当代北京大学女性诗人的创作情况,亦可管窥女性诗人们对时代和生命,各不相同且较为复杂的时空感知与呈现。
上世纪90年代迄今,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文明和文学中催发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叠加出现的复杂情形。这种情形是当代北京大学女性诗人所共同面临的时代图景。在一个缺乏价值感、景观不断转换、时空转瞬即逝的时代,人意图追慕、细审的对象也随着变动在不断丧失。因为无从把握无尽变动时空中的对象,人只能转向自我。其中,马雁的诗作最为突出也最为深刻地表现了这种自我的痛苦体验。此外,尹丽川、李琬等诗人的诗作中,也弥散着这种忧郁。对这种情形最为具象化的表述,出现在袁绍珊的《旋转餐厅》中。诗中,诗人在跨年夜带母亲去了台北101高楼的旋转餐厅,母亲认为“自助餐是20世纪的伟大发明”,诗人的体验却是不同的,她认为:“人、餐点、桌椅,万物无法静止,/沉默与风景,残忍地每半小时轮回一次。/我和旋转餐厅,皆是20世纪的糟糕发明。”“我”为何也和旋转餐厅一样糟糕呢?诗人在后面写道:“不可逾越。该死的牛顿第一定律。/她的永恒静止,我不灭的匀速直线运动。”“我想留住此时,但万物/推辞,没有一年活得称心如意……”“我坐上最快速的电梯,却仍困于尘世”。这里,旋转餐厅(外部世界)和诗人(内在世界)均在机械时间之流中无法静止,不可回避的运动导致万物时时消逝,无法留驻。失去和受困,成为了诗人对所处文明和自我的一种基本体验。
在这样的图景和前提下,敏感于时代和生命的诗人总是开始选择,试图为自我确立或建构一个时空中的位置。在《燕南园的星空》中,女诗人们有两组基本的选择:就空间意识来说,她们面临的是在无限运动空间中的定位问题,一部分女诗人选择转向内部空间,对自我展开深层地探索,秦立彦、周瓒、范雪等诗人由于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她们在自我探索的写作上走到了深远的地步。一部分女诗人则选择开放自我,转向外部世界,不断确定生命和世界的边界与外延,杨碧薇在不断的行旅中为所遇人事写下的诗篇是非常好的例证,此外,顾春芳、张石然、谢雨新、夏露等人的诗作,她们试着在诗中通过令自然、风景等与生命的对应,使得生命重新与外部世界关联。
就时间意识来说,女诗人们面临着挽救瞬间还是投入怀旧(或未来)的诗学命题。前者意味着与运动作斗争,意味着生命之流突然断裂,由此呈现出一个瞬间所蕴含的丰饶空间,在曹疏影、范雪、黄茜、葭苇的诗作中,可以见出这种审美品质。后者则意味着承认时间的运动,承认当下自我的缺失,前面说的忧郁情绪正是由于无法向不断消逝、不可获得的对象道别而触发,部分女诗人在时间上找到解决之道,即试图塑造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面向一个可能完美的过去或未来,在苏晗、陈雅芳、赵汗青等的诗中可见此努力。在时间意识上,康宇辰的诗作是较为特别的存在,她的诗既是一种对当下日常的饱满抒情,又不时在想象中引入历史之流,是一种切换颇为自如、带有互文性特征的写作。
集题中的燕南园,被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集缩之地,也是北京大学的象征,诗人冰心、林庚先后寓居于此,可以说是充满诗性的。而《燕南园的星空》则可以被视为生活在当下的知识女性—诗人的生命—诗歌情态的一个集缩之处所。值得关注的是,这部选集贯穿了李少君持续关切和建构的诗学命题,选择当代北大女诗人诗作作为切入口,既有诗学样本的价值,也有不断揭示新维度、折射时代真实、突入不同层面读者的理想。其中所录诗人和诗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建构特征,打破了对北大诗歌写作注重历史意识和知识分子写作精英化的总体认知。北大当代女诗人群体的写作,既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也从多种向度切中了这个时代的实情与真情。这部选集因此无疑是新年里先声夺人的重要出版物,它的价值,在时间中会更为明亮地显现。
《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李少君 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