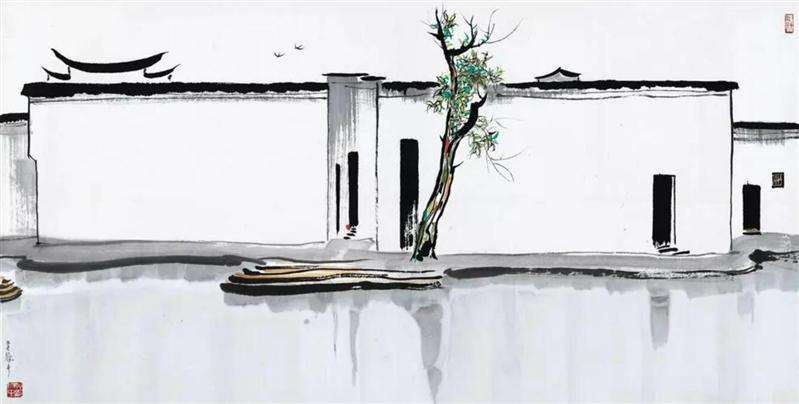1
在对江南文化相关资料的梳理中,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环太湖地区,古今地名中带“兴”字较多,如宜兴(义兴)、长兴、吴兴、嘉兴、绍兴、合兴等,这应当不是一个巧合,就像历史上的边境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安”“×化”地名比较多也不是巧合。“×安”“×化”的命名,代表了这个地区是新征服或文明初化之地,而“兴”的意思是兴发、勃兴、开发之意。事实上江南地区特别是环太湖地区,历史上就是文明兴发兴盛之地,从青莲岗文化,到良渚文化、湖熟文化,从泰伯奔吴到春申治吴,贯串的一条主线,就是对吴地乃至吴越地区的开发、垦殖。
早期吴地的开发主要是农业、水利、交通和城邑的开发。《越绝书》记载:春申君治吴时,“立无锡塘,治无锡湖”,实际上就是指对无锡地区的开发。可以想见,如今的无锡主城地区当时还是汪洋一片的无锡湖。开发的具体手段是筑堤拦水、围湖造田。根据老一辈农史学家缪启愉的研究,“塘”是沿湖修筑的圩堤,把太湖及其他湖泊与湖周边地区间隔开来,防止湖水泛滥;同时沿着圩堤再开挖一条深沟,通过密集的水网系统把低地沼泽地区的水引排出去。这样就形成了一片可以种植和居住的陆地。反过来,也可以朝着太湖方向,不断围湖造田。就是通过这样的开发方式,江南地区形成了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塘浦圩田”地貌(“浦”是指与塘堤垂直的河道,所谓“横塘纵浦”),如今,在江浙沪地区,也留存着很多“×塘”“×浦”的地名,记载着这些地区早期开发的历史。
所以,我们认为,江南文化的特质首先就是“兴”,就是“开发开拓”;江南地区可形象地称之为较早的“文明开发区”。
2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从来都不是内生性、关门式开发。泰伯奔吴的时代,太湖周边处于新石器良渚文化阶段,西北文明与东南文明第一次实现了碰撞融合;春秋战国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楚地文明对吴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大量的楚人入吴尤其是楚人相吴(吴国先后有三任丞相是楚人:狐庸、伍子胥、伯噽,越国的范蠡也是楚人),带来了楚地的水利、筑城理念和技术。伍子胥在太湖周边开挖凿通了多条河道,对于今天江南水系和城乡风貌的形成意义重大。
随后有两次比较大的中原文化的融入:东晋衣冠南渡与宋室南迁。东晋衣冠南渡时期,环太湖地区已经成为富庶发达区域,两种地域文化之间出现交流、冲突并最终走向融合。著名的“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实际上是中原文化对江南文化的一个想象性寓言:宜兴周氏在当时是豪族,自然被外来的中原人物视为“一害”,而周处终至醒悟,代表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成功沟通与和解。
在宋室南迁之后,江南地区接受一定规模的人口流入以及较有影响的文化融入还有几次,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万历之后的徽商入吴,在诸多领域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结论,江南文化第二方面的特质是开放包容。开放是能够拥抱一切文化的异量之美,并在与新的文化的结合中开拓出文化新特色、新境界。
江南的开放包容特质在进入晚清、民国特别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所以,中国东南一域的海派文化之“海”,不应是代表上海或海洋的“海”字,也不应是指泛滥低贱(最早北京诬称外地进京班子为“海派”),而应该是指“海量能容”和“海纳百川”。
3
历代文人爱歌咏江南、谈论江南。而作为意象和话题的“江南”,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地理概念,江南具有多义性和变迁性,甚至有所谓的“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明清经济史专家李伯重把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苏、松、常、镇、宁、杭、嘉、湖、仓州)定义为明清时期的江南,与我们今天常说的“长三角地区”高度重合,涉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相关地区。而作为文化概念的江南,其同源性和整一性从什么方面得以体现出来?本文力图从整体而不是从某一个具体城市碎片的角度,给江南文化画一张速写,形成我们谈论江南文化的一个粗要框架。
江南文化第三方面特质是重实学、务实事。与儒学、道家比较关注天、道、心等抽象形而上概念相比,实学更多关注如兵、农、工、医等具体学科的学问和技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实学的传统。在最初的儒家教育体系中,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在当时就是实学。但随着儒学在国家政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实学的空间没有如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样得到充分发展,反而成为某些道学家们眼中的“小道”甚至是“奇技淫巧”。实学与心性之学的对立,本质上是功利与道义的对立(“义利之辨”),实学往往代表的是功利的一边,而心性之学代表的是“道义”的一边。这对矛盾关系,有时候还表达为“农商之辨”:农为本,代表了道义一方;商为末,代表了功利一方。这样,实学与“务功事利”几乎划上了等号,而心性之学往往排斥实务、“蹈空凌虚”,与“百姓日用”距离较远。
江南文化底蕴中的重实学、务实事的特征一直非常明显。范蠡撰写《养鱼经》和经商而致巨富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另一个很好的注解是《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这两部书是江南人士书写自身历史、争取文化地位最重要的代表作。二书共同推崇孔门弟子子贡(端木赐)。子贡是个大商人,也是个战略家、外交家,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和孔门其他弟子相比,子贡身上的“王霸兼用”、务功事利的色彩非常明显。《越绝书》说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与之里”,树立了子贡之学崇高价值地位。这两部书也说明了子贡之学在吴越地区的影响巨大,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吴越地区精神文化标签(太湖的贡湖得名很可能与子贡有关,待考)。
江南地区的实学传统,到宋室南渡以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张扬契机。南宋小朝廷相当长一段时期崇尚“安石之学”。这一点让理学家朱熹非常恼火。王安石非常重视实学教育,主张将《周官》这一类记载实用管理知识的书作为官学教材。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一大贡献就是重实学。他说,王安石之前的儒家经学研究“顾其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由于临安朝廷对安石之学的倚重,江南地区成为“安石之学”的滥觞之所;而后,在该地区及周边出现了以陈亮、陈傅良浙东、金华学派为代表的系统化“事功之学”理论。到了明中后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是对过分强调“心性之学”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反动,与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关联度很高。在无锡地区,东林学人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反对当时空洞玄虚的学风。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近现代以来,一些思想界先锋学者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福明),也与江南文化中的重实学、务实事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4
正因为江南文化中重实学、务实事的价值取向,经商谋利在这里从来就不是卑贱之事。传统中国儒家文人追求的“耕读传家”,在江南社会中非常自然地转化为“商读传家”,“士而商”“商而士”情况非常普遍。据严迪昌先生的研究,“士而商”“商而士”的风气之盛,可以从“盐商占籍”中反映出来。“占籍”是一种科举制度安排。原先,安徽盐商及其子弟,要参加地方科举考试必须回到原籍。明万历三十三年,经过盐商御史(相当于今天盐政领域的督查组组长)叶永盛(安徽人)的争取,安徽盐商及其子弟可以在杭州参加科举,录取名额单列。也正是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江南地区“商而士”“士而商”的社会风气。据统计,明清两代产生的进士与状元中,出身于盐商家族的占有一个很高的比例。
江南地区“商而士”“士而商”的社会风气,造就了“崇文”与“乐商”并重的价值理念,形成了江南文化第四方面的特质。在重文与乐商并重的理念作用下,江南地区读书的氛围、经商的风气同时都很浓厚,也造就了一代一代“儒商”和怀抱工商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更促成了知识资源和经济资源充分融通,这和国内某些地区过分重文轻商或过分重商轻文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如果说“开发开拓”“开放包容”“重实学务实事”“崇文与乐商并重”这四个方面能够概括江南文化,那么这四个方面还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兴”,就是开发开拓。
开放包容是开发开拓的动力基础。放眼世界,几乎每一个发展得好、文明兴盛之地,都和移民迁入、文化大融合有关。江南文化的传承发展,也符合这个规律。从3200年前的泰伯奔吴,到东晋衣冠南迁,到后来的宋室南迁,再到后来的明代万历之后徽商入吴,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地人口流向长三角,每一次人口迁移,都给这个地区造成了新的发展局面。
重实学务实事是开发开拓的客观要求。无论是筑塘筑城,还是种植作物、打造农具兵器,都需要专业技术支撑。而组织开发活动,也不能天天空谈哲理、大喊口号、为“君子小人”“姓社姓资”等问题争论不休。崇文与乐商并重决定了开发的综合性与质量。江南地区的开发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开发,而且是精神层面的开发。只有物质开发与精神开发互动共促,这样的开发才是全面的、高质量的。
粗要速写江南文化,探秘江南文化精神,为我们今天传承弘扬江南文化、促进未来发展指点了一个方向。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谋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形成长三角更强大的整体联动融合优势;我们应当始终把握江南文化中开发开拓之魂,在新时代再造江南地区发展辉煌;我们应当以更宽广的怀抱拥抱世界,更大规模地引进高素质人才,打造知识与经济融合发展高地;我们应当进一步擦亮工商品牌、锤炼工商价值,让工商基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中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