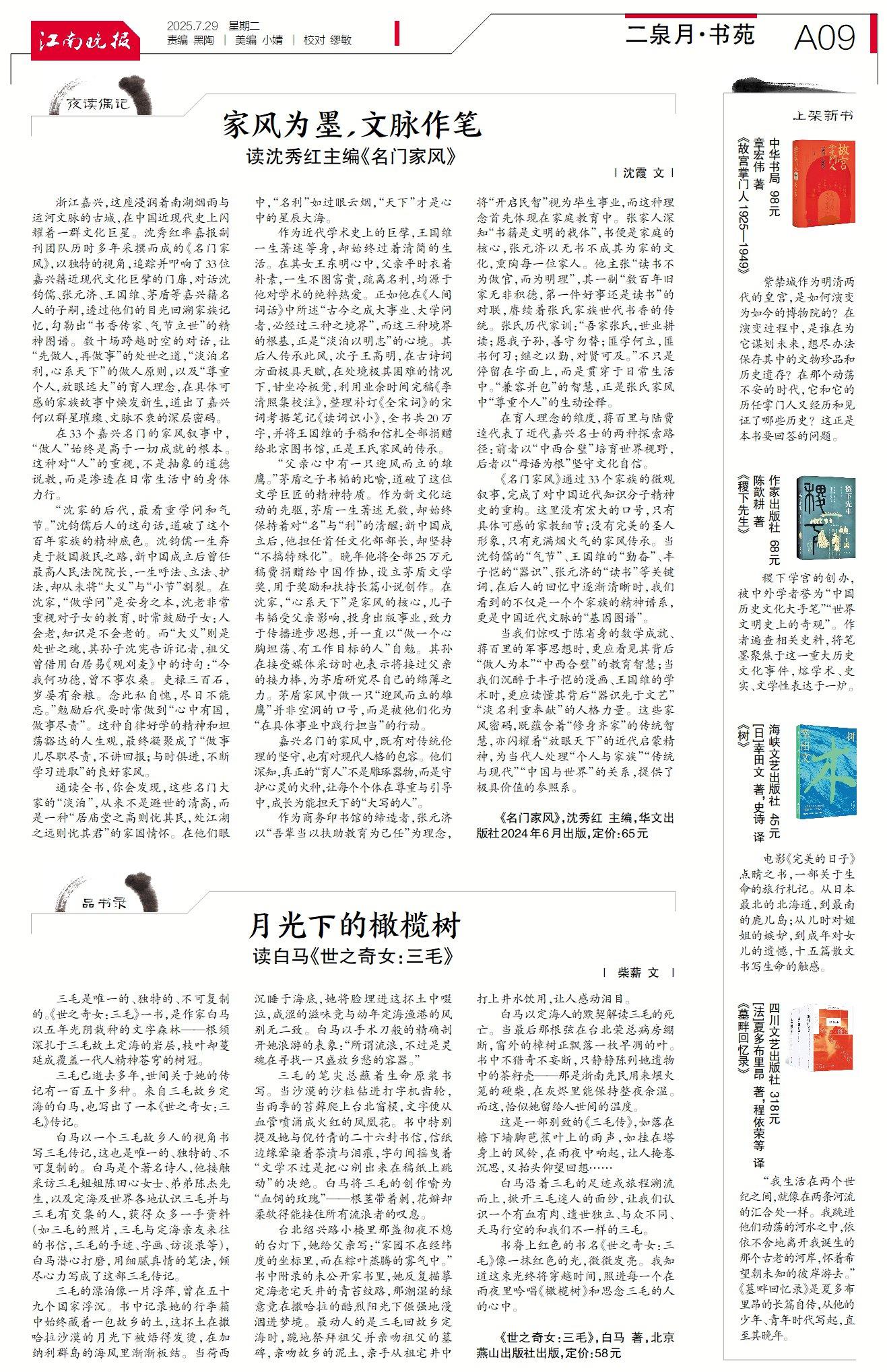| 柴薪 文 |
三毛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世之奇女:三毛》一书,是作家白马以五年光阴栽种的文字森林——根须深扎于三毛故土定海的岩层,枝叶却蔓延成覆盖一代人精神苍穹的树冠。
三毛已逝去多年,世间关于她的传记有一百五十多种。来自三毛故乡定海的白马,也写出了一本《世之奇女:三毛》传记。
白马以一个三毛故乡人的视角书写三毛传记,这也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白马是个著名诗人,他接触采访三毛姐姐陈田心女士、弟弟陈杰先生,以及定海及世界各地认识三毛并与三毛有交集的人,获得众多一手资料(如三毛的照片,三毛与定海亲友来往的书信,三毛的手迹、字画、访谈录等),白马潜心打磨,用细腻真情的笔法,倾尽心力写成了这部三毛传记。
三毛的漂泊像一片浮萍,曾在五十九个国家浮沉。书中记录她的行李箱中始终藏着一包故乡的土,这抔土在撒哈拉沙漠的月光下被焐得发烫,在加纳利群岛的海风里渐渐板结。当荷西沉睡于海底,她将脸埋进这抔土中啜泣,咸涩的滋味竟与幼年定海渔港的风别无二致。白马以手术刀般的精确剖开她浪游的表象:“所谓流浪,不过是灵魂在寻找一只盛放乡愁的容器。”
三毛的笔尖总蘸着生命原浆书写。当沙漠的沙粒钻进打字机齿轮,当雨季的苔藓爬上台北窗棂,文字便从血管喷涌成火红的凤凰花。书中特别提及她与倪竹青的二十六封书信,信纸边缘晕染着茶渍与泪痕,字句间摇曳着“文学不过是把心剜出来在稿纸上跳动”的决绝。白马将三毛的创作喻为“血饲的玫瑰”——根茎带着刺,花瓣却柔软得能接住所有流浪者的叹息。
台北绍兴路小楼里那盏彻夜不熄的台灯下,她给父亲写:“家园不在经纬度的坐标里,而在粽叶蒸腾的雾气中。”书中附录的未公开家书里,她反复描摹定海老宅天井的青苔纹路,那潮湿的绿意竟在撒哈拉的酷烈阳光下倔强地漫洇进梦境。最动人的是三毛回故乡定海时,跪地祭拜祖父并亲吻祖父的墓碑,亲吻故乡的泥土,亲手从祖宅井中打上井水饮用,让人感动泪目。
白马以定海人的默契解读三毛的死亡。当最后那根弦在台北荣总病房绷断,窗外的樟树正飘落一枚早凋的叶。书中不猎奇不妄断,只静静陈列她遗物中的茶籽壳——那是浙南先民用来煨火笼的硬柴,在灰烬里能保持整夜余温。而这,恰似她留给人世间的温度。
这是一部别致的《三毛传》,如落在檐下墙脚芭蕉叶上的雨声,如挂在塔身上的风铃,在雨夜中响起,让人掩卷沉思,又抬头仰望回想……
白马沿着三毛的足迹或旅程溯流而上,掀开三毛迷人的面纱,让我们认识一个有血有肉、遗世独立、与众不同、天马行空的和我们不一样的三毛。
书脊上红色的书名《世之奇女:三毛》像一抹红色的光,微微发亮。我知道这束光终将穿越时间,照进每一个在雨夜里吟唱《橄榄树》和思念三毛的人的心中。
《世之奇女:三毛》,白马 著,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定价: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