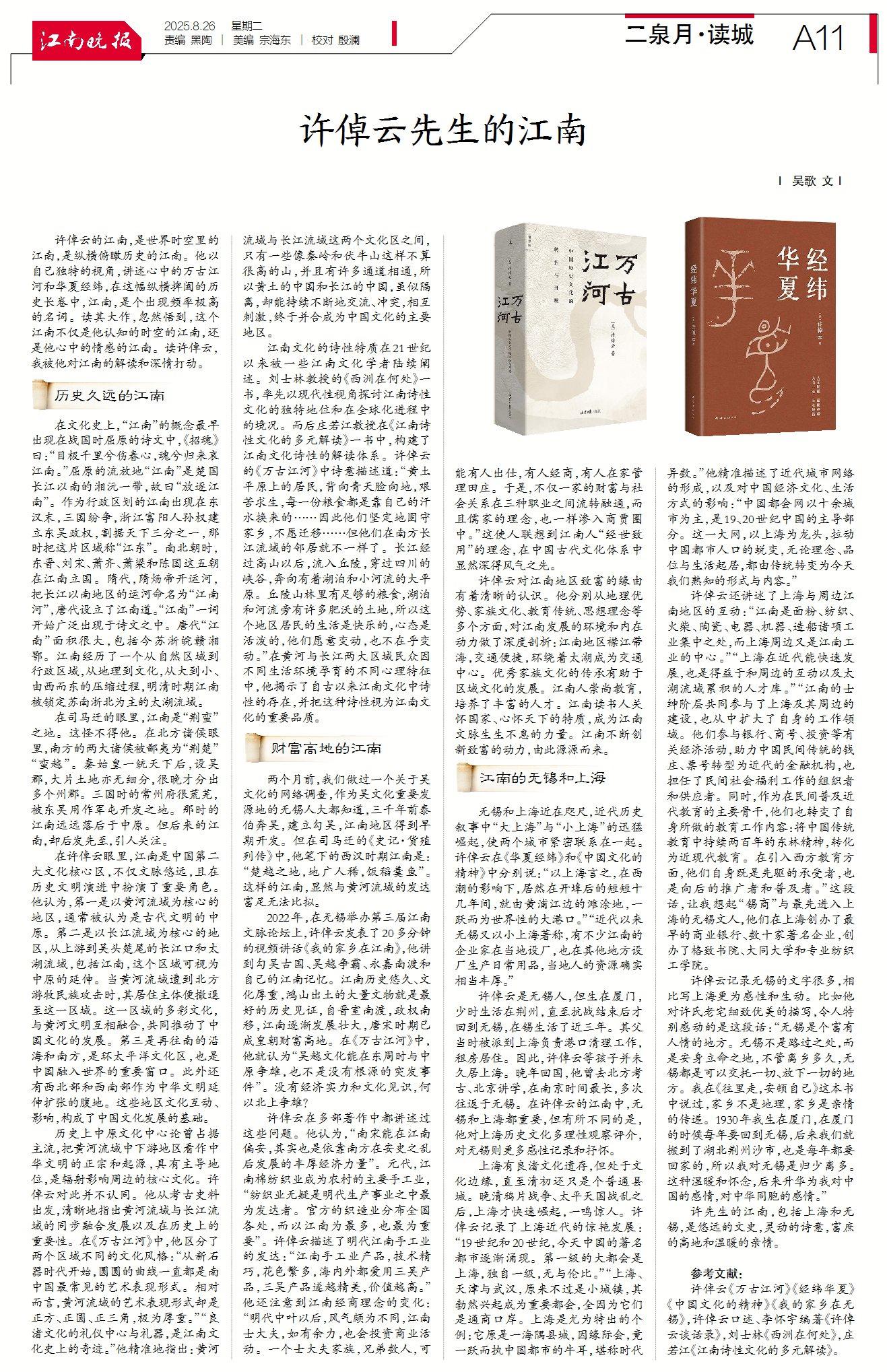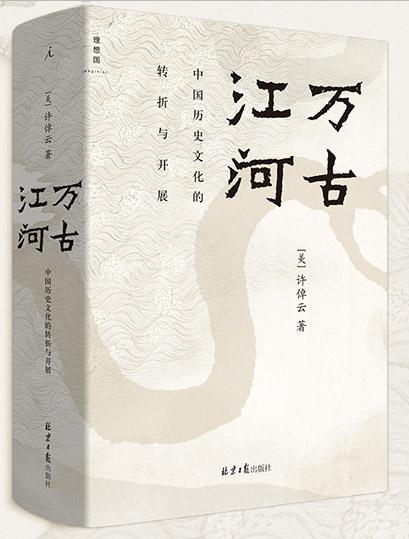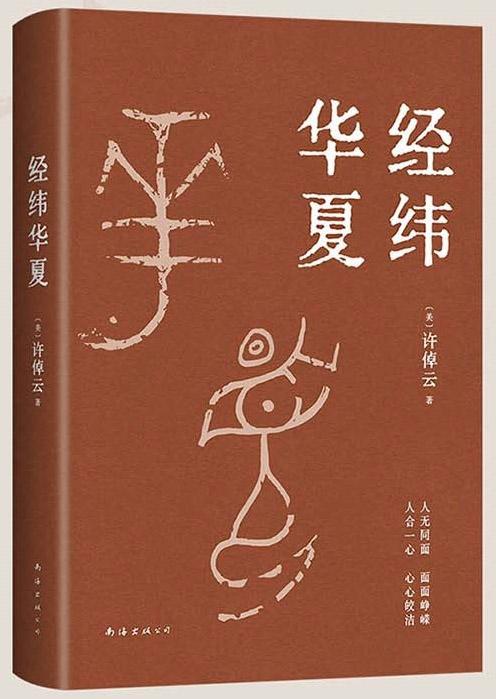许倬云的江南,是世界时空里的江南,是纵横俯瞰历史的江南。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讲述心中的万古江河和华夏经纬,在这幅纵横捭阖的历史长卷中,江南,是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名词。读其大作,忽然悟到,这个江南不仅是他认知的时空的江南,还是他心中的情感的江南。读许倬云,我被他对江南的解读和深情打动。
历史久远的江南
在文化史上,“江南”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战国时屈原的诗文中,《招魂》曰:“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屈原的流放地“江南”是楚国长江以南的湘沅一带,故曰“放逐江南”。作为行政区划的江南出现在东汉末,三国纷争,浙江富阳人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割据天下三分之一,那时把这片区域称“江东”。南北朝时,东晋、刘宋、萧齐、萧梁和陈国这五朝在江南立国。隋代,隋炀帝开运河,把长江以南地区的运河命名为“江南河”,唐代设立了江南道。“江南”一词开始广泛出现于诗文之中。唐代“江南”面积很大,包括今苏浙皖赣湘鄂。江南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区域到行政区域,从地理到文化,从大到小、由西而东的压缩过程,明清时期江南被锁定苏南浙北为主的太湖流域。
在司马迁的眼里,江南是“荆蛮”之地。这怪不得他。在北方诸侯眼里,南方的两大诸侯被鄙夷为“荆楚”“蛮越”。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设吴郡,大片土地亦无细分,很晚才分出多个州郡。三国时的常州府很荒芜,被东吴用作军屯开发之地。那时的江南远远落后于中原。但后来的江南,却后发先至,引人关注。
在许倬云眼里,江南是中国第二大文化核心区,不仅文脉悠远,且在历史文明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第一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古代文明的中原。第二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地区,从上游到吴头楚尾的长江口和太湖流域,包括江南,这个区域可视为中原的延伸。当黄河流域遭到北方游牧民族攻击时,其居住主体便撤退至这一区域。这一区域的多彩文化,与黄河文明互相融合,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第三是再往南的沿海和南方,是环太平洋文化区,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窗口。此外还有西北部和西南部作为中华文明延伸扩张的腹地。这些地区文化互动、影响,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
历史上中原文化中心论曾占据主流,把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看作中华文明的正宗和起源,具有主导地位,是辐射影响周边的核心文化。许倬云对此并不认同。他从考古史料出发,清晰地指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同步融合发展以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万古江河》中,他区分了两个区域不同的文化风格:“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与礼器,是江南文化史上的奇迹。”他精准地指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
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在21世纪以来被一些江南文化学者陆续阐述。刘士林教授的《西洲在何处》一书,率先以现代性视角探讨江南诗性文化的独特地位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境况。而后庄若江教授在《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一书中,构建了江南文化诗性的解读体系。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诗意描述道:“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家乡,不愿迁移……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在黄河与长江两大区域民众因不同生活环境孕育的不同心理特征中,他揭示了自古以来江南文化中诗性的存在,并把这种诗性视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品质。
财富高地的江南
两个月前,我们做过一个关于吴文化的网络调查,作为吴文化重要发源地的无锡人大都知道,三千年前泰伯奔吴,建立勾吴,江南地区得到早期开发。但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他笔下的西汉时期江南是:“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样的江南,显然与黄河流域的发达富足无法比拟。
2022年,在无锡举办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上,许倬云发表了20多分钟的视频讲话《我的家乡在江南》,他讲到勾吴古国、吴越争霸、永嘉南渡和自己的江南记忆。江南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鸿山出土的大量文物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自晋室南渡,政权南移,江南逐渐发展壮大,唐宋时期已成皇朝财富高地。在《万古江河》中,他就认为“吴越文化能在东周时与中原争雄,也不是没有根源的突发事件”。没有经济实力和文化见识,何以北上争雄?
许倬云在多部著作中都讲述过这些问题。他认为,“南宋能在江南偏安,其实也是依靠南方在安史之乱后发展的丰厚经济力量”。元代,江南棉纺织业成为农村的主要手工业,“纺织业无疑是明代生产事业之中最为发达者。官方的织造业分布全国各处,而以江南为最多,也最为重要”。许倬云描述了明代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手工业产品,技术精巧,花色繁多,海内外都爱用三吴产品,三吴产品遂越精美,价值越高。”他还注意到江南经商理念的变化:“明代中叶以后,风气颇为不同,江南士大夫,如有余力,也会投资商业活动。一个士大夫家族,兄弟数人,可能有人出仕,有人经商,有人在家管理田庄。于是,不仅一家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在三种职业之间流转融通,而且儒家的理念,也一样渗入商贾圈中。”这使人联想到江南人“经世致用”的理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显然深得风气之先。
许倬云对江南地区致富的缘由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分别从地理优势、家族文化、教育传统、思想理念等多个方面,对江南发展的环境和内在动力做了深度剖析:江南地区襟江带海,交通便捷,环绕着太湖成为交通中心。优秀家族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区域文化的发展。江南人崇尚教育,培养了丰富的人才。江南读书人关怀国家、心怀天下的特质,成为江南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江南不断创新致富的动力,由此源源而来。
江南的无锡和上海
无锡和上海近在咫尺,近代历史叙事中“大上海”与“小上海”的迅猛崛起,使两个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倬云在《华夏经纬》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分别说:“以上海言之,在西潮的影响下,居然在开埠后的短短十几年间,就由黄浦江边的滩涂地,一跃而为世界性的大港口。”“近代以来无锡又以小上海著称,有不少江南的企业家在当地设厂,也在其他地方设厂生产日常用品,当地人的资源确实相当丰厚。”
许倬云是无锡人,但生在厦门,少时生活在荆州,直至抗战结束后才回到无锡,在锡生活了近三年。其父当时被派到上海负责港口清理工作,租房居住。因此,许倬云等孩子并未久居上海。晚年回国,他曾去北方考古、北京讲学,在南京时间最长,多次往返于无锡。在许倬云的江南中,无锡和上海都重要,但有所不同的是,他对上海历史文化多理性观察评介,对无锡则更多感性记录和抒怀。
上海有良渚文化遗存,但处于文化边缘,直至清初还只是个普通县城。晚清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之后,上海才快速崛起,一鸣惊人。许倬云记录了上海近代的惊艳发展:“19世纪和20世纪,今天中国的著名都市逐渐涌现。第一级的大都会是上海,独自一级,无与伦比。”“上海、天津与武汉,原来不过是小城镇,其勃然兴起成为重要都会,全因为它们是通商口岸。上海是尤为特出的个例:它原是一海隅县城,因缘际会,竟一跃而执中国都市的牛耳,堪称时代异数。”他精准描述了近代城市网络的形成,以及对中国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都会网以十余城市为主,是19、20世纪中国的主导部分。这一大网,以上海为龙头,拉动中国都市人口的蜕变,无论理念、品位与生活起居,都由传统转变为今天我们熟知的形式与内容。”
许倬云还讲述了上海与周边江南地区的互动:“江南是面粉、纺织、火柴、陶瓷、电器、机器、造船诸项工业集中之处,而上海周边又是江南工业的中心。”“上海在近代能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和周边的互动以及太湖流域累积的人才库。”“江南的士绅阶层共同参与了上海及其周边的建设,也从中扩大了自身的工作领域。他们参与银行、商号、投资等有关经济活动,助力中国民间传统的钱庄、票号转型为近代的金融机构,也担任了民间社会福利工作的组织者和供应者。同时,作为在民间普及近代教育的主要骨干,他们也转变了自身所做的教育工作内容:将中国传统教育中持续两百年的东林精神,转化为近现代教育。在引入西方教育方面,他们自身既是先驱的承受者,也是向后的推广者和普及者。”这段话,让我想起“锡商”与最先进入上海的无锡文人,他们在上海创办了最早的商业银行、数十家著名企业,创办了格致书院、大同大学和专业纺织工学院。
许倬云记录无锡的文字很多,相比写上海更为感性和生动。比如他对许氏老宅细致优美的描写,令人特别感动的是这段话:“无锡是个富有人情的地方。无锡不是路过之处,而是安身立命之地,不管离乡多久,无锡都是可以交托一切、放下一切的地方。我在《往里走,安顿自己》这本书中说过,家乡不是地理,家乡是亲情的传递。1930年我生在厦门,在厦门的时候每年要回到无锡,后来我们就搬到了湖北荆州沙市,也是每年都要回家的,所以我对无锡是归少离多。这种温暖和怀念,后来升华为我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华同胞的感情。”
许先生的江南,包括上海和无锡,是悠远的文史,灵动的诗意,富庶的高地和温暖的亲情。
参考文献:
许倬云《万古江河》《经纬华夏》《中国文化的精神》《我的家乡在无锡》,许倬云口述、李怀宇编著《许倬云谈话录》,刘士林《西洲在何处》,庄若江《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