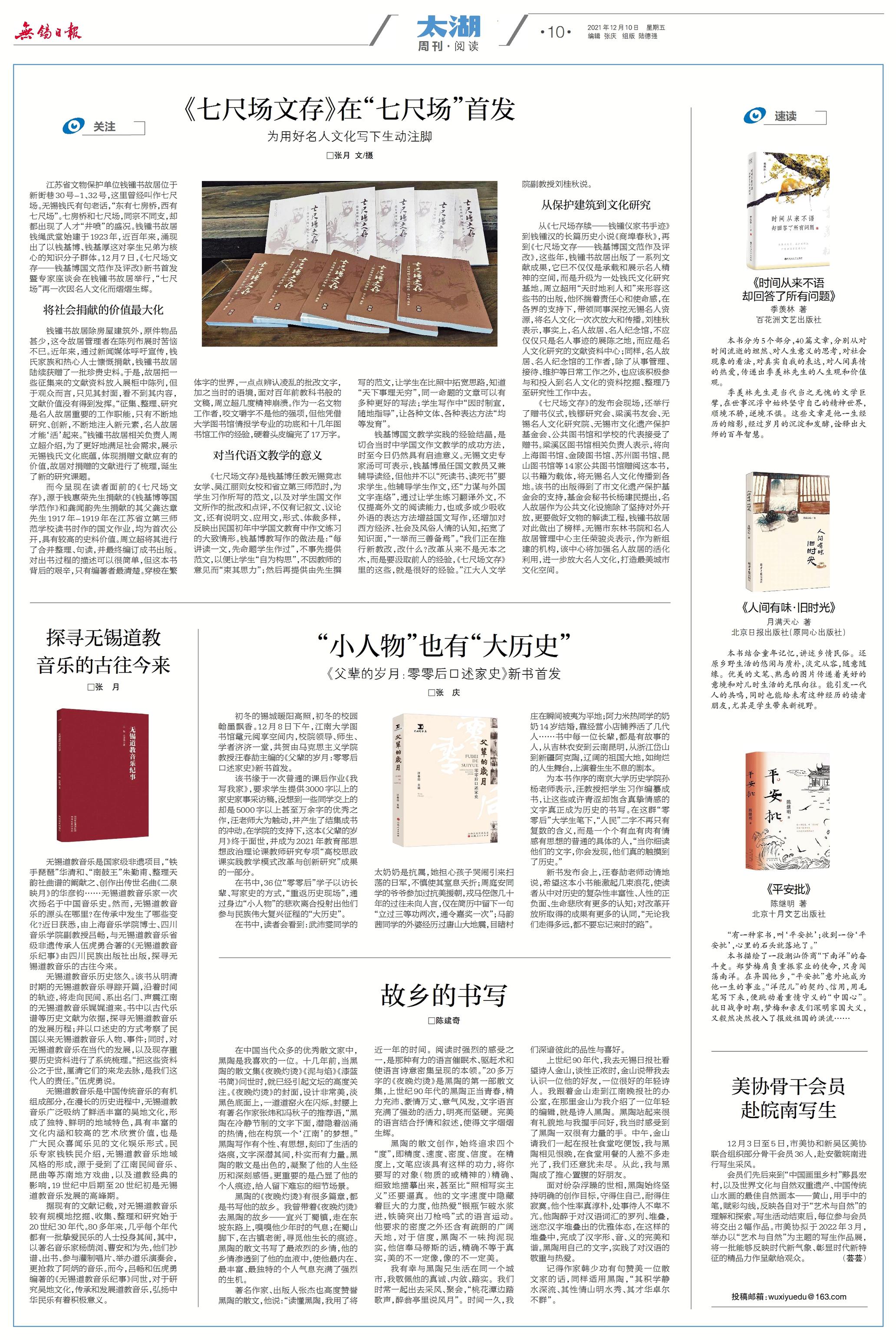□陈建奇
在中国当代众多的优秀散文家中,黑陶是我喜欢的一位。十几年前,当黑陶的散文集《夜晚灼烫》《泥与焰》《漆蓝书简》问世时,就已经引起文坛的高度关注。《夜晚灼烫》的封面,设计非常美,淡黑色底面上,一道道窑火在闪烁。封腰上有著名作家张炜和冯秋子的推荐语,“黑陶在冷静节制的文字下面,潜隐着汹涌的热情,他在构筑一个‘江南’的梦想。”黑陶写作有个性、有思想,刻印了生活的烙痕,文字深潜其间,朴实而有力量。黑陶的散文是出色的,凝聚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深刻感悟。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他的个人痕迹,给人留下难忘的细节场景。
黑陶的《夜晚灼烫》有很多篇章,都是书写他的故乡。我曾带着《夜晚灼烫》去黑陶的故乡——宜兴丁蜀镇,走在东坡东路上,嗅嗅他少年时的气息;在蜀山脚下,在古镇老街,寻觅他生长的痕迹。黑陶的散文书写了最浓烈的乡情,他的乡情渗透到了他的血液中,使他最内在、最丰富、最独特的个人气息充满了强烈的生机。
著名作家、出版人张杰也高度赞誉黑陶的散文,他说:“读懂黑陶,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阅读时强烈的感受之一,是那种有力的语言催眠术、驱赶术和使语言诗意密集呈现的本领。”20多万字的《夜晚灼烫》是黑陶的第一部散文集,上世纪90年代的黑陶正当青春,精力充沛、豪情万丈、意气风发,文字语言充满了强劲的活力,明亮而坚硬。完美的语言结合抒情和叙述,使得文字熠熠生辉。
黑陶的散文创作,始终追求四个“度”,即精度、速度、密度、信度。在精度上,文笔应该具有这样的功力,将你要写的对象(物质的或精神的)精确、细致地描摹出来,甚至比“照相写实主义”还要逼真。他的文字速度中隐藏着巨大的力度,他热爱“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式的语言运动。他要求的密度之外还含有疏朗的广阔天地,对于信度,黑陶不一味拘泥现实,他信奉马蒂斯的话,精确不等于真实,美的不一定像,像的不一定美。
我有幸与黑陶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敬佩他的真诚、内敛、踏实。我们时常一起出去采风、聚会,“桃花潭边踏歌声,醉翁亭里说风月”。时间一久,我们深谙彼此的品性与喜好。
上世纪90年代,我去无锡日报社看望诗人金山,谈性正浓时,金山说带我去认识一位他的好友,一位很好的年轻诗人。我跟着金山走到江南晚报社的办公室,在那里金山为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编辑,就是诗人黑陶。黑陶站起来很有礼貌地与我握手问好,我当时感受到了黑陶一双很有力量的手。中午,金山请我们一起在报社食堂吃便饭,我与黑陶相见恨晚,在食堂用餐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我们还意犹未尽。从此,我与黑陶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面对纷杂浮躁的世相,黑陶始终坚持明确的创作目标,守得住自己,耐得住寂寞。他个性率真淳朴,处事待人不卑不亢。他陶醉于对汉语词汇的罗列、堆叠,迷恋汉字堆叠出的优雅体态,在这样的堆叠中,完成了汉字形、音、义的完美和谐。黑陶用自己的文字,实践了对汉语的敬重与热爱。
记得作家韩少功有句赞美一位散文家的话,同样适用黑陶,“其积学静水深流、其性情山明水秀、其才华卓尔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