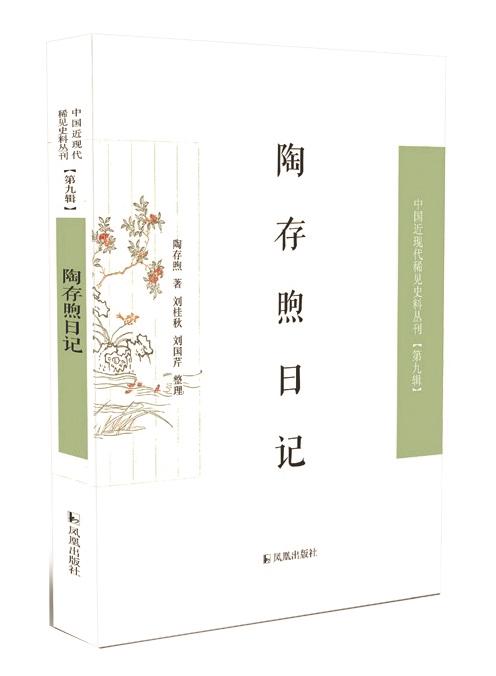□任逸飞
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历程,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哲领域的专才。其中,王蘧常、唐兰、钱仲联、蒋天枢、冯其庸等,都是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相比之下,陶存煦(1913—1933)这位因病早逝的国专第八届毕业生,却宛如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陶存煦是钱基博执教国专时赞誉有加的三名得意弟子之一,他曾评价说:“吾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得三人焉。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于韩愈文得俞生振楣。”足见其对陶存煦学识的器重。《文史通义》是清代学者章学诚(字实斋,1738—1801)的一部代表作。乾嘉年间,章学诚逆训诂考据之时流,独标文史校雠之学,提出“六经皆史”的突破性见解,这也令他的学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备受冷遇。直至民国时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下,“章学”才重新获得学界关注,相关著述大量涌现,包括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钱基博的《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等。陶存煦当时虽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但其“章学”成绩已不容小觑,据说他的国专毕业论文《章学诚学案》是一部总计五六十万字的巨著,意图全面讨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虽如今《学案》已难觅全秩,但其部分章节曾分期刊载于《国专月刊》上,使得后人能够一窥该书的体例规模。
陶存煦究竟是怎样确立自己对章学诚的研究兴趣,其“章学”基本见解又是如何形成的?由于资料的匮乏,过去人们曾一度将其简单归结为老师钱基博的启发与影响,这自然是可以言之成理的观点,但无疑也相应轻忽了陶存煦主观的选择和思考。幸运的是,近期《陶存煦日记》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国专时期陶存煦求学和治学的具体经过提供了一手资料,也为洞悉陶氏走向章学诚研究与“浙东学术”的内心隐微打开了一扇窗口。
一
陶存煦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商贾之家,从他的曾祖父陶琴士开始,陶家即以经营布店、染坊在绍兴知名,至父亲陶传祺时,更进军实业界,集资创建大明电气公司,开绍兴现代工业之先河。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陶存煦却并未承继衣钵,走经商的道路,反而以研究国学为职志,个中原因是耐人寻味的。尽管陶存煦成长的年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直至国民大革命席卷全国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陶家沿袭科举时代“贾而好儒”的逻辑,通过提升子弟的文化水准,实现商人家族融入地方士绅阶层的目标。陶存煦在《日记》中即不止一次记录父亲的教诲:“予生平有恨事数也,而子弟不能文,尤所痛恨。吾家以商起家,尔祖而外,无一人能握笔者,以是而受尽揶揄,已非一日。(1930年7月11日)”族中子弟“素不讲求文事”始终是父亲口中的一大隐痛,这也使得陶存煦的修读国学被赋予了远超一般读书求知的诉求:“汝侪有志习国学,亦所以雪吾家累年之耻,竟吾家三代之功,何乐而不可为?(1930年7月30日)”
长辈的巨大期待让陶存煦在入读无锡国专——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所以国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府时,背负了较高的自我期许,而一旦发觉实际情况与预想有落差时,他不免产生对人生道路的彷徨和困惑:“予日来睹家国现状,知翘翘予室,来日大难,非有投时利器,不足以谋自立;非有自立能力,不足以图温饱。研究举世唾弃之国学,肄业举世鄙薄之国专,深虑茫茫禹州,他日将无立足之地。(1930年4月15日)”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研习传统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国学教育在趋于一元化、标准化的教育体制中不断式微,为取得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注册立案,已有近十年办学历史的无锡国专曾不得不一再更名,并被限定为一所专科学校,饱受居处边缘之苦;更有甚者,被国专校长唐文治视为立校之本的理学学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跃成为主流学术范式的“新汉学”间似乎也是凿枘不投。这些深层次的矛盾自然都被陶存煦看在眼里,成了他1930年暑假一度打算转学投靠浙大的诱因。不过,陶存煦最终还是打消了转学的念头,修读国学以振兴家运的道德使命感乃至对本国文化的深度体认,令他不忍放弃已经开启的学术事业:“今乃知此日之我,只有在国学打出一条新路,断无舍国学以强阿时好,否则罪无可逭矣。(1930年7月23日)”
二
既然确定了“在国学打出一条新路”的志向,陶存煦接下来所要面对的便是如何梳理自身治学路径的问题,为此他走的是一条看似繁复迂远实则直接明快的道路——勤奋苦读、精进学问。据统计,在《日记》所涉及的一年半时间里,陶存煦阅读的书籍文章达到一百二十余部(篇),他严格按照自己制定的“读书日程”进行系统性的读书自修,并在《日记》中写下心得体会。此外,他的课余阅读往往能与课上所学相互衔接、紧密配合,而非泛观博览、贪多求全,这令他能够在对各类学说的沉潜往复和斟酌损益中,逐渐确定个人的学术方向。
从《日记》内容看,陶存煦对汉宋今古之学都有自己的一番独到见解。譬如,针对校长唐文治引以为傲的“宋学”,陶氏曾一再指斥其空疏之病,“气命心性,如堕迷雾”(1931年10月13日),但茹经老人以道德文章挽救世风的凛然气节却让他深受触动;而对于当时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汉学”的主流学风,陶存煦也并非简单地一概排斥,他认为胡适所谓“搜集、审定、整理”的三步学术研究功夫是值得效法的,陶氏自己编列的各类国学著述计划以及撰写的《最低限度国学入门书目》几乎都渗透着胡适的学术风格。但陶存煦从不自认是“新汉学”中人,他对胡适、顾颉刚等人持有的激进疑古思想,乃至全盘否定本国固有文化的倾向始终不能苟同。总体上,他更偏好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汉学那种“由名物训诂以通大义”的征实学风,在此基础上又能避免汉学琐碎之弊,力求致用。这一经过反思得出的治学方向,为陶存煦最终归宿于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这一更具实践性格与事功精神的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浙东学术”(又可称“浙东学派”或“浙东史学”)是一个与章学诚紧密相连的学术命题,章学诚在临终前一年的1800年完成《浙东学术》一文,构建了一个“言性命者必究于史”“讲学者必有事事”的浙东学派谱系。现在一般认为,该谱系的“人造”成分是比较浓厚的,实斋的用意或许是希望通过将自身学说组织进一个源远流长的浙东传统,以与心目中的学术劲敌戴震争夺儒学内部的话语权。
但对陶存煦来说,他进入“浙东学术”的讨论始终有其别样的关怀,那就是试图从章学诚学说甚至更大范围的“浙东学术”内部,寻找到一条能够印证自身治学路径的思想线索,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他对章学诚的研究兴趣,并不是从听讲钱基博《文史通义》课程的1930年上半年立即发生,而是经过了一番沉淀,至1931年秋才最终形成。陶存煦从浙籍学者陈训慈的文章《浙东史学管窥》获得启发,将章学诚学说乃至“浙东学术”的渊源上溯至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金华、永嘉、永康等学派):“实斋之学,其要在即器以见道,道不离于事;明文通于史,史将以经世。道不离事,永嘉学术也;史以经世,浙东史学也。(1931年11月21日)”这番发现,让陶存煦倍感振奋,他写道:“煦乡党末学,平素志趣略同先生,然不见先生书,未知心印;既读先生书,当以浙东坠绪自勉策也。(1931年11月14日)”正是在章学诚的思想中,陶存煦作为浙东人的地域认同(“乡党末学”)、个人治学路径(“平素志趣”)与研究对象(“先生书”/浙东学术)三者达成了完美统一,“章学”成了他的“生命之学”,身为浙东人的陶存煦也由此自觉担负起承接“浙东坠绪”的学术使命。
四
如今看来,陶存煦将章学诚思想与“浙东学术”的渊源追溯至南宋浙东学派的观点不免有生硬之处,但在当时确实是个极为新颖和大胆的见解。老师钱基博赞叹之余,更勉励陶存煦:“尊闻行知,发挥光大,以延此一脉,余于生有厚望焉!”若假以时日,我们当能期待陶存煦的“章学”研究能更上层楼,然而,1933年春,陶存煦在绍兴道墟乡寻访章学诚墓址后,突患脑膜炎,于同年7月18日骤然离世,年仅20岁。去世前,他自撰挽联“死生原本一理,但浙东坠绪茫茫,孰继吾业?寿夭同是有尽,顾重闱春日绵绵,莫报寸心”,深以“浙东学术”后继无人为憾,而他走向“章学”研究的一番艰辛历程与生命体悟,也随其离世而变得鲜为人知了。
陶存煦走向“浙东学术”和章学诚研究或多或少有着一些偶然的机缘,这其中有浙东的地域认同,有商人家庭的出身背景所带来的对修读传统学问的执着,自然也少不了钱基博、陈训慈等名家的启发。但最重要的或许在于,对章学诚的学术兴趣是在陶存煦读书学习的自觉行动中逐渐变得明朗的,它本身构成了陶存煦治学路径的一种内在延伸,而并非仅是各种外缘因素刺激下的产物,这也使它显得弥足珍贵。
最后必须指出,陶存煦的学术成绩与传承古代书院精神的无锡国专注意维持学生各依喜好、主动求知的宽松氛围,以及培养学生独立自学能力的教学特点是分不开的。尽管陶存煦在国专读书期间时常表达与校长唐文治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压制和阻碍,他依然能够贯彻自己的想法来探求学问。无锡国专这种以学术为重,不拘泥门户之见的优良校风是尤其值得今人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