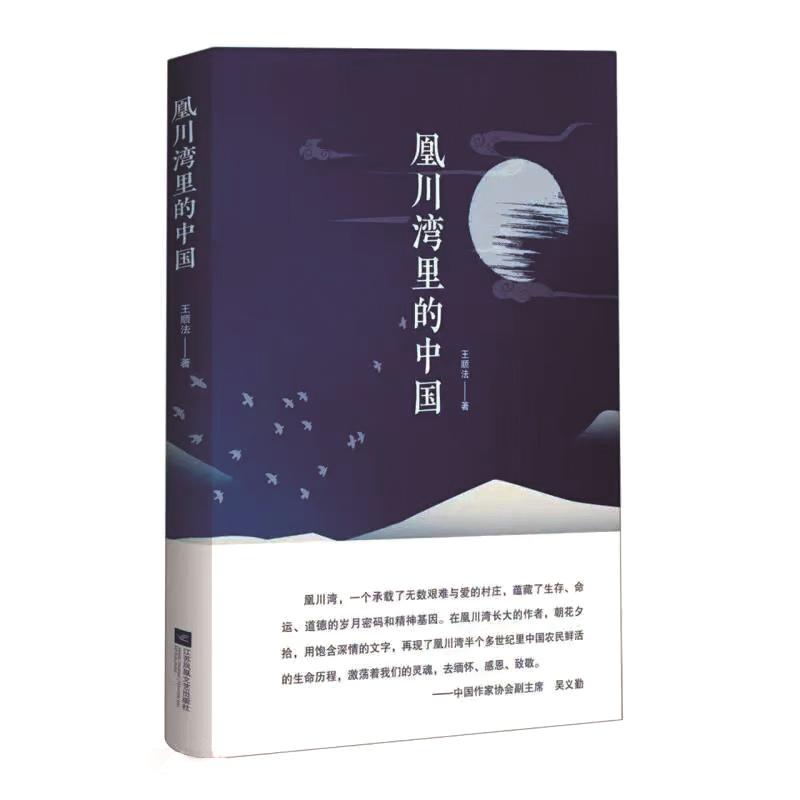□王顺法
近两年有多篇散文被杂志社当小说刊发,我颇感意外。
小说是创造性写作,属“我写”,行笔可以天马行空任意想象,而我这些作品叙说的故事,像铜钱落在青石板上叮当响,十足的“写我”,纯属散文写作范畴。
仔细想来,编辑“误解”有多方面因素。
我投稿时从不标明作品类型或许是一个原因。我自认为不需要。编辑既端了这饭碗,作者就要相信他们的“法眼”,看得出这是碗白米饭还是牛肉拉面,自己该做的,是让他们读了文章开头就想赶紧看后文。
其实,真正这样做,是因为我在写完一些文本,交稿前再审视时,自己心里也犯了迷糊:这些文章不就是小说?
我喜欢写小说,仅在2018年至2020年间,就在《中国作家》《钟山》两刊物发表了3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作强调塑造人物,偏我写出一些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真实人物,他们个性分明,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现在一个个鲜活地走到我面前。作品特征,符合小说的范畴。
再想,是了,我是用文字还原了人世间曾经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场景,那些很多在这个世界已永远消失的人与事,现代人多感陌生,过来人看过觉得亲切,这样的文章就有了可读性,有了深度、温度,杂志将其作为小说发表就有了理由。
文学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我亦不例外。
时代关系,儿时的我自卑刻在骨子里,凡事小心翼翼。这种性格的养成,使我的写作习惯也变得常人难以理喻:凌晨3点起床写作,天亮即收工。为防偶尔收不住手,天大亮了还在写,我会将窗帘整治得密不透光,如此一来,哪怕外边早已阳光灿烂,房里依然如深夜般宁静,我依然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将早已化成轻风的往事、故人,用心召唤回来,在我用文字精心构筑的舞台,上演一幕幕或壮烈或凄美或欢快的剧目。
是的,我的写作习惯就是如此。我知道自己的短板,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初中生,56岁开始学写作,不真正用心去写,想要在传统文学读物亮一个相,难如登天。
好读善悟帮了我的忙。写作不久,我就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写作“独门绝技”:用文字演戏,让读者落到我文章的第一眼,就会见到为故事服务的布景、道具,再由这些布景、道具牵动他们的心进入文本。
我刊发在《北京文学》2023年第五期的中篇小说《美男子》这样开篇:“村西小河边光秃秃的老杨树梢,一只斗笠大的鸟巢随风摇晃。寒风刺骨,雪花星星点点飘落在苏南原野。全队社员在清理着麦垄沟泥,仿佛怕惹着鸟巢中的乌鸦作祟,都闷头忙着各自手中的活计。不过,时不时的,总有人面朝山道的东头,滴溜溜转着眼珠子……”
杂志的导读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温暖而悲凉的故事,关于一个人与一座村庄的默契与信任,还有一段隐秘无私的情感。一个贩卖旧衣物的小贩,半边脸看上去是美男子,而另一半呢?”
该作品所讲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个事件完全真实,我不过是用演戏的手法,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开篇的画面,我把叙说故事的大幕拉开,读者马上就会知道,我便是“滴溜溜转着眼珠子”,看着山道东头那群人中的一个。我演出了想象中的自己,也用观众的目光,写出了那个时间段里,我眼睛见着的故事里的一众男女。
因为是真人真事,我写来毫不费力。又因是“演戏”,我十分享受这次灵魂的美好旅途。许是故事题材与表述别具一格,该作品发表后即由《海外文摘》转载。
我的写作是野路子。每个写作者的写作方法、题材都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爱上写与被人、被工作逼着去写是两回事。如兴趣使然,写作的动力会让你不断探索文本的表现方式,也会让你感受到写作过程的美好,成功的作品则会如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孩子,给你终身安慰。
《春叔》发表于《安徽文学》2024年第二期,作品内容几乎就是我与妻子相恋的日记,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故事。这种最普通不过的人生经历,根本不符合小说写作题材“出新出奇”的要求,而我只是用了“演戏”这一“土方子”叙说故事,《小说选刊》转载时,就给予“春水春叔,春情春事,春风十里,不如有个春叔你!《春叔》跳宕,幽默,深情,活泼,过去年代的保媒拉纤故事,一读起来就上瘾……”朗朗数百字的赞美之辞。
其实,文学创作就如春回大地,在这万花园里,无论花儿长在何处,扎根什么土壤,花色是红是黄,味道或臭或香,总是大自然的一分子,鲜活的生命总会牵引欣赏者的目光。我相信自己写作用的“土方子”,“有什么食材做什么菜”,写完,不管编辑去定性为小说、散文,还是什么非虚构,只要作品能对上读者的胃口就好,就会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