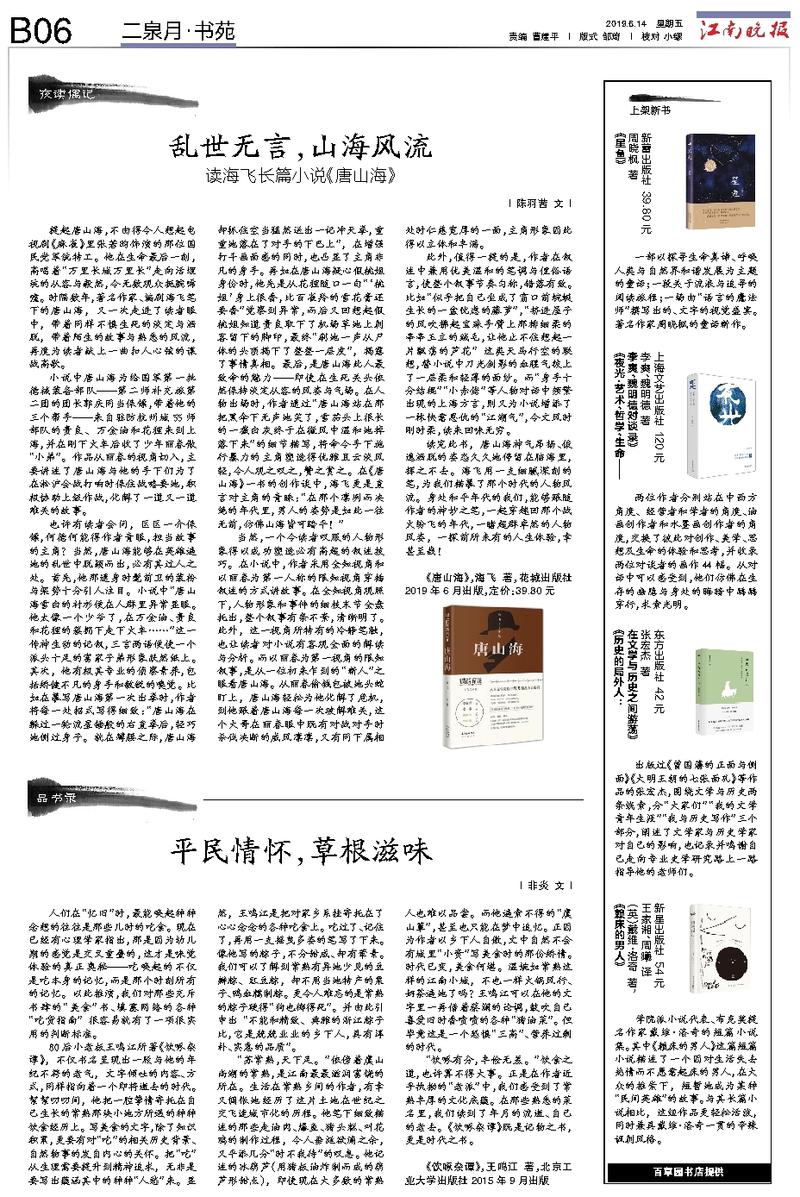| 非炎 文 |
人们在“忆旧”时,最能唤起种种念想的往往是那些儿时的吃食。现在已经有心理学家指出,那是因为幼儿期的感觉是交叉重叠的,这才是味觉体验的真正奥秘——吃唤起的不仅是吃本身的记忆,而是那个时刻所有的记忆。以此推演,我们对那些充斥书肆的“美食”书、填塞网络的各种“吃货指南”很容易就有了一项很实用的判断标准。
80后小老板王鸣江所著《饮啄杂谭》,不仅书名呈现出一股与他的年纪不符的老气,文字倾吐的内容、方式,同样指向着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絮絮叨叨间,他把一腔挚情寄托在自己生长的常熟那块小地方所遇的种种饮食经历上。写美食的文字,除了知识积累,更要有对“吃”的相关历史背景、自然物事的发自内心的关怀。把“吃”从生理需要提升到精神追求,无非是要写出蕴涵其中的种种“人愁”来。显然,王鸣江是把对家乡系挂寄托在了心心念念的各种吃食上。吃过了、记住了,再用一支摇曳多姿的笔写了下来。像他写的粽子,不分甜咸、却有荤素。我们可以了解到常熟有异地少见的豆瓣粽、豇豆粽,却不用当地特产的栗子、鸭血糯制粽。更令人难忘的是常熟的粽子硬得“狗也掷得死”。并由此引申出“不能和精致、典雅的浙江粽子比,它是兢兢业业的乡下人,具有淳朴、实惠的品质”。
“苏常熟,天下足。”依傍着虞山尚湖的常熟,是江南最最滋润富饶的所在。生活在常熟乡间的作者,有幸又惆怅地经历了这片土地在世纪之交飞速城市化的历程。他笔下细致描述的那些走油肉、爆鱼、猪头糕、叫花鸡的制作过程,令人垂涎欲滴之余,又平添几分“时不我待”的叹息。他记述的冰葫芦(用猪板油炸制而成的葫芦形甜点),即使现在大多数的常熟人也难以品尝。而他遍索不得的“虞山蕈”,甚至也只能在梦中追忆。正因为作者以乡下人自傲,文中自然不会有城里“小资”写美食时的那份矫情。时代已变,美食何堪。温婉如常熟这样的江南小城,不也一样火锅风行、奶茶遍地了吗?王鸣江可以在他的文字里一再借着蔡澜的论调,鼓吹自己喜爱旧时香喷喷的各种“猪油菜”。但毕竟这是一个恐惧“三高”、营养过剩的时代。
“饮啄有分,丰俭无差。”饮食之道,也许算不得大事。正是在作者近乎执拗的“老派”中,我们感受到了常熟丰厚的文化底蕴。在那些熟悉的菜名里,我们读到了年月的流逝、自己的老去。《饮啄杂谭》既是记物之书,更是时代之书。
《饮啄杂谭》,王鸣江 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