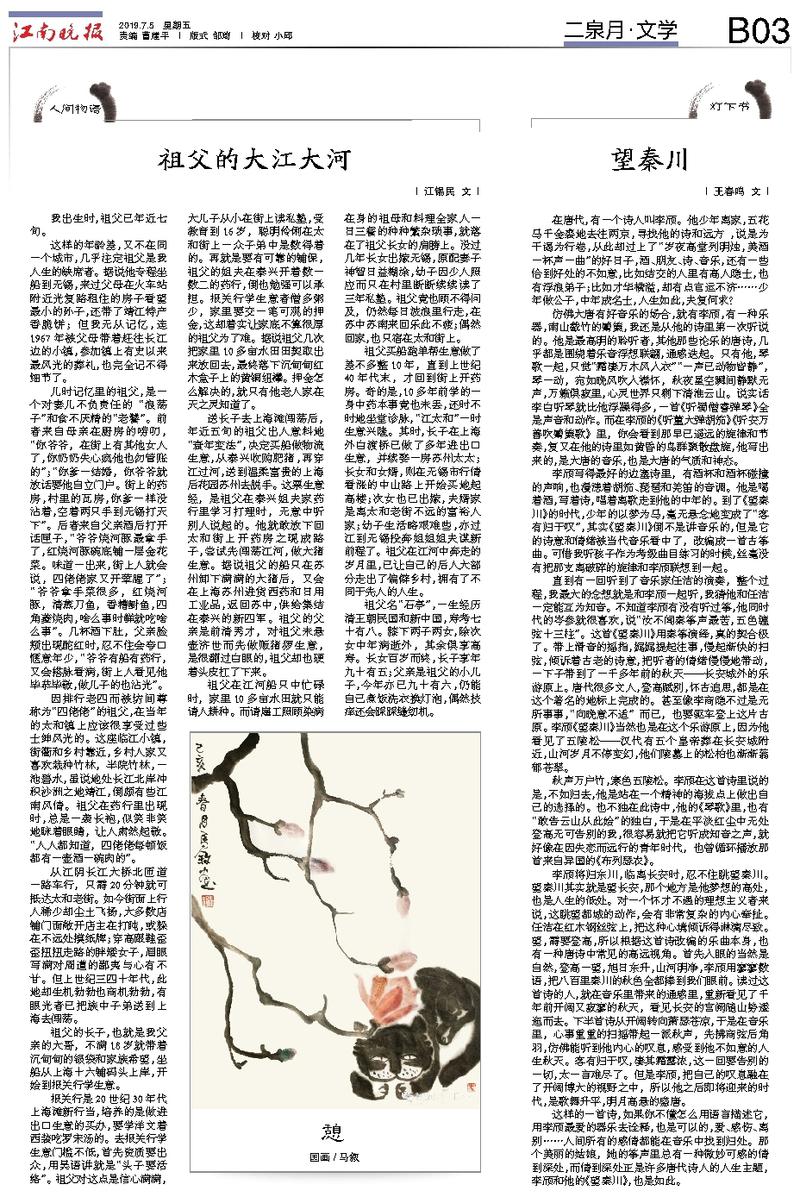| 江锡民 文 |
我出生时,祖父已年近七旬。
这样的年龄差,又不在同一个城市,几乎注定祖父是我人生的缺席者。据说他专程坐船到无锡,来过父母在火车站附近光复路租住的房子看望最小的孙子,还带了靖江特产香脆饼;但我无从记忆,连1967年被父母带着赶往长江边的小镇,参加镇上有史以来最风光的葬礼,也完全记不得细节了。
儿时记忆里的祖父,是一个对妻儿不负责任的“浪荡子”和食不厌精的“老饕”。前者来自母亲在厨房的唠叨,“你爷爷,在街上有其他女人了,你奶奶失心疯他也勿管账的”;“你爹一结婚,你爷爷就放话要他自立门户。街上的药房,村里的瓦房,你爹一样没沾着,空着两只手到无锡打天下”。后者来自父亲酒后打开话匣子,“爷爷烧河豚最拿手了,红烧河豚碗底铺一层金花菜。味道一出来,街上人就会说,四佬佬家又开荤腥了”;“爷爷拿手菜很多,红烧河豚,清蒸刀鱼,香糟鲥鱼,四角菱烧肉,啥么事时鲜就吃啥么事”。几杯酒下肚,父亲脸颊出现酡红时,忍不住会夸口惬意年少,“爷爷有船有药行,又会搭脉看病,街上人看见他毕恭毕敬,做儿子的也沾光”。
因排行老四而被坊间尊称为“四佬佬”的祖父,在当年的太和镇上应该很享受过些士绅风光的。这座临江小镇,街衢和乡村靠近,乡村人家又喜欢栽种竹林,半院竹林,一池碧水,虽说地处长江北岸冲积沙洲之地靖江,倒颇有些江南风情。祖父在药行里出现时,总是一袭长袍,似笑非笑地眯着眼睛,让人肃然起敬。“人人都知道,四佬佬每顿饭都有一壶酒一碗肉的”。
从江阴长江大桥北匝道一路车行,只需20分钟就可抵达太和老街。如今街面上行人稀少却尘土飞扬,大多数店铺门面敞开店主在打盹,或躲在不远处摸纸牌;穿高跟鞋歪歪扭扭走路的胖矮女子,眉眼写满对周遭的鄙夷与心有不甘。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此地却生机勃勃也商机勃勃,有眼光者已把族中子弟送到上海去闯荡。
祖父的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大哥,不满18岁就带着沉甸甸的银袋和家族希望,坐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开始到报关行学生意。
报关行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新行当,培养的是做进出口生意的买办,要学洋文着西装吃罗宋汤的。去报关行学生意门槛不低,首先资质要出众,用吴语讲就是“头子要活络”。祖父对这点是信心满满,大儿子从小在街上读私塾,受教育到16岁,聪明伶俐在太和街上一众子弟中是数得着的。再就是要有可靠的铺保,祖父的姐夫在泰兴开着数一数二的药行,倒也勉强可以承担。报关行学生意者僧多粥少,家里要交一笔可观的押金,这却着实让家底不算很厚的祖父为了难。据说祖父几次把家里10多亩水田田契取出来放回去,最终落下沉甸甸红木盒子上的黄铜纽襻。押金怎么解决的,就只有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知道了。
送长子去上海滩闯荡后,年近五旬的祖父出人意料地“衰年变法”,决定买船做物流生意,从泰兴收购肥猪,再穿江过河,送到温柔富贵的上海后花园苏州去脱手。这票生意经,是祖父在泰兴姐夫家药行里学习打理时,无意中听别人说起的。他就敢放下回太和街上开药房之现成路子,尝试先闯荡江河,做大猪生意。据说祖父的船只在苏州卸下满满的大猪后,又会在上海苏州进货西药和日用工业品,返回苏中,供给集结在泰兴的新四军。祖父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对祖父未悬壶济世而先做贩猪猡生意,是很翻过白眼的,祖父却也硬着头皮扛了下来。
祖父在江河船只中忙碌时,家里10多亩水田就只能请人耕种。而请雇工照顾染病在身的祖母和料理全家人一日三餐的种种繁杂琐事,就落在了祖父长女的肩膀上。没过几年长女出嫁无锡,原配妻子神智日益糊涂,幼子因少人照应而只在村里断断续续读了三年私塾。祖父竟也顾不得问及,仍然每日波浪里行走,在苏中苏南来回乐此不疲;偶然回家,也只宿在太和街上。
祖父买船跑单帮生意做了差不多整10年,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才回到街上开药房。奇的是,10多年前学的一身中药本事竟也未丢,还时不时地坐堂诊脉,“江太和”一时生意兴隆。其时,长子在上海外白渡桥已做了多年进出口生意,并续娶一房苏州太太;长女和女婿,则在无锡市行情看涨的中山路上开始买地起高楼;次女也已出嫁,夫婿家是离太和老街不远的富裕人家;幼子生活略艰难些,亦过江到无锡投奔姐姐姐夫谋新前程了。祖父在江河中奔走的岁月里,已让自己的后人大部分走出了偏僻乡村,拥有了不同于先人的人生。
祖父名“石亭”,一生经历清王朝民国和新中国,寿考七十有八。膝下两子两女,除次女中年病逝外,其余俱享高寿。长女百岁而终,长子享年九十有五;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今年亦已九十有六,仍能自己煮饭洗衣换灯泡,偶然技痒还会踩踩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