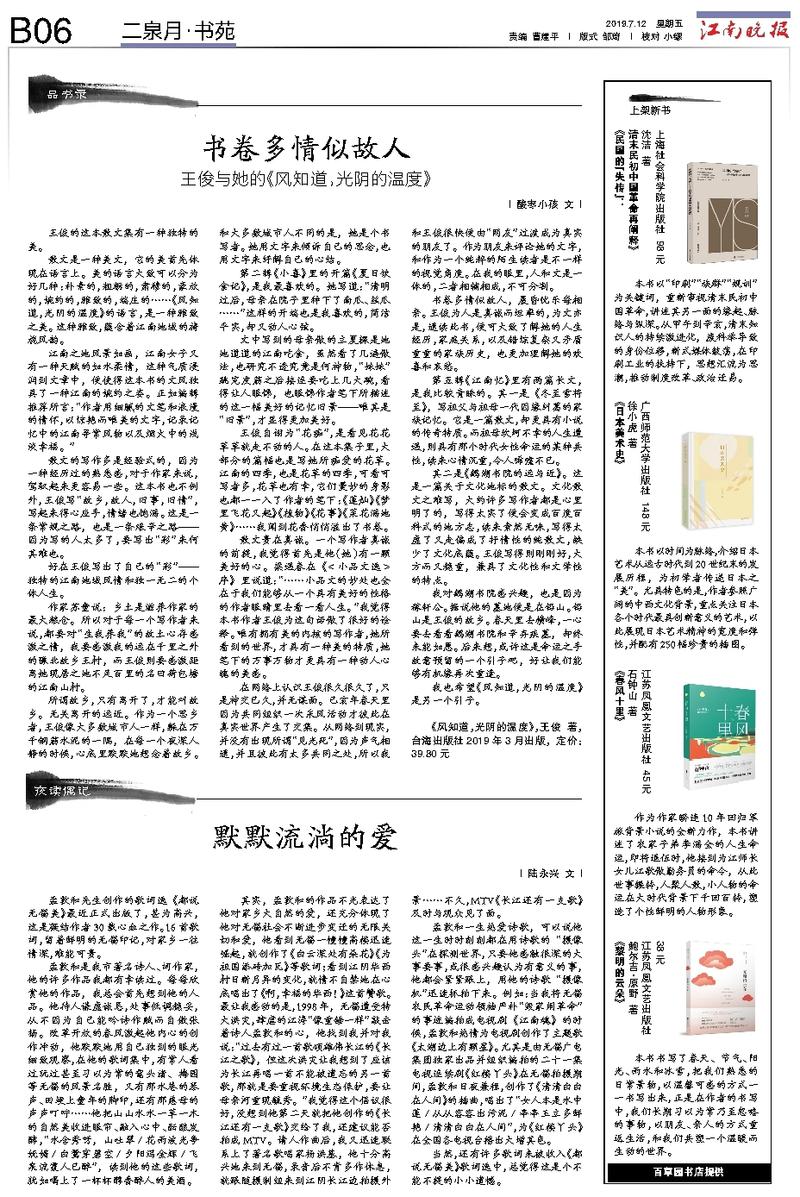| 酸枣小孩 文 |
王俊的这本散文集有一种独特的美。
散文是一种美文,它的美首先体现在语言上。美的语言大致可以分为好几种:朴素的,粗粝的,肃穆的,豪放的,婉约的,雅致的,端庄的……《风知道,光阴的温度》的语言,是一种雅致之美。这种雅致,蕴含着江南地域的旖旎风韵。
江南之地风景如画,江南女子又有一种天赋的如水柔情,这种气质浸润到文章中,便使得这本书的文风独具了一种江南的婉约之姿。正如编辑推荐所言:“作者用细腻的文笔和浪漫的情怀,以惊艳而唯美的文字,记录记忆中的江南寻常风物以及烟火中的浅淡幸福。”
散文的写作多是经验式的,因为一种经历过的熟悉感,对于作家来说,驾驭起来更容易一些。这本书也不例外,王俊写“故乡,故人,旧事,旧情”,写起来得心应手,情绪也饱满。这是一条常规之路,也是一条艰辛之路——因为写的人太多了,要写出“彩”来何其难也。
好在王俊写出了自己的“彩”——独特的江南地域风情和独一无二的个体人生。
作家苏童说:乡土是滋养作家的最大粮仓。所以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来说,都要对“生我养我”的故土心存感激之情,我要感激我的远在千里之外的豫北故乡王村,而王俊则要感激距离她现居之地不足百里的名曰荷包塘的江南山村。
所谓故乡,只有离开了,才能叫故乡。无关离开的远近。作为一个思乡者,王俊像大多数城市人一样,躲在万千钢筋水泥的一隅,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心底里默默地想念着故乡。和大多数城市人不同的是,她是个书写者。她用文字来倾诉自己的思念,也用文字来纾解自己的心结。
第二辑《小喜》里的开篇《夏日饮食记》,是我最喜欢的。她写道:“清明过后,母亲在院子里种下了南瓜、丝瓜……”这样的开端也是我喜欢的,简洁平实,却又动人心弦。
文中写到的母亲做的立夏粿是地地道道的江南吃食,虽然看了几遍做法,也研究不透究竟是何神物,“妹妹”跳完皮筋之后接连要吃上几大碗,看得让人眼馋,也眼馋作者笔下所描述的这一幅美好的记忆旧景——唯其是“旧景”,才显得更加美好。
王俊自诩为“花痴”,是看见花花草草就走不动的人。在这本集子里,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写她所痴爱的花草。江南的四季,也是花草的四季,可看可写者多,花草也有幸,它们曼妙的身影也都一一入了作者的笔下:《莲灿》《梦里飞花又起》《植物》《花事》《菜花满地黄》……我闻到花香悄悄溢出了书卷。
散文贵在真诚。一个写作者真诚的前提,我觉得首先是他(她)有一颗美好的心。梁遇春在《<小品文选>序》里说道:“……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我觉得本书作者王俊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唯有拥有美的内核的写作者,她所看到的世界,才具有一种美的特质,她笔下的万事万物才更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感。
在网络上认识王俊很久很久了,只是神交已久,并无谋面。己亥年春天里因为共同组织一次采风活动才彼此在真实世界产生了交集。从网络到现实,并没有出现所谓“见光死”,因为声气相通,并且彼此有太多共同之处,所以我和王俊很快便由“网友”过渡成为真实的朋友了。作为朋友来评论她的文字,和作为一个纯粹的陌生读者是不一样的视觉角度。在我的眼里,人和文是一体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王俊为人是真诚而坦率的,为文亦是,通读此书,便可大致了解她的人生经历,家庭关系,以及错综复杂又矛盾重重的家族历史,也更加理解她的欢喜和哀愁。
第五辑《江南忆》里有两篇长文,是我比较青睐的。其一是《冬至雪将至》,写祖父与祖母一代因缘纠葛的家族记忆。它是一篇散文,却更具有小说的传奇特质。而祖母坎坷不幸的人生遭遇,则具有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某种共性,读来心情沉重,令人唏嘘不已。
其二是《鹅湖书院的远与近》。这是一篇关于文化地标的散文。文化散文之难写,大约许多写作者都是心里明了的,写得太实了便会变成百度百科式的地方志,读来索然无味,写得太虚了又走偏成了抒情性的纯散文,缺少了文化底蕴。王俊写得则刚刚好,大方而又稳重,兼具了文化性和文学性的特点。
我对鹅湖书院感兴趣,也是因为稼轩公。据说他的墓地便是在铅山。铅山是王俊的故乡。春天里去横峰,一心要去看看鹅湖书院和辛弃疾墓,却终未能如愿。后来想,或许这是命运之手故意预留的一个引子吧,好让我们能够有机缘再次重逢。
我也希望《风知道,光阴的温度》是另一个引子。
《风知道,光阴的温度》,王俊 著,台海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