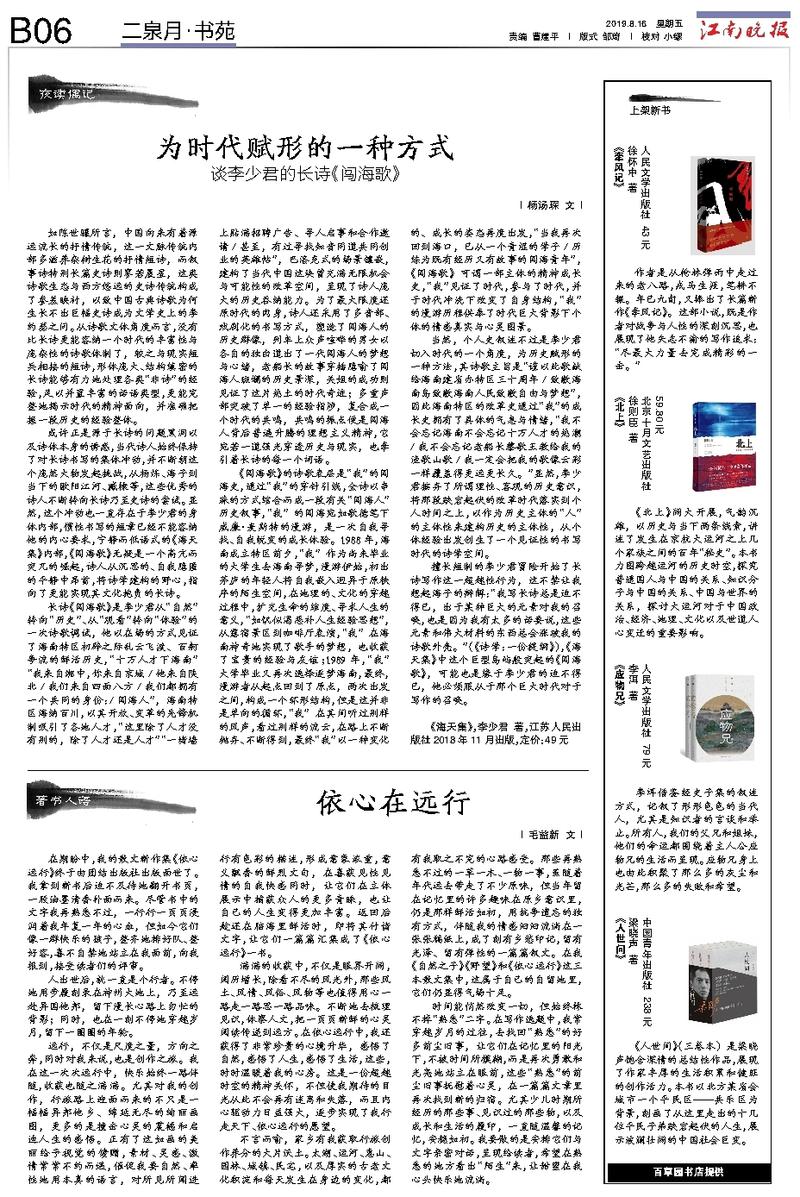| 杨汤琛 文 |
如陈世骧所言,中国向来有着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这一文脉传统内部多滋养杂树生花的抒情短诗,而叙事诗特别长篇史诗则寥若晨星,这类诗歌生态与西方悠远的史诗传统构成了参差映衬,以致中国古典诗歌为何生长不出巨幅史诗成为文学史上的李约瑟之问。从诗歌文体角度而言,没有比长诗更能容纳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与庞杂性的诗歌体制了,较之与现实短兵相接的短诗,形体庞大、结构缜密的长诗能够有力地处理各类“非诗”的经验,足以并置丰富的话语类型,更能完整地揭示时代的精神面向,并准确把握一段历史的经验整体。
或许正是源于长诗的问题黑洞以及诗体本身的诱惑,当代诗人始终保持了对长诗书写的集体冲动,并不断朝这个庞然大物发起挑战,从杨炼、海子到当下的欧阳江河、臧棣等,这些优秀的诗人不断转向长诗乃至史诗的尝试。显然,这个冲动也一直存在于李少君的身体内部,惯性书写的短章已经不能容纳他的内心要求,宁静而低语式的《海天集》内部,《闯海歌》无疑是一个高亢而突兀的崛起,诗人从沉思的、自我隐匿的平静中昂首,将诗学建构的野心,指向了更能实现其文化抱负的长诗。
长诗《闯海歌》是李少君从“自然”转向“历史”、从“观看”转向“体验”的一次诗歌调试,他以在场的方式见证了海南特区初辟之际乱云飞渡、百舸争流的鲜活历史,“十万人才下海南” “我来自湘中,你来自京城/他来自陕北/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闯海人”,海南特区海纳百川,以其开放、变革的先锋机制吸引了各地人才,“这里除了人才没有别的,除了人才还是人才”“一堵墙上贴满招聘广告、寻人启事和合作邀请/甚至,有过寻找知音同道共同创业的英雄帖”,巴洛克式的场景镶嵌,建构了当代中国这块曾充满无限机会与可能性的改革空间,呈现了诗人庞大的历史吞纳能力。为了最大限度还原时代的肉身,诗人还采用了多音部、戏剧化的书写方式,塑造了闯海人的历史群像,列车上众声喧哗的男女以各自的独白道出了一代闯海人的梦想与心绪,老船长的故事穿插隐喻了闯海人斑斓的历史景深,关姐的成功则见证了这片热土的时代奇迹;多重声部突破了单一的经验指涉,复合成一个时代的共鸣,共鸣的振点便是闯海人背后普遍升腾的理想主义精神,它宛若一道强光穿透历史与现实,也牵引着长诗的每一个词语。
《闯海歌》的诗歌表层是“我”的闯海史,通过“我”的穿针引线,全诗以串珠的方式绾合而成一段有关“闯海人”历史叙事,“我”的闯海宛如歌德笔下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是一次自我寻找、自我蜕变的成长体验。1988年,海南成立特区前夕,“我”作为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去海南寻梦,漫游伊始,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将自我嵌入迥异于原秩序的陌生空间,在地理的、文化的穿越过程中,扩充生命的维度、寻求人生的意义,“如饥似渴恶补人生经验思想”,从露宿景区到咖啡厅表演,“我”在海南神奇地实现了歌手的梦想,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与友谊;1989年,“我”大学毕业又再次选择逐梦海南,最终,漫游者从起点回到了原点,两次出发之间,构成一个环形结构,但是这并非是单向的循环,“我”在其间听过别样的风声,看过别样的流云,在路上不断抛弃、不断得到,最终“我”以一种变化的、成长的姿态再度出发,“当我再次回到海口,已从一个青涩的学子/历练为既有经历又有故事的闯海青年”,《闯海歌》可谓一部主体的精神成长史,“我”见证了时代,参与了时代,并于时代冲洗下改变了自身结构,“我”的漫游历程供奉了时代巨大背影下个体的情感真实与心灵图景。
当然,个人史叙述不过是李少君切入时代的一个角度,为历史赋形的一种方法,其诗歌主旨是“谨以此歌献给海南建省办特区三十周年/致敬海南岛致敬海南人民致敬自由与梦想”,因此海南特区的改革史通过“我”的成长史拥有了具体的气息与情绪,“我不会忘记海南不会忘记十万人才的热潮/我不会忘记老船长黎歌王教给我的渔歌山歌/我一定会把我的歌像云彩一样覆盖得更远更长久。”显然,李少君摈弃了所谓理性、客观的历史意识,将那段跌宕起伏的改革时代落实到个人时间之上,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主体性来建构历史的主体性,从个体经验出发创生了一个见证性的书写时代的诗学空间。
擅长短制的李少君冒险开始了长诗写作这一超越性行为,这不禁让我想起海子的辩解:“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诗学:一份提纲》),《海天集》中这个巨型岛屿般突起的《闯海歌》,可能也是缘于李少君的迫不得已,他必须服从于那个巨大时代对于写作的召唤。
《海天集》,李少君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定价: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