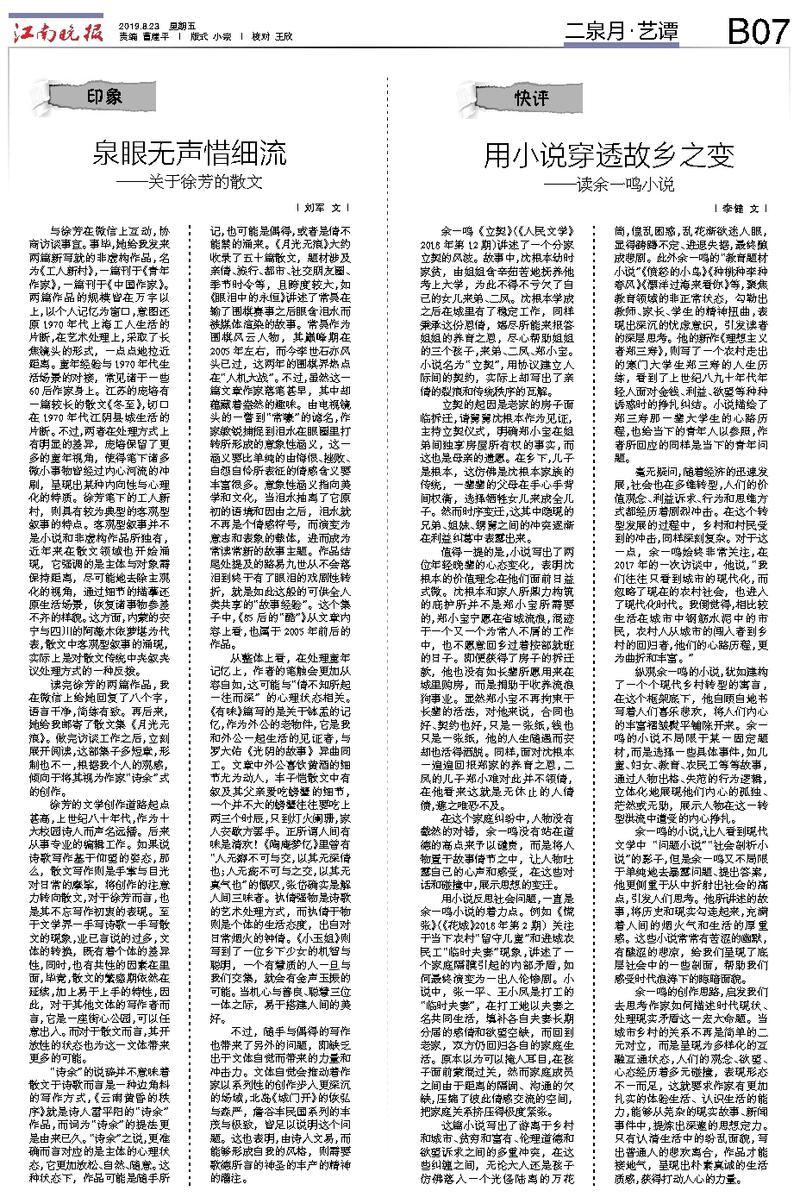| 李健 文 |
余一鸣《立契》(《人民文学》2018年第12期)讲述了一个分家立契的风波。故事中,沈根本幼时家贫,由姐姐含辛茹苦地抚养他考上大学,为此不得不亏欠了自己的女儿来弟、二凤。沈根本学成之后在城里有了稳定工作,同样秉承这份恩情,竭尽所能来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尽心帮助姐姐的三个孩子,来弟、二凤、郑小宝。小说名为“立契”,用协议建立人际间的契约,实际上却写出了亲情的裂痕和传统秩序的瓦解。
立契的起因是老家的房子面临拆迁,请舅舅沈根本作为见证,主持立契仪式,明确郑小宝在姐弟间独享房屋所有权的事实,而这也是母亲的遗愿。在乡下,儿子是根本,这仿佛是沈根本家族的传统,一辈辈的父母在手心手背间权衡,选择牺牲女儿来成全儿子。然而时序变迁,这其中隐现的兄弟、姐妹、甥舅之间的冲突逐渐在利益纠葛中表露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写出了两位年轻晚辈的心态变化,表明沈根本的价值理念在他们面前日益式微。沈根本和家人所鼎力构筑的庇护所并不是郑小宝所需要的,郑小宝宁愿在省城流浪,混迹于一个又一个为常人不屑的工作中,也不愿意回乡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即便获得了房子的拆迁款,他也没有如长辈所愿用来在城里购房,而是捐助于收养流浪狗事业。显然郑小宝不再拘束于长辈的活法,对他来说,合同也好、契约也好,只是一张纸,钱也只是一张纸,他的人生随遇而安却也活得洒脱。同样,面对沈根本一遍遍回报郑家的养育之恩,二凤的儿子郑小难对此并不领情,在他看来这就是无休止的人情债,避之唯恐不及。
在这个家庭纠纷中,人物没有截然的对错,余一鸣没有站在道德的高点来予以谴责,而是将人物置于故事情节之中,让人物吐露自己的心声和感受,在这些对话和碰撞中,展示思想的变迁。
用小说反思社会问题,一直是余一鸣小说的着力点。例如《慌张》(《花城》2018年第2期)关注于当下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讲述了一个家庭隔膜引起的内部矛盾,如何最终演变为一出人伦惨剧。小说中,张一平、王小凤是打工的“临时夫妻”,在打工地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填补各自夫妻长期分居的感情和欲望空缺,而回到老家,双方仍回归各自的家庭生活。原本以为可以掩人耳目,在孩子面前蒙混过关,然而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距离的隔阂、沟通的欠缺,压缩了彼此情感交流的空间,把家庭关系挤压得极度紧张。
这篇小说写出了游离于乡村和城市、贫穷和富有、伦理道德和欲望诉求之间的多重冲突,在这些纠缠之间,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仿佛落入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惶乱困惑,乱花渐欲迷人眼,显得踌躇不定、进退失据,最终酿成悲剧。此外余一鸣的“教育题材小说”《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漂洋过海来看你》等,聚焦教育领域的非正常状态,勾勒出教师、家长、学生的精神扭曲,表现出深沉的忧虑意识,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他的新作《理想主义者郑三寿》,则写了一个农村走出的寒门大学生郑三寿的人生历练,看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人面对金钱、利益、欲望等种种诱惑时的挣扎纠结。小说描绘了郑三寿那一辈大学生的心路历程,也给当下的青年人以参照,作者所回应的同样是当下的青年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也在多维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行为和思维方式都经历着剧烈冲击。在这个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和村民受到的冲击,同样深刻复杂。对于这一点,余一鸣始终非常关注,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们往往只看到城市的现代化,而忽略了现在的农村社会,也进入了现代化时代。我倒觉得,相比较生活在城市中钢筋水泥中的市民,农村人从城市的闯入者到乡村的回归者,他们的心路历程,更为曲折和丰富。”
纵观余一鸣的小说,犹如建构了一个个现代乡村转型的寓言,在这个框架底下,他自顾自地书写着人们喜乐悲欢,将人们内心的丰富褶皱熨平铺陈开来。余一鸣的小说不局限于某一固定题材,而是选择一些具体事件,如儿童、妇女、教育、农民工等等故事,通过人物出格、失范的行为逻辑,立体化地展现他们内心的孤独、茫然或无助,展示人物在这一转型洪流中遭受的内心挣扎。
余一鸣的小说,让人看到现代文学中“问题小说”“社会剖析小说”的影子,但是余一鸣又不局限于单纯地去暴露问题、提出答案,他更侧重于从中折射出社会的痛点,引发人们思考。他所讲述的故事,将历史和现实勾连起来,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和生活的厚重感。这些小说常常有苦涩的幽默,有酸涩的悲凉,给我们呈现了底层社会中的一些剖面,帮助我们感受时代浪涛下的晦暗面貌。
余一鸣的创作思路,启发我们去思考作家如何描述时代现状、处理现实矛盾这一宏大命题。当城市乡村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为多样化的互融互通状态,人们的观念、欲望、心态经历着多元碰撞,表现形态不一而足,这就要求作家有更加扎实的体验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能够从芜杂的现实故事、新闻事件中,提炼出深邃的思想定力。只有认清生活中的纷乱面貌,写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作品才能接地气,呈现出朴素真诚的生活质感,获得打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