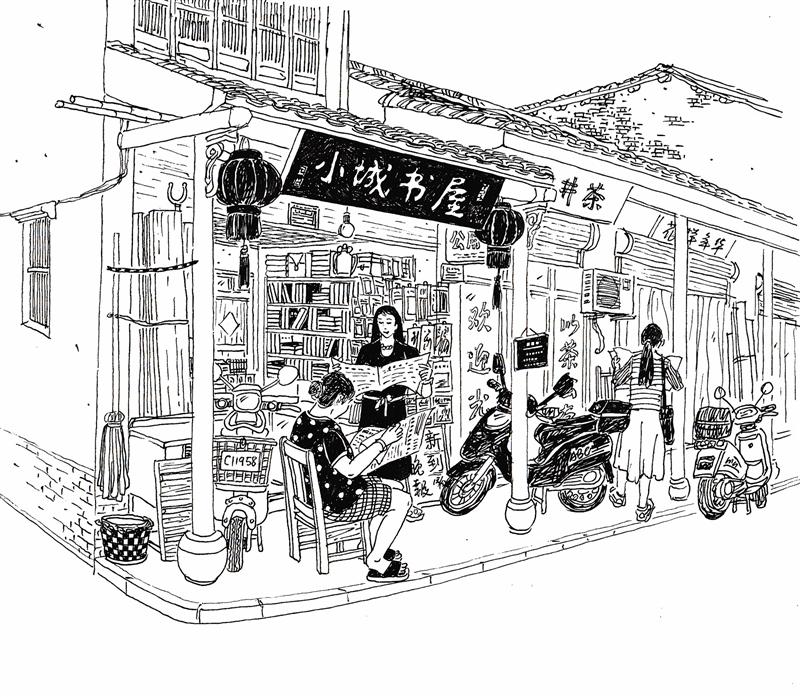| 薛明 文 |
小时候的寒假、暑假,我都要帮做散工的母亲送篮。母亲在前竹场巷的运河码头上(离莲蓉桥约50多米)帮人洗菜、淘米、汰衣裳。洗净了,我就把菜篮、米篮、衣裳篮送到各家各户;再把新的一批菜篮、米篮、衣裳篮送到面朝运河的母亲背后。
河滩上尽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篮。寒冬腊月,我小手冻得通红,十个手指就像十根小小的胡萝卜。坐在冰冷的石阶上,寒冷的风铁青着脸,好像下决心要把我冻成石阶的一部分。
母亲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劳作,不时挥动棒槌,把篮中的衣裤取出来,放在石阶上槌打,清除衣物中间的肥皂水。如果洗得不清,衣物留存肥皂的气味,主人是要皱眉头的。
母亲洗的米与菜,洗的衣物,向来很干净。她总是忍着冰冷的河水刺骨的冷,忍着十根手指头被运河水撕咬。偶尔,才听到母亲发出“嗤、嗤、嗤” 的呼声。母亲能吃大苦,她的呼喊声总是压得很低。她很冷哇,我知道。我坐在石阶上都冻得发抖,母亲的双手要浸到冰冷的水里,洗、洗、洗,不停地洗,每月才能到各家领到两元、三元。一天不做,一天不活。没钱,就无法去买柴米油盐。
没有油,就没有灯火,晚上我就不能做作业。五年级前,我家里点的还是“油盏头”。就是放些油,里边放两根灯草点燃着发光。那么一点明亮,远远不够我挥霍,我要看大量的书。我的眼睛逐渐近视,额前头发总是烧焦的。好在那时的人都不懂得美观,也不知美发是什么样子。
母亲比我冷,但她总说我坐在石阶上冷。
我坐在石阶上。码头旁边是一家弹棉花店,兼营毛竹生意。所以,从中山路走来,过莲蓉桥向右转、沿运河的那条巷名“前竹场巷”。离运河稍远与“前竹场巷”平行的一条巷,名“后竹场巷”。棉花店里弹着棉花,丝弦在弹棉花槌子的敲拨下,发出“当当当”的响声,是非常好听的。小时候,我总是当它音乐听。
运河里摇着各式各样的船,发出“嗯得罗”“嗯得罗”的声音。那时我很佩服摇船的,想:长大了学会摇船,摇各式各样的船,到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各条河浜里,都去游游。
“咯咯咯咯”,有时也有小火轮开过,一不小心,大浪头就会卷去衣物、棒槌,那就要快抢。卷走了人家的衣物,可要赔的。那时我就冲下去,帮妈按捺住石阶上的衣物。常常会很惊险。有一次,棒槌卷走了,母亲上岸追了好多远,好心的船家用篙子帮我们拨到另一个码头上,我守着衣物,等了好久,母亲才拿着棒槌回来。
但是,那个年代的小火轮毕竟不多。大多时候,我总是安静地坐在母亲背后,做我学摇船的梦。
有时,母亲回过头,见我坐在石阶上双手抱肩直发抖。她走上三级,摸摸我的小手。我心里暖烘烘的,身边好像又多了一个太阳。
母亲脱下围巾,把我的手包起来。然后,她转身走下三级,又把双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洗、洗、洗……洗不完的菜、米、衣。
这样,毎天要洗整整一个上午。我起身送篮时,再悄悄把围巾披到母亲的颈项上。
陶家弄,前、后竹场巷,泗堡弄,大河池,我串家走户地送篮……
现在,这一带建起幢幢高楼,建成“中大颐和”小区。
那里,曾经有我住过的破烂小屋,是我送着各式各样的篮慢慢成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