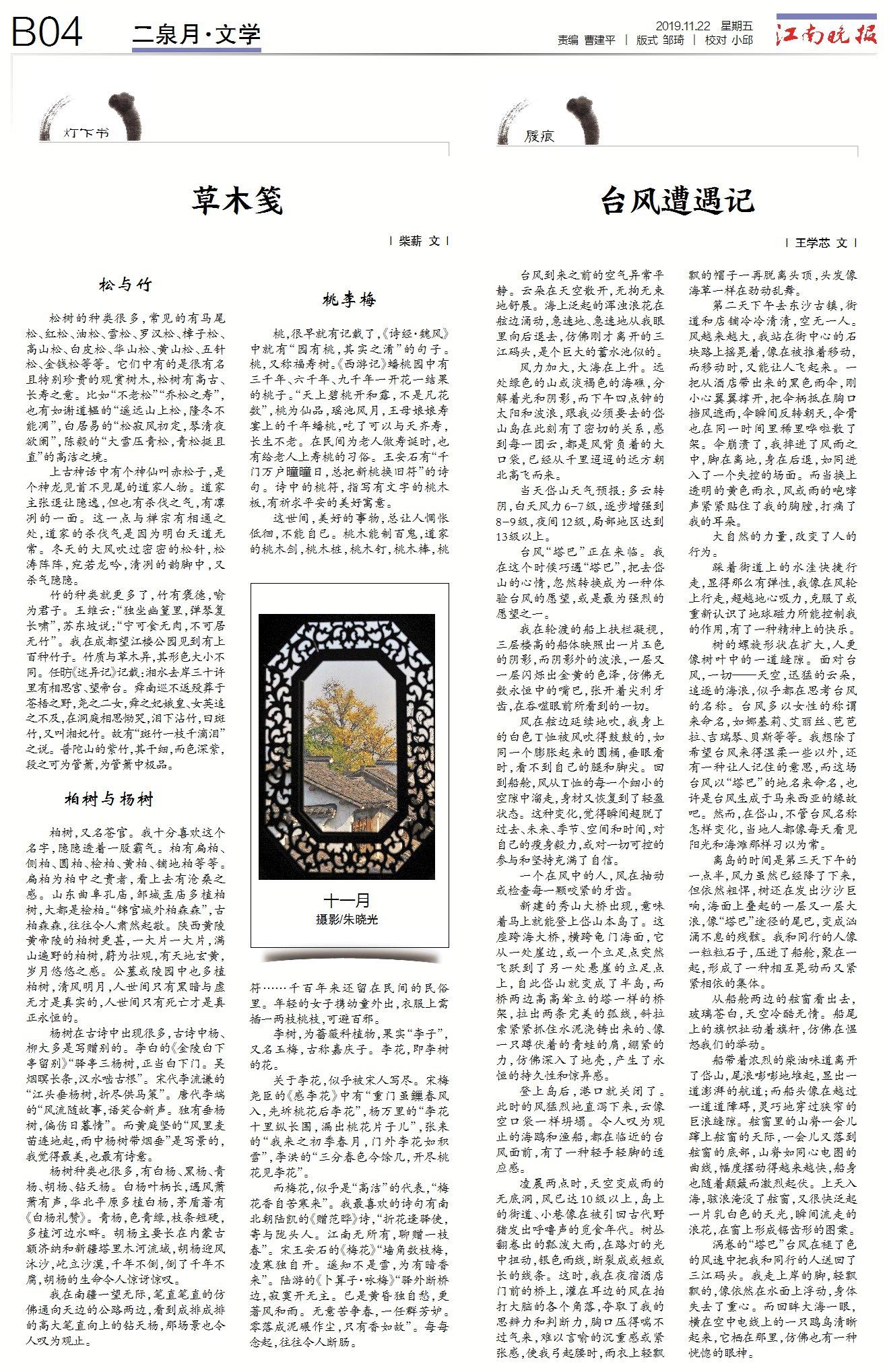| 王学芯 文 |
台风到来之前的空气异常平静。云朵在天空散开,无拘无束地舒展。海上泛起的浑浊浪花在舷边涌动,急速地、急速地从我眼里向后退去,仿佛刚才离开的三江码头,是个巨大的蓄水池似的。
风力加大,大海在上升。远处绿色的山或淡褐色的海礁,分解着光和阴影,而下午四点钟的太阳和波浪,跟我必须要去的岱山岛在此刻有了密切的关系,感到每一团云,都是风背负着的大口袋,已经从千里迢迢的远方朝北高飞而来。
当天岱山天气预报:多云转阴,白天风力6-7级,逐步增强到8-9级,夜间12级,局部地区达到13级以上。
台风“塔巴”正在来临。我在这个时候巧遇“塔巴”,把去岱山的心情,忽然转换成为一种体验台风的愿望,或是最为强烈的愿望之一。
我在轮渡的船上扶栏凝视,三层楼高的船体映照出一片玉色的阴影,而阴影外的波浪,一层又一层闪烁出金黄的色泽,仿佛无数永恒中的嘴巴,张开着尖利牙齿,在吞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风在舷边延续地吹,我身上的白色T恤被风吹得鼓鼓的,如同一个膨胀起来的圆桶,垂眼看时,看不到自己的腿和脚尖。回到船舱,风从T恤的每一个细小的空隙中溜走,身材又恢复到了轻盈状态。这种变化,觉得瞬间超脱了过去、未来、季节、空间和时间,对自己的瘦身毅力,或对一切可控的参与和坚持充满了自信。
一个在风中的人,风在抽动或检查每一颗咬紧的牙齿。
新建的秀山大桥出现,意味着马上就能登上岱山本岛了。这座跨海大桥,横跨龟门海面,它从一处崖边,或一个立足点突然飞跃到了另一处悬崖的立足点上,自此岱山就变成了半岛,而桥两边高高耸立的塔一样的桥架,拉出两条完美的弧线,斜拉索紧紧抓住水泥浇铸出来的、像一只蹲伏着的青蛙的肩,绷紧的力,仿佛深入了地壳,产生了永恒的持久性和惊异感。
登上岛后,港口就关闭了。此时的风猛烈地直泻下来,云像空口袋一样坍塌。令人叹为观止的海鸥和渔船,都在临近的台风面前,有了一种轻手轻脚的适应感。
凌晨两点时,天空变成雨的无底洞,风已达10级以上,岛上的街道、小巷像在被引回古代野猪发出呼噜声的觅食年代。树丛翻卷出的瓢泼大雨,在路灯的光中扭动,银色雨线,断裂成或短或长的线条。这时,我在夜宿酒店门前的桥上,灌在耳边的风在拍打大脑的各个角落,夺取了我的思辨力和判断力,胸口压得喘不过气来,难以言喻的沉重感或紧张感,使我弓起腰时,雨衣上轻飘飘的帽子一再脱离头顶,头发像海草一样在劲动乱舞。
第二天下午去东沙古镇,街道和店铺冷冷清清,空无一人。风越来越大,我站在街中心的石块路上摇晃着,像在被推着移动,而移动时,又能让人飞起来。一把从酒店带出来的黑色雨伞,刚小心翼翼撑开,把伞柄抵在胸口挡风遮雨,伞瞬间反转朝天,伞骨也在同一时间里稀里哗啦散了架。伞崩溃了,我摔进了风雨之中,脚在离地,身在后退,如同进入了一个失控的场面。而当换上透明的黄色雨衣,风或雨的咆哮声紧紧贴住了我的胸膛,打痛了我的耳朵。
大自然的力量,改变了人的行为。
踩着街道上的水洼快捷行走,显得那么有弹性,我像在风轮上行走,超越地心吸力,克服了或重新认识了地球磁力所能控制我的作用,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快乐。
树的螺旋形状在扩大,人更像树叶中的一道缝隙。面对台风,一切——天空,迅猛的云朵,追逐的海浪,似乎都在思考台风的名称。台风多以女性的称谓来命名,如娜基莉、艾丽丝、芭芭拉、吉瑞琴、贝斯等等。我想除了希望台风来得温柔一些以外,还有一种让人记住的意思,而这场台风以“塔巴”的地名来命名,也许是台风生成于马来西亚的缘故吧。然而,在岱山,不管台风名称怎样变化,当地人都像每天看见阳光和海滩那样习以为常。
离岛的时间是第三天下午的一点半,风力虽然已经降了下来,但依然粗悍,树还在发出沙沙巨响,海面上叠起的一层又一层大浪,像“塔巴”途径的尾巴,变成汹涌不息的残骸。我和同行的人像一粒粒石子,压进了船舱,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相互晃动而又紧紧相依的集体。
从船舱两边的舷窗看出去,玻璃苍白,天空冷酷无情。船尾上的旗帜扯动着旗杆,仿佛在愠怒我们的举动。
船带着浓烈的柴油味道离开了岱山,尾浪嘭嘭地堆起,显出一道澎湃的航道;而船头像在越过一道道障碍,灵巧地穿过狭窄的巨浪缝隙。舷窗里的山脊一会儿蹿上舷窗的天际,一会儿又落到舷窗的底部,山脊如同心电图的曲线,幅度摆动得越来越快,船身也随着颠簸而激烈起伏。上天入海,骇浪淹没了舷窗,又很快泛起一片乳白色的天光,瞬间流走的浪花,在窗上形成锯齿形的图案。
涡卷的“塔巴”台风在褪了色的风速中把我和同行的人送回了三江码头。我走上岸的脚,轻飘飘的,像依然在水面上浮动,身体失去了重心。而回眸大海一眼,横在空中电线上的一只鸥鸟清晰起来,它栖在那里,仿佛也有一种恍惚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