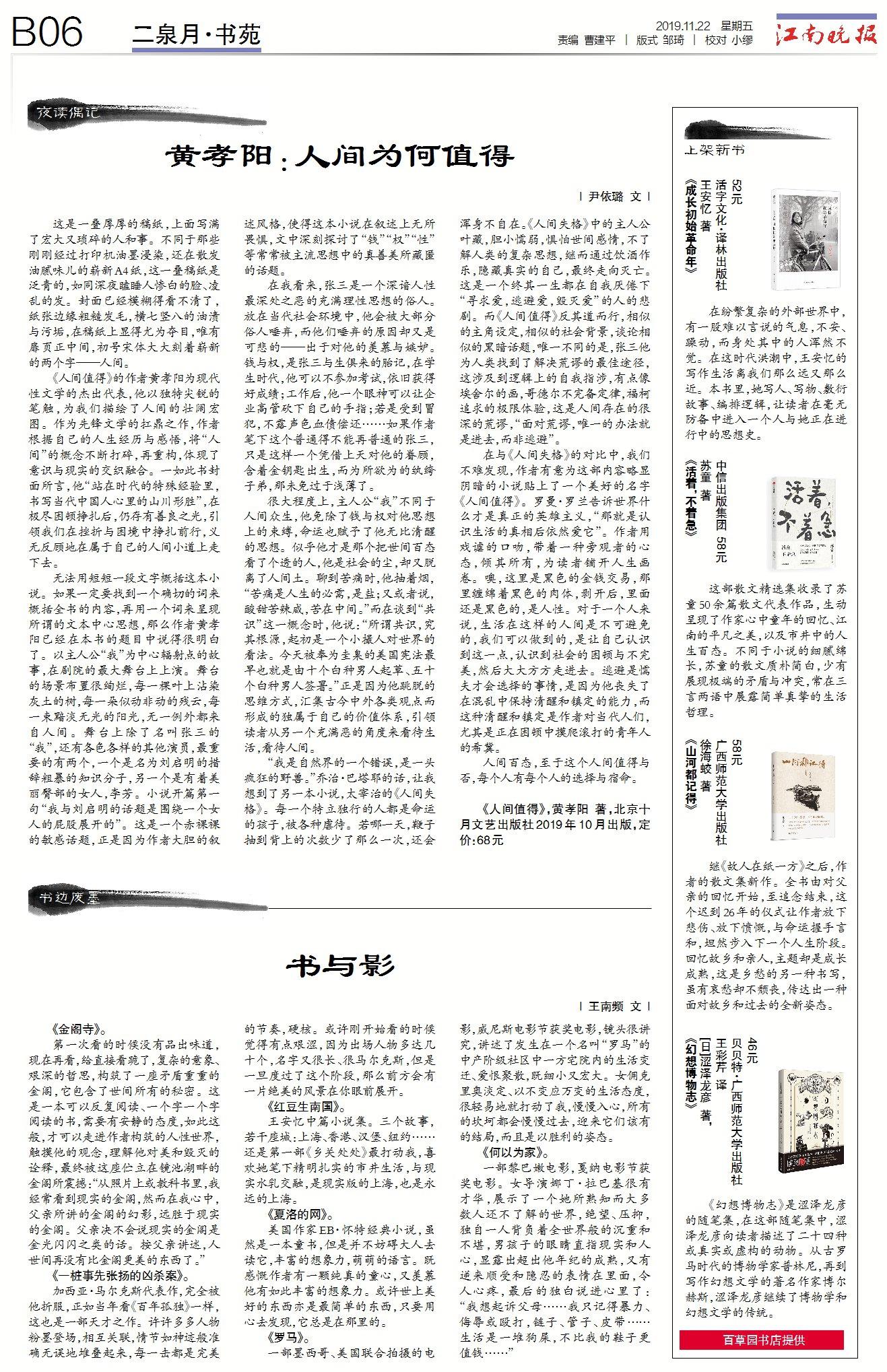| 尹依璐 文 |
这是一叠厚厚的稿纸,上面写满了宏大又琐碎的人和事。不同于那些刚刚经过打印机油墨浸染,还在散发油腻味儿的崭新A4纸,这一叠稿纸是泛青的,如同深夜瞌睡人惨白的脸、凌乱的发。封面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纸张边缘粗糙发毛,横七竖八的油渍与污垢,在稿纸上显得尤为夺目,唯有扉页正中间,初号宋体大大刻着崭新的两个字——人间。
《人间值得》的作者黄孝阳为现代性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以独特尖锐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人间的壮阔宏图。作为先锋文学的扛鼎之作,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将“人间”的概念不断打碎,再重构,体现了意识与现实的交织融合。一如此书封面所言,他“站在时代的特殊经验里,书写当代中国人心里的山川形胜”,在极尽困顿挣扎后,仍存有善良之光,引领我们在挫折与困境中挣扎前行,义无反顾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小道上走下去。
无法用短短一段文字概括这本小说。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来概括全书的内容,再用一个词来呈现所谓的文本中心思想,那么作者黄孝阳已经在本书的题目中说得很明白了。以主人公“我”为中心辐射点的故事,在剧院的最大舞台上上演。舞台的场景布置很绚烂,每一棵叶上沾染灰土的树,每一朵似动非动的残云,每一束黯淡无光的阳光,无一例外都来自人间。舞台上除了名叫张三的“我”,还有各色各样的其他演员,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名为刘启明的措辞粗暴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是有着美丽臀部的女人,李芳。小说开篇第一句“我与刘启明的话题是围绕一个女人的屁股展开的”。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敏感话题,正是因为作者大胆的叙述风格,使得这本小说在叙述上无所畏惧,文中深刻探讨了“钱”“权”“性”等常常被主流思想中的真善美所藏匿的话题。
在我看来,张三是一个深谙人性最深处之恶的充满理性思想的俗人。放在当代社会环境中,他会被大部分俗人唾弃,而他们唾弃的原因却又是可悲的——出于对他的羡慕与嫉妒。钱与权,是张三与生俱来的胎记,在学生时代,他可以不参加考试,依旧获得好成绩;工作后,他一个眼神可以让企业高管砍下自己的手指;若是受到冒犯,不露声色血债偿还……如果作者笔下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张三,只是这样一个凭借上天对他的眷顾,含着金钥匙出生,而为所欲为的纨绔子弟,那未免过于浅薄了。
很大程度上,主人公“我”不同于人间众生,他免除了钱与权对他思想上的束缚,命运也赋予了他无比清醒的思想。似乎他才是那个把世间百态看了个透的人,他是社会的尘,却又脱离了人间土。聊到苦痛时,他抽着烟,“苦痛是人生的必需,是盐;又或者说,酸甜苦辣咸,苦在中间。”而在谈到“共识”这一概念时,他说:“所谓共识,究其根源,起初是一个小撮人对世界的看法。今天被奉为圭臬的美国宪法最早也就是由十个白种男人起草、五十个白种男人签署。”正是因为他跳脱的思维方式,汇集古今中外各类观点而形成的独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引领读者从另一个充满恶的角度来看待生活,看待人间。
“我是自然界的一个错误,是一头疯狂的野兽。”乔治·巴塔耶的话,让我想到了另一本小说,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每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都是命运的孩子,被各种虐待。若哪一天,鞭子抽到背上的次数少了那么一次,还会浑身不自在。《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叶藏,胆小懦弱,惧怕世间感情,不了解人类的复杂思想,继而通过饮酒作乐,隐藏真实的自己,最终走向灭亡。这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在自我厌倦下“寻求爱,逃避爱,毁灭爱”的人的悲剧。而《人间值得》反其道而行,相似的主角设定,相似的社会背景,谈论相似的黑暗话题,唯一不同的是,张三他为人类找到了解决荒谬的最佳途径,这涉及到逻辑上的自我指涉,有点像埃舍尔的画,哥德尔不完备定律,福柯追求的极限体验,这是人间存在的很深的荒谬,“面对荒谬,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去,而非逃避”。
在与《人间失格》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有意为这部内容略显阴暗的小说贴上了一个美好的名字《人间值得》。罗曼·罗兰告诉世界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作者用戏谑的口吻,带着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倾其所有,为读者铺开人生画卷。噢,这里是黑色的金钱交易,那里缠绵着黑色的肉体,剥开后,里面还是黑色的,是人性。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在这样的人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自己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社会的困顿与不完美,然后大大方方走进去。逃避是懦夫才会选择的事情,是因为他丧失了在混乱中保持清醒和镇定的能力,而这种清醒和镇定是作者对当代人们,尤其是正在困顿中摸爬滚打的青年人的希冀。
人间百态,至于这个人间值得与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与宿命。
《人间值得》,黄孝阳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