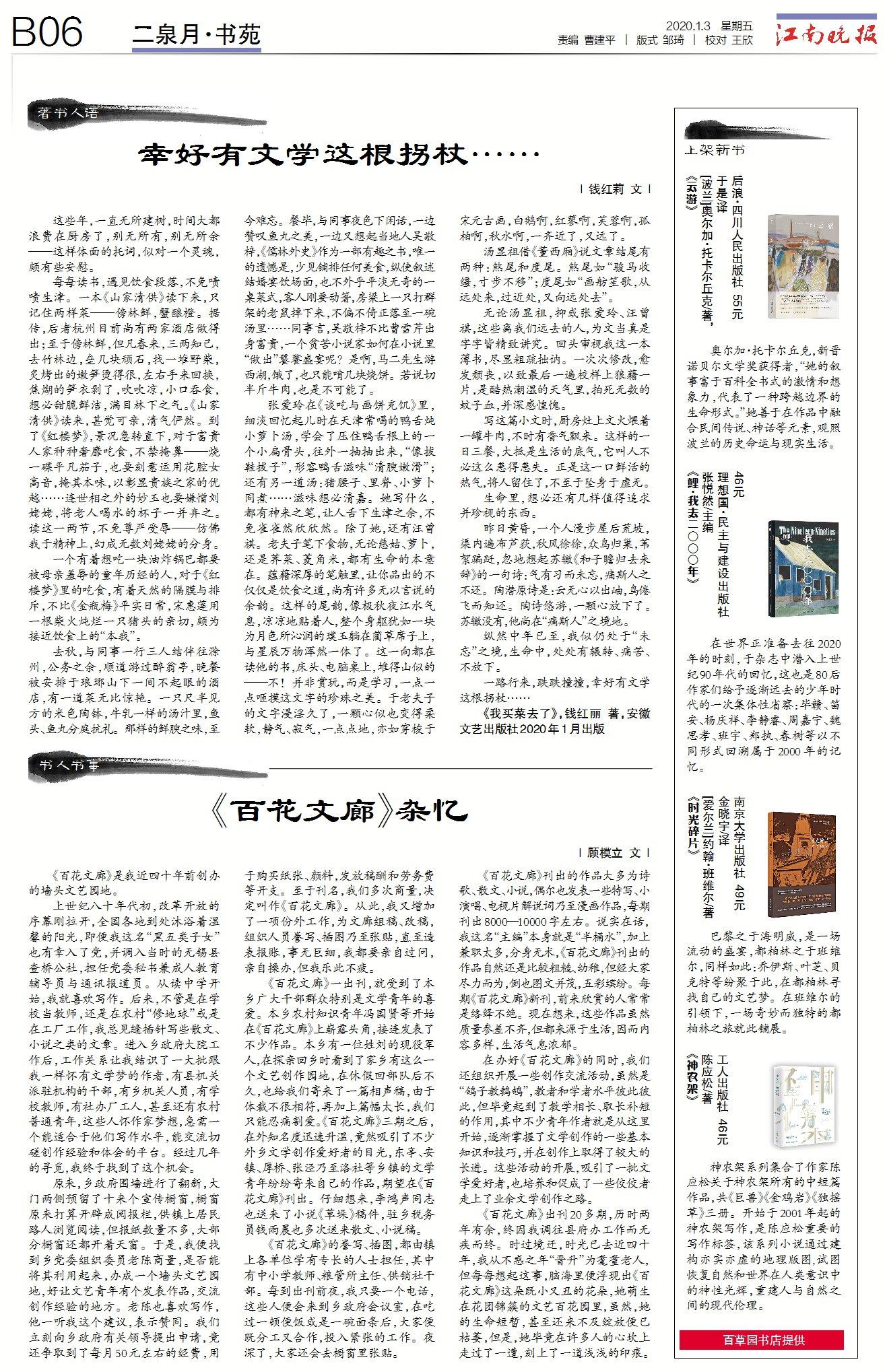| 顾模立 文 |
《百花文廊》是我近四十年前创办的墙头文艺园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序幕刚拉开,全国各地到处沐浴着温馨的阳光,即便我这名“黑五类子女”也有幸入了党,并调入当时的无锡县查桥公社,担任党委秘书兼成人教育辅导员与通讯报道员。从读中学开始,我就喜欢写作。后来,不管是在学校当教师,还是在农村“修地球”或是在工厂工作,我总见缝插针写些散文、小说之类的文章。进入乡政府大院工作后,工作关系让我结识了一大批跟我一样怀有文学梦的作者,有县机关派驻机构的干部,有乡机关人员,有学校教师,有社办厂工人,甚至还有农村普通青年,这些人怀作家梦想,急需一个能适合于他们写作水平,能交流切磋创作经验和体会的平台。经过几年的寻觅,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
原来,乡政府围墙进行了翻新,大门两侧预留了十来个宣传橱窗,橱窗原来打算开辟成阅报栏,供镇上居民路人浏览阅读,但报纸数量不多,大部分橱窗还都开着天窗。于是,我便找到乡党委组织委员老陈商量,是否能将其利用起来,办成一个墙头文艺园地,好让文艺青年有个发表作品,交流创作经验的地方。老陈也喜欢写作,他一听我这个建议,表示赞同。我们立刻向乡政府有关领导提出申请,竟还争取到了每月50元左右的经费,用于购买纸张、颜料,发放稿酬和劳务费等开支。至于刊名,我们多次商量,决定叫作《百花文廊》。从此,我又增加了一项份外工作,为文廊组稿、改稿,组织人员誊写、插图乃至张贴,直至造表报账,事无巨细,我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操办,但我乐此不疲。
《百花文廊》一出刊,就受到了本乡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喜爱。本乡农村知识青年冯国贤等开始在《百花文廊》上崭露头角,接连发表了不少作品。本乡有一位姓刘的现役军人,在探亲回乡时看到了家乡有这么一个文艺创作园地,在休假回部队后不久,也给我们寄来了一篇相声稿,由于体裁不很相符,再加上篇幅太长,我们只能忍痛割爱。《百花文廊》三期之后,在外知名度迅速升温,竟然吸引了不少外乡文学创作爱好者的目光,东亭、安镇、厚桥、张泾乃至洛社等乡镇的文学青年纷纷寄来自己的作品,期望在《百花文廊》刊出。仔细想来,李鸿声同志也送来了小说《草垛》稿件,驻乡税务员钱雨晨也多次送来散文、小说稿。
《百花文廊》的誊写、插图,都由镇上各单位学有专长的人士担任,其中有中小学教师、粮管所主任、供销社干部。每到出刊前夜,我只要一个电话,这些人便会来到乡政府会议室,在吃过一顿便饭或是一碗面条后,大家便既分工又合作,投入紧张的工作。夜深了,大家还会去橱窗里张贴。
《百花文廊》刊出的作品大多为诗歌、散文、小说,偶尔也发表一些特写、小演唱、电视片解说词乃至漫画作品,每期刊出8000—10000字左右。说实在话,我这名“主编”本身就是“半桶水”,加上兼职太多,分身无术,《百花文廊》刊出的作品自然还是比较粗糙、幼稚,但经大家尽力而为,倒也图文并茂,五彩缤纷。每期《百花文廊》新刊,前来欣赏的人常常是络绎不绝。现在想来,这些作品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都来源于生活,因而内容多样,生活气息浓郁。
在办好《百花文廊》的同时,我们还组织开展一些创作交流活动,虽然是“鸽子教鹁鸪”,教者和学者水平彼此彼此,但毕竟起到了教学相长、取长补短的作用,其中不少青年作者就是从这里开始,逐渐掌握了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巧,并在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长进。这些活动的开展,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也培养和促成了一些佼佼者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之路。
《百花文廊》出刊20多期,历时两年有余,终因我调往县府办工作而无疾而终。时过境迁,时光已去近四十年,我从不惑之年“晋升”为耄耋老人,但每每想起这事,脑海里便浮现出《百花文廊》这朵既小又丑的花朵,她萌生在花团锦簇的文艺百花园里,虽然,她的生命短暂,甚至还来不及绽放便已枯萎,但是,她毕竟在许多人的心坎上走过了一遭,刻上了一道浅浅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