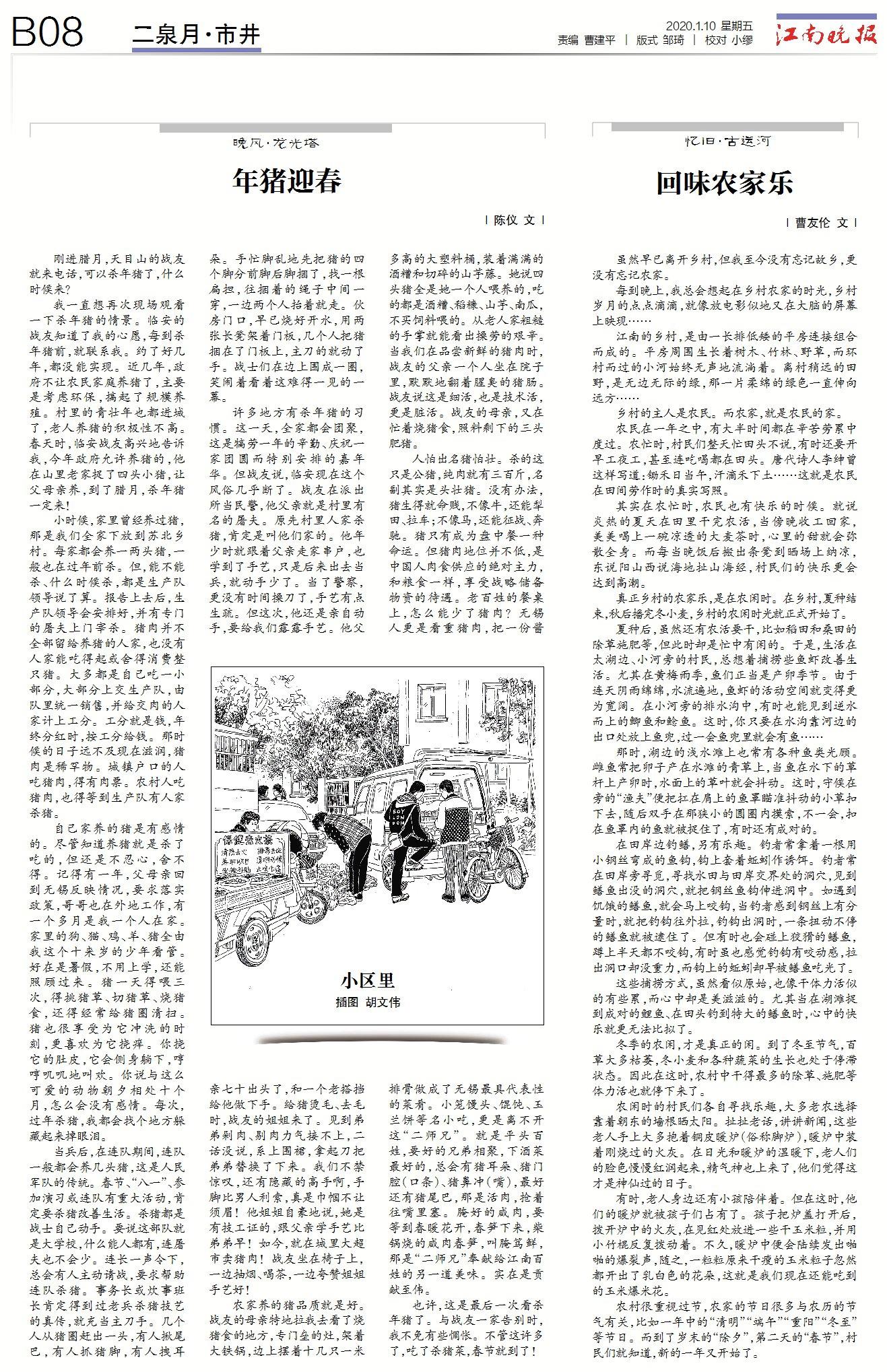| 陈仪 文 |
刚进腊月,天目山的战友就来电话,可以杀年猪了,什么时候来?
我一直想再次现场观看一下杀年猪的情景。临安的战友知道了我的心愿,每到杀年猪前,就联系我。约了好几年,都没能实现。近几年,政府不让农民家庭养猪了,主要是考虑环保,搞起了规模养殖。村里的青壮年也都进城了,老人养猪的积极性不高。春天时,临安战友高兴地告诉我,今年政府允许养猪的,他在山里老家捉了四头小猪,让父母亲养,到了腊月,杀年猪一定来!
小时候,家里曾经养过猪,那是我们全家下放到苏北乡村。每家都会养一两头猪,一般也在过年前杀。但,能不能杀、什么时候杀,都是生产队领导说了算。报告上去后,生产队领导会安排好,并有专门的屠夫上门宰杀。猪肉并不全部留给养猪的人家,也没有人家能吃得起或舍得消费整只猪。大多都是自己吃一小部分,大部分上交生产队,由队里统一销售,并给交肉的人家计上工分。工分就是钱,年终分红时,按工分给钱。那时候的日子远不及现在滋润,猪肉是稀罕物。城镇户口的人吃猪肉,得有肉票。农村人吃猪肉,也得等到生产队有人家杀猪。
自己家养的猪是有感情的。尽管知道养猪就是杀了吃的,但还是不忍心,舍不得。记得有一年,父母亲回到无锡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哥哥也在外地工作,有一个多月是我一个人在家。家里的狗、猫、鸡、羊、猪全由我这个十来岁的少年看管。好在是暑假,不用上学,还能照顾过来。猪一天得喂三次,得挑猪草、切猪草、烧猪食,还得经常给猪圈清扫。猪也很享受为它冲洗的时刻,更喜欢为它挠痒。你挠它的肚皮,它会侧身躺下,哼哼叽叽地叫欢。你说与这么可爱的动物朝夕相处十个月,怎么会没有感情。每次,过年杀猪,我都会找个地方躲藏起来掉眼泪。
当兵后,在连队期间,连队一般都会养几头猪,这是人民军队的传统。春节、“八一”、参加演习或连队有重大活动,肯定要杀猪改善生活。杀猪都是战士自己动手。要说这部队就是大学校,什么能人都有,连屠夫也不会少。连长一声令下,总会有人主动请战,要求帮助连队杀猪。事务长或炊事班长肯定得到过老兵杀猪技艺的真传,就充当主刀手。几个人从猪圈赶出一头,有人揪尾巴,有人抓猪脚,有人拽耳朵。手忙脚乱地先把猪的四个脚分前脚后脚捆了,找一根扁担,往捆着的绳子中间一穿,一边两个人抬着就走。伙房门口,早已烧好开水,用两张长凳架着门板,几个人把猪捆在了门板上,主刀的就动了手。战士们在边上围成一圈,笑闹着看着这难得一见的一幕。
许多地方有杀年猪的习惯。这一天,全家都会团聚,这是犒劳一年的辛勤、庆祝一家团圆而特别安排的嘉年华。但战友说,临安现在这个风俗几乎断了。战友在派出所当民警,他父亲就是村里有名的屠夫。原先村里人家杀猪,肯定是叫他们家的。他年少时就跟着父亲走家串户,也学到了手艺,只是后来出去当兵,就动手少了。当了警察,更没有时间操刀了,手艺有点生疏。但这次,他还是亲自动手,要给我们露露手艺。他父亲七十出头了,和一个老搭挡给他做下手。给猪烫毛、去毛时,战友的姐姐来了。见到弟弟剁肉、剔肉力气接不上,二话没说,系上围裙,拿起刀把弟弟替换了下来。我们不禁惊叹,还有隐藏的高手啊,手脚比男人利索,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他姐姐自豪地说,她是有技工证的,跟父亲学手艺比弟弟早!如今,就在城里大超市卖猪肉!战友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夸赞姐姐手艺好!
农家养的猪品质就是好。战友的母亲特地拉我去看了烧猪食的地方,专门垒的灶,架着大铁锅,边上摆着十几只一米多高的大塑料桶,装着满满的酒糟和切碎的山芋藤。她说四头猪全是她一个人喂养的,吃的都是酒糟、稻糠、山芋、南瓜,不买饲料喂的。从老人家粗糙的手掌就能看出操劳的艰辛。当我们在品尝新鲜的猪肉时,战友的父亲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默默地翻着腥臭的猪肠。战友说这是细活,也是技术活,更是脏活。战友的母亲,又在忙着烧猪食,照料剩下的三头肥猪。
人怕出名猪怕壮。杀的这只是公猪,纯肉就有三百斤,名副其实是头壮猪。没有办法,猪生得就命贱,不像牛,还能犁田、拉车;不像马,还能征战、奔驰。猪只有成为盘中餐一种命运。但猪肉地位并不低,是中国人肉食供应的绝对主力,和粮食一样,享受战略储备物资的待遇。老百姓的餐桌上,怎么能少了猪肉?无锡人更是看重猪肉,把一份酱排骨做成了无锡最具代表性的菜肴。小笼馒头、馄饨、玉兰饼等名小吃,更是离不开这“二师兄”。就是平头百姓,要好的兄弟相聚,下酒菜最好的,总会有猪耳朵、猪门腔(口条)、猪鼻冲(嘴),最好还有猪尾巴,那是活肉,抢着往嘴里塞。腌好的咸肉,要等到春暖花开,春笋下来,柴锅烧的咸肉春笋,叫腌笃鲜,那是“二师兄”奉献给江南百姓的另一道美味。实在是贡献至伟。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看杀年猪了。与战友一家告别时,我不免有些惆怅。不管这许多了,吃了杀猪菜,春节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