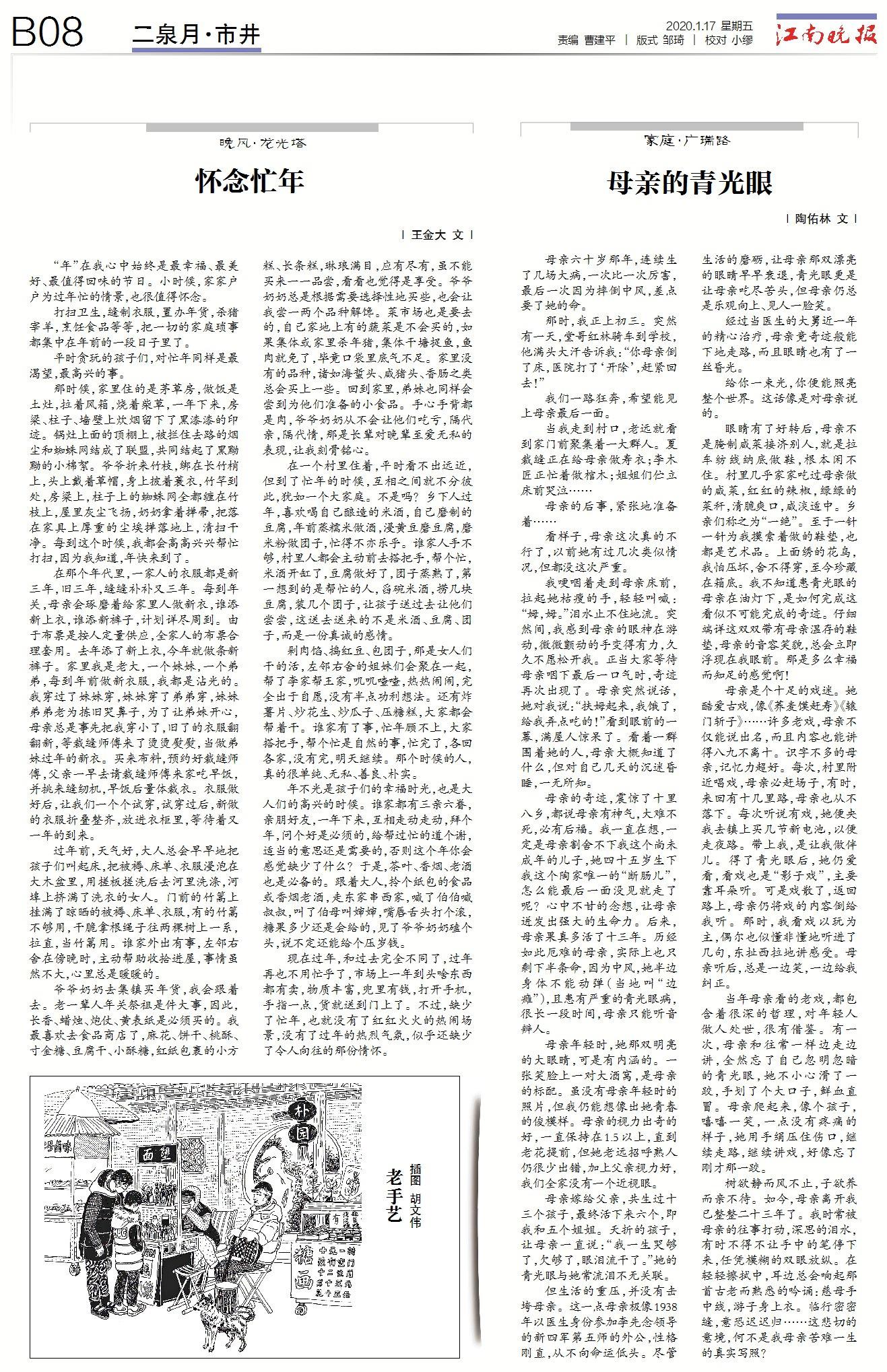| 陶佑林 文 |
母亲六十岁那年,连续生了几场大病,一次比一次厉害,最后一次因为摔倒中风,差点要了她的命。
那时,我正上初三。突然有一天,堂哥红林骑车到学校,他满头大汗告诉我:“你母亲倒了床,医院打了‘开除’,赶紧回去!”
我们一路狂奔,希望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当我走到村口,老远就看到家门前聚集着一大群人。夏裁缝正在给母亲做寿衣;李木匠正忙着做棺木;姐姐们伫立床前哭泣……
母亲的后事,紧张地准备着……
看样子,母亲这次真的不行了,以前她有过几次类似情况,但都没这次严重。
我哽咽着走到母亲床前,拉起她枯瘦的手,轻轻叫喊:“姆,姆。”泪水止不住地流。突然间,我感到母亲的眼神在游动,微微颤动的手变得有力,久久不愿松开我。正当大家等待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奇迹再次出现了。母亲突然说话,她对我说:“扶姆起来,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看到眼前的一幕,满屋人惊呆了。看着一群围着她的人,母亲大概知道了什么,但对自己几天的沉迷昏睡,一无所知。
母亲的奇迹,震惊了十里八乡,都说母亲有神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一直在想,一定是母亲割舍不下我这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她四十五岁生下我这个陶家唯一的“断肠儿”,怎么能最后一面没见就走了呢?心中不甘的念想,让母亲迸发岀强大的生命力。后来,母亲果真多活了十三年。历经如此厄难的母亲,实际上也只剩下半条命,因为中风,她半边身体不能动弹(当地叫“边瘫”),且患有严重的青光眼病,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只能听音辨人。
母亲年轻时,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可是有内涵的。一张笑脸上一对大酒窝,是母亲的标配。虽没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但我仍能想像出她青春的俊模样。母亲的视力出奇的好,一直保持在1.5以上,直到老花提前,但她老远招呼熟人仍很少出错,加上父亲视力好,我们全家没有一个近视眼。
母亲嫁给父亲,共生过十三个孩子,最终活下来六个,即我和五个姐姐。夭折的孩子,让母亲一直说:“我一生哭够了,欠够了,眼泪流干了。”她的青光眼与她常流泪不无关联。
但生活的重压,并没有击垮母亲。这一点母亲极像1938年以医生身份参加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外公,性格刚直,从不向命运低头。尽管生活的磨砺,让母亲那双漂亮的眼睛早早衰退,青光眼更是让母亲吃尽苦头,但母亲仍总是乐观向上、见人一脸笑。
经过当医生的大舅近一年的精心治疗,母亲竟奇迹般能下地走路,而且眼睛也有了一丝昏光。
给你一束光,你便能照亮整个世界。这话像是对母亲说的。
眼睛有了好转后,母亲不是腌制咸菜接济别人,就是拉车纺线纳底做鞋,根本闲不住。村里几乎家家吃过母亲做的咸菜,红红的辣椒,绿绿的菜秆,清脆爽口,咸淡适中。乡亲们称之为“一绝”。至于一针一针为我摸索着做的鞋垫,也都是艺术品。上面绣的花鸟,我怕压坏,舍不得穿,至今珍藏在箱底。我不知道患青光眼的母亲在油灯下,是如何完成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奇迹。仔细端详这双双带有母亲温存的鞋垫,母亲的音容笑貌,总会立即浮现在我眼前。那是多么幸福而知足的感觉啊!
母亲是个十足的戏迷。她酷爱古戏,像《荞麦馍赶寿》《辕门斩子》……许多老戏,母亲不仅能说出名,而且内容也能讲得八九不离十。识字不多的母亲,记忆力超好。每次,村里附近唱戏,母亲必赶场子,有时,来回有十几里路,母亲也从不落下。每次听说有戏,她便央我去镇上买几节新电池,以便走夜路。带上我,是让我做伴儿。得了青光眼后,她仍爱看,看戏也是“影子戏”,主要靠耳朵听。可是戏散了,返回路上,母亲仍将戏的内容倒给我听。那时,我看戏以玩为主,偶尔也似懂非懂地听进了几句,东扯西拉地讲感受。母亲听后,总是一边笑,一边给我纠正。
当年母亲看的老戏,都包含着很深的哲理,对年轻人做人处世,很有借鉴。有一次,母亲和往常一样边走边讲,全然忘了自己忽明忽暗的青光眼,她不小心滑了一跤,手划了个大口子,鲜血直冒。母亲爬起来,像个孩子,嘻嘻一笑,一点没有疼痛的样子,她用手绢压住伤口,继续走路,继续讲戏,好像忘了刚才那一跤。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今,母亲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三年了。我时常被母亲的往事打动,深思的泪水,有时不得不让手中的笔停下来,任凭模糊的双眼放纵。在轻轻擦拭中,耳边总会响起那首古老而熟悉的吟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悲切的意境,何不是我母亲苦难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