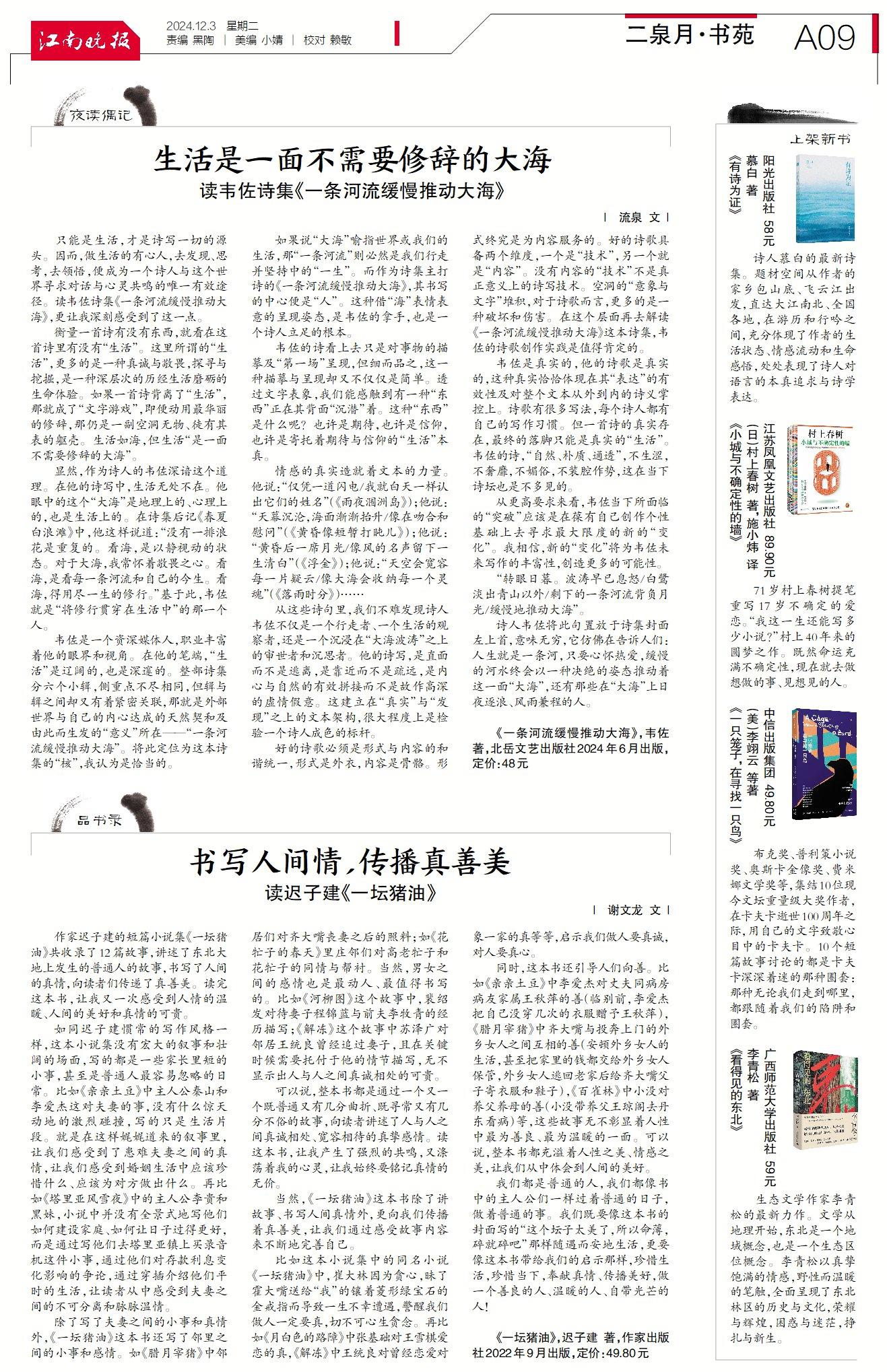| 流泉 文 |
只能是生活,才是诗写一切的源头。因而,做生活的有心人,去发现、思考,去领悟,便成为一个诗人与这个世界寻求对话与心灵共鸣的唯一有效途径。读韦佐诗集《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
衡量一首诗有没有东西,就看在这首诗里有没有“生活”。这里所谓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真诚与敬畏,探寻与挖掘,是一种深层次的历经生活磨砺的生命体验。如果一首诗背离了“生活”,那就成了“文字游戏”,即便动用最华丽的修辞,那仍是一副空洞无物、徒有其表的躯壳。生活如海,但生活“是一面不需要修辞的大海”。
显然,作为诗人的韦佐深谙这个道理。在他的诗写中,生活无处不在。他眼中的这个“大海”是地理上的、心理上的,也是生活上的。在诗集后记《春夏白浪滩》中,他这样说道:“没有一排浪花是重复的。看海,是以静视动的状态。对于大海,我常怀着敬畏之心。看海,是看每一条河流和自己的今生。看海,得用尽一生的修行。”基于此,韦佐就是“将修行贯穿在生活中”的那一个人。
韦佐是一个资深媒体人,职业丰富着他的眼界和视角。在他的笔端,“生活”是辽阔的,也是深邃的。整部诗集分六个小辑,侧重点不尽相同,但辑与辑之间却又有着紧密关联,那就是外部世界与自己的内心达成的天然契和及由此而生发的“意义”所在——“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将此定位为这本诗集的“核”,我认为是恰当的。
如果说“大海”喻指世界或我们的生活,那“一条河流”则必然是我们行走并坚持中的“一生”。而作为诗集主打诗的《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其书写的中心便是“人”。这种借“海”表情表意的呈现姿态,是韦佐的拿手,也是一个诗人立足的根本。
韦佐的诗看上去只是对事物的描摹及“第一场”呈现,但细而品之,这一种描摹与呈现却又不仅仅是简单。透过文字表象,我们能感触到有一种“东西”正在其背面“沉潜”着。这种“东西”是什么呢?也许是期待,也许是信仰,也许是寄托着期待与信仰的“生活”本真。
情感的真实造就着文本的力量。他说:“仅凭一道闪电/我就白天一样认出它们的姓名”(《雨夜涠洲岛》);他说:“天幕沉沦,海面渐渐抬升/像在吻合和慰问”(《黄昏像短暂打盹儿》);他说:“黄昏后一席月光/像风的名声留下一生清白”(《浮金》);他说:“天空会宽容每一片疑云/像大海会收纳每一个灵魂”(《落雨时分》)……
从这些诗句里,我们不难发现诗人韦佐不仅是一个行走者、一个生活的观察者,还是一个沉浸在“大海波涛”之上的审世者和沉思者。他的诗写,是直面而不是逃离,是靠近而不是疏远,是内心与自然的有效拼接而不是故作高深的虚情假意。这建立在“真实”与“发现”之上的文本架构,很大程度上是检验一个诗人成色的标杆。
好的诗歌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形式是外衣,内容是骨骼。形式终究是为内容服务的。好的诗歌具备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另一个就是“内容”。没有内容的“技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写技术。空洞的“意象与文字”堆积,对于诗歌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破坏和伤害。在这个层面再去解读《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这本诗集,韦佐的诗歌创作实践是值得肯定的。
韦佐是真实的,他的诗歌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恰恰体现在其“表达”的有效性及对整个文本从外到内的诗义掌控上。诗歌有很多写法,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但一首诗的真实存在,最终的落脚只能是真实的“生活”。韦佐的诗,“自然、朴质、通透”,不生涩,不奢靡,不媚俗,不装腔作势,这在当下诗坛也是不多见的。
从更高要求来看,韦佐当下所面临的“突破”应该是在葆有自己创作个性基础上去寻求最大限度的新的“变化”。我相信,新的“变化”将为韦佐未来写作的丰富性,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转眼日暮。波涛早已息怒/白鹭淡出青山以外/剩下的一条河流背负月光/缓慢地推动大海”。
诗人韦佐将此句置放于诗集封面左上首,意味无穷,它仿佛在告诉人们:人生就是一条河,只要心怀热爱,缓慢的河水终会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推动着这一面“大海”,还有那些在“大海”上日夜逐浪、风雨兼程的人。
《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韦佐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定价: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