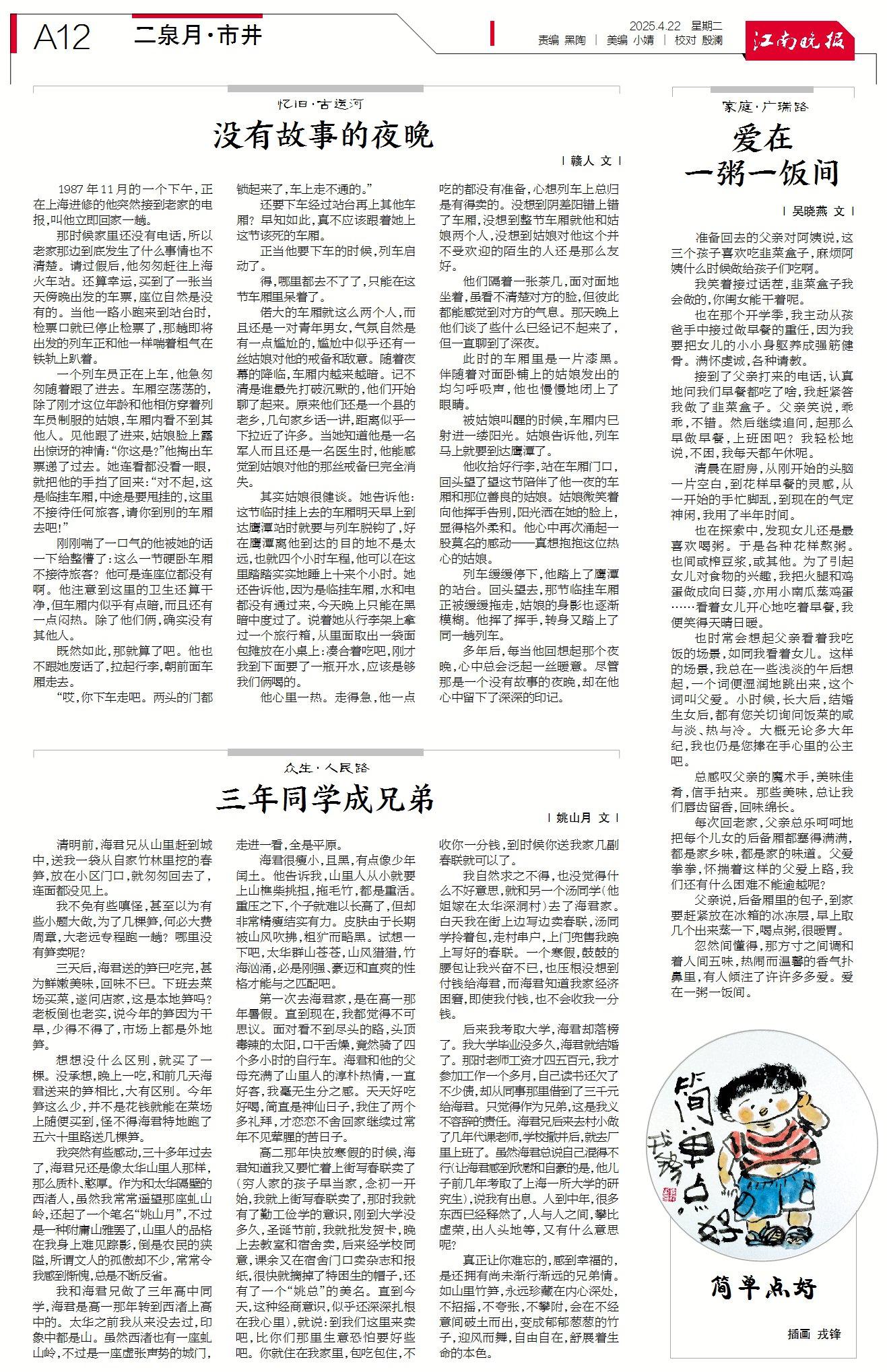| 姚山月 文 |
清明前,海君兄从山里赶到城中,送我一袋从自家竹林里挖的春笋,放在小区门口,就匆匆回去了,连面都没见上。
我不免有些嗔怪,甚至以为有些小题大做,为了几棵笋,何必大费周章,大老远专程跑一趟?哪里没有笋卖呢?
三天后,海君送的笋已吃完,甚为鲜嫩美味,回味不已。下班去菜场买菜,遂问店家,这是本地笋吗?老板倒也老实,说今年的笋因为干旱,少得不得了,市场上都是外地笋。
想想没什么区别,就买了一棵。没承想,晚上一吃,和前几天海君送来的笋相比,大有区别。今年笋这么少,并不是花钱就能在菜场上随便买到,怪不得海君特地跑了五六十里路送几棵笋。
我突然有些感动,三十多年过去了,海君兄还是像太华山里人那样,那么质朴、憨厚。作为和太华隔壁的西渚人,虽然我常常遥望那座虬山岭,还起了一个笔名“姚山月”,不过是一种附庸山雅罢了,山里人的品格在我身上难见踪影,倒是农民的狭隘,所谓文人的孤傲却不少,常常令我感到惭愧,总是不断反省。
我和海君兄做了三年高中同学,海君是高一那年转到西渚上高中的。太华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印象中都是山。虽然西渚也有一座虬山岭,不过是一座虚张声势的城门,走进一看,全是平原。
海君很瘦小,且黑,有点像少年闰土。他告诉我,山里人从小就要上山樵柴挑担,拖毛竹,都是重活。重压之下,个子就难以长高了,但却非常精瘦结实有力。皮肤由于长期被山风吹拂,粗犷而略黑。试想一下吧,太华群山苍苍,山风猎猎,竹海汹涌,必是刚强、豪迈和直爽的性格才能与之匹配吧。
第一次去海君家,是在高一那年暑假。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可思议。面对看不到尽头的路,头顶毒辣的太阳,口干舌燥,竟然骑了四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海君和他的父母充满了山里人的淳朴热情,一直好客,我毫无生分之感。天天好吃好喝,简直是神仙日子,我住了两个多礼拜,才恋恋不舍回家继续过常年不见荤腥的苦日子。
高二那年快放寒假的时候,海君知道我又要忙着上街写春联卖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念初一开始,我就上街写春联卖了,那时我就有了勤工俭学的意识,刚到大学没多久,圣诞节前,我就批发贺卡,晚上去教室和宿舍卖,后来经学校同意,课余又在宿舍门口卖杂志和报纸,很快就摘掉了特困生的帽子,还有了一个“姚总”的美名。直到今天,这种经商意识,似乎还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就说:到我们这里来卖吧,比你们那里生意恐怕要好些吧。你就住在我家里,包吃包住,不收你一分钱,到时候你送我家几副春联就可以了。
我自然求之不得,也没觉得什么不好意思,就和另一个汤同学(他姐嫁在太华深洞村)去了海君家。白天我在街上边写边卖春联,汤同学拎着包,走村串户,上门兜售我晚上写好的春联。一个寒假,鼓鼓的腰包让我兴奋不已,也压根没想到付钱给海君,而海君知道我家经济困窘,即使我付钱,也不会收我一分钱。
后来我考取大学,海君却落榜了。我大学毕业没多久,海君就结婚了。那时老师工资才四五百元,我才参加工作一个多月,自己读书还欠了不少债,却从同事那里借到了三千元给海君。只觉得作为兄弟,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海君兄后来去村小做了几年代课老师,学校撤并后,就去厂里上班了。虽然海君总说自己混得不行(让海君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他儿子前几年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说我有出息。人到中年,很多东西已经释然了,人与人之间,攀比虚荣,出人头地等,又有什么意思呢?
真正让你难忘的,感到幸福的,是还拥有尚未渐行渐远的兄弟情。如山里竹笋,永远珍藏在内心深处,不招摇,不夸张,不攀附,会在不经意间破土而出,变成郁郁葱葱的竹子,迎风而舞,自由自在,舒展着生命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