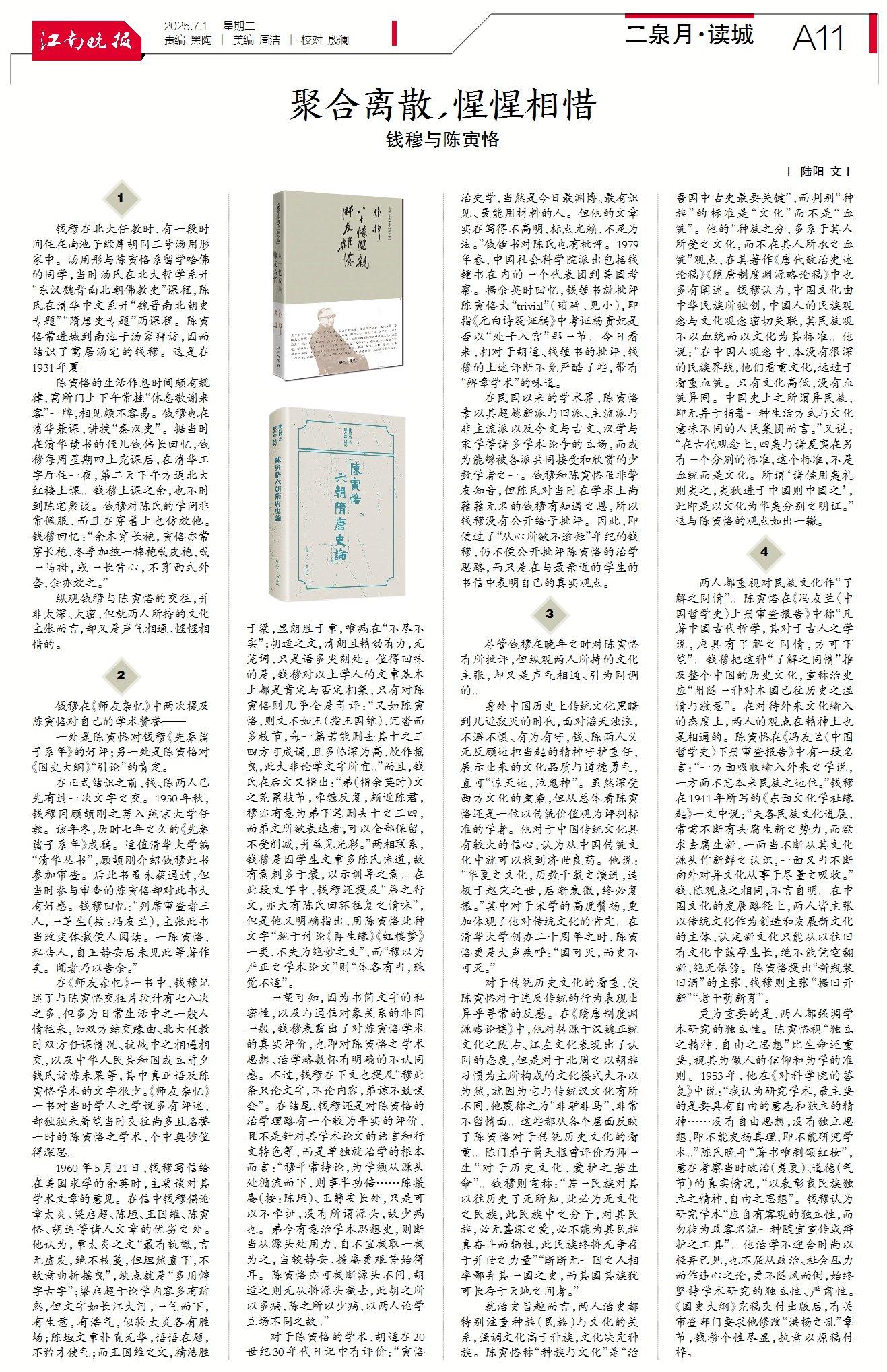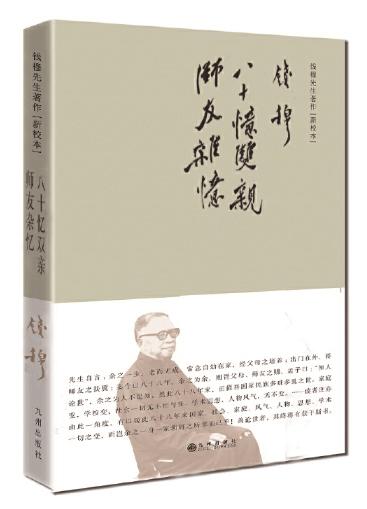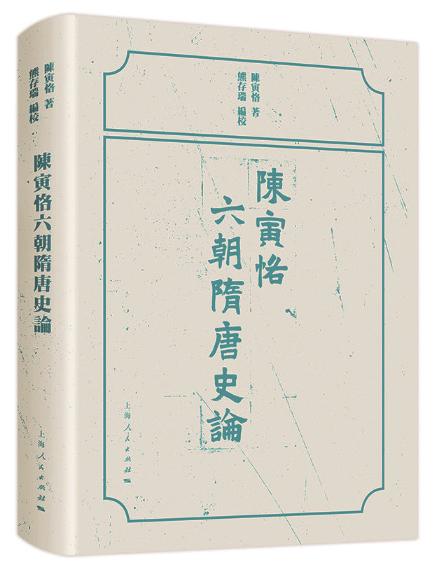| 陆阳 文|
1
钱穆在北大任教时,有一段时间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汤用彤家中。汤用彤与陈寅恪系留学哈佛的同学,当时汤氏在北大哲学系开“东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课程,陈氏在清华中文系开“魏晋南北朝史专题”“隋唐史专题”两课程。陈寅恪常进城到南池子汤家拜访,因而结识了寓居汤宅的钱穆。这是在1931年夏。
陈寅恪的生活作息时间颇有规律,寓所门上下午常挂“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见颇不容易。钱穆也在清华兼课,讲授“秦汉史”。据当时在清华读书的侄儿钱伟长回忆,钱穆每周星期四上完课后,在清华工字厅住一夜,第二天下午方返北大红楼上课。钱穆上课之余,也不时到陈宅聚谈。钱穆对陈氏的学问非常佩服,而且在穿着上也仿效他。钱穆回忆:“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纵观钱穆与陈寅恪的交往,并非太深、太密,但就两人所持的文化主张而言,却又是声气相通、惺惺相惜的。
2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两次提及陈寅恪对自己的学术赞誉——
一处是陈寅恪对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好评;另一处是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肯定。
在正式结识之前,钱、陈两人已先有过一次文字之交。1930年秋,钱穆因顾颉刚之荐入燕京大学任教。该年冬,历时七年之久的《先秦诸子系年》成稿。适值清华大学编“清华丛书”,顾颉刚介绍钱穆此书参加审查。后此书虽未获通过,但当时参与审查的陈寅恪却对此书大有好感。钱穆回忆:“列席审查者三人,一芝生(按:冯友兰),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闻者乃以告余。”
在《师友杂忆》一书中,钱穆记述了与陈寅恪交往片段计有七八次之多,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钱氏访陈未果等,其中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很少。《师友杂忆》一书对当时学人之学说多有评述,却独独未着笔当时交往尚多且名誉一时的陈寅恪之学术,个中奥妙值得深思。
1960年5月21日,钱穆写信给在美国求学的余英时,主要谈对其学术文章的意见。在信中钱穆倡论章太炎、梁启超、陈垣、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诸人文章的优劣之处。他认为,章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缺点就是“多用僻字古字”;梁启超于论学内容多有疏忽,但文字如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较太炎各有胜场;陈垣文章朴直无华,语语在题,不矜才使气;而王国维之文,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唯病在“不尽不实”;胡适之文,清朗且精劲有力,无芜词,只是语多尖刻处。值得回味的是,钱穆对以上学人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与否定相集,只有对陈寅恪则几乎全是苛评:“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指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而且,钱氏在后文又指出:“弟(指余英时)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穆亦有意为弟下笔删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彩。”两相联系,钱穆是因学生文章多陈氏味道,故有意刺多于褒,以示训导之意。在此段文字中,钱穆还提及“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复之情味”,但是他又明确指出,用陈寅恪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穆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
一望可知,因为书简文字的私密性,以及与通信对象关系的非同一般,钱穆表露出了对陈寅恪学术的真实评价,也即对陈寅恪之学术思想、治学路数怀有明确的不认同感。不过,钱穆在下文也提及“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在结尾,钱穆还是对陈寅恪的治学理路有一个较为平实的评价,且不是针对其学术论文的语言和行文特色等,而是单独就治学的根本而言:“穆平常持论,为学须从源头处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陈援庵(按:陈垣)、王静安长处,只是可以不牵扯,没有所谓源头,故少病也。弟今有意治学术思想史,则断当从源头处用力,自不宜截取一截为之,当较静安、援庵更艰苦始得耳。陈寅恪亦可截断源头不问,胡适之则无从将源头截去,此胡之所以多病,陈之所以少病,以两人论学立场不同之故。”
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日记中有评价:“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钱锺书对陈氏也有批评。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包括钱锺书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据余英时回忆,钱锺书就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今日看来,相对于胡适、钱锺书的批评,钱穆的上述评断不免严酷了些,带有“辨章学术”的味道。
在民国以来的学术界,陈寅恪素以其超越新派与旧派、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以及今文与古文、汉学与宋学等诸多学术论争的立场,而成为能够被各派共同接受和欣赏的少数学者之一。钱穆和陈寅恪虽非挚友知音,但陈氏对当时在学术上尚藉藉无名的钱穆有知遇之恩,所以钱穆没有公开给予批评。因此,即便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年纪的钱穆,仍不便公开批评陈寅恪的治学思路,而只是在与最亲近的学生的书信中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
3
尽管钱穆在晚年之时对陈寅恪有所批评,但纵观两人所持的文化主张,却又是声气相通、引为同调的。
身处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面对滔天浊浪,不避不惧、有为有守,钱、陈两人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的精神守护重任,展示出来的文化品质与道德勇气,直可“惊天地,泣鬼神”。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但从总体看陈寅恪还是一位以传统价值观为评判标准的学者。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大的信心,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找到济世良药。他说:“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其中对于宋学的高度赞扬,更加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在清华大学创办二十周年之时,陈寅恪更是大声疾呼:“国可灭,而史不可灭。”
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看重,使陈寅恪对于违反传统的行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反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他对转源于汉魏正统文化之陇右、江左文化表现出了认同的态度,但是对于北周之以胡族习惯为主所构成的文化模式大不以为然,就因为它与传统汉文化有所不同,他蔑称之为“非驴非马”,非常不留情面。这些都从各个层面反映了陈寅恪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看重。陈门弟子蒋天枢曾评价乃师一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钱穆则宣称:“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长存于天地之间者。”
就治史旨趣而言,两人治史都特别注重种族(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文化决定种族。陈寅恪称“种族与文化”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统”。他的“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观点,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也多有阐述。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由中华民族所独创,中国人的民族观念与文化观念密切关联,其民族观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为其标准。他说:“在中国人观念中,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他们看重文化,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史上之所谓异民族,即无异于指著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团而言。”又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与陈寅恪的观点如出一辙。
4
两人都重视对民族文化作“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钱穆把这种“了解之同情”推及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宣称治史应“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在对待外来文化输入的态度上,两人的观点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有一段名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在1941年所写的《东西文化学社缘起》一文中说:“夫各民族文化进展,常需不断有去腐生新之势力,而欲求去腐生新,一面当不断从其文化源头作新鲜之认识,一面又当不断向外对异文化从事于尽量之吸收。”钱、陈观点之相同,不言自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上,两人皆主张以传统文化作为创造和发展新文化的主体,认定新文化只能从以往旧有文化中蕴孕生长,绝不能凭空翻新,绝无依傍。陈寅恪提出“新瓶装旧酒”的主张,钱穆则主张“据旧开新”“老干萌新芽”。
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陈寅恪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生命还重要,视其为做人的信仰和为学的准则。1953年,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思想,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氏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意在考察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的真实情况,“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钱穆认为研究学术“应自有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他治学不迎合时尚以轻弃己见,也不屈从政治、社会压力而作违心之论,更不随风而倒,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严肃性。《国史大纲》完稿交付出版后,有关审查部门要求他修改“洪杨之乱”章节,钱穆个性尽显,执意以原稿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