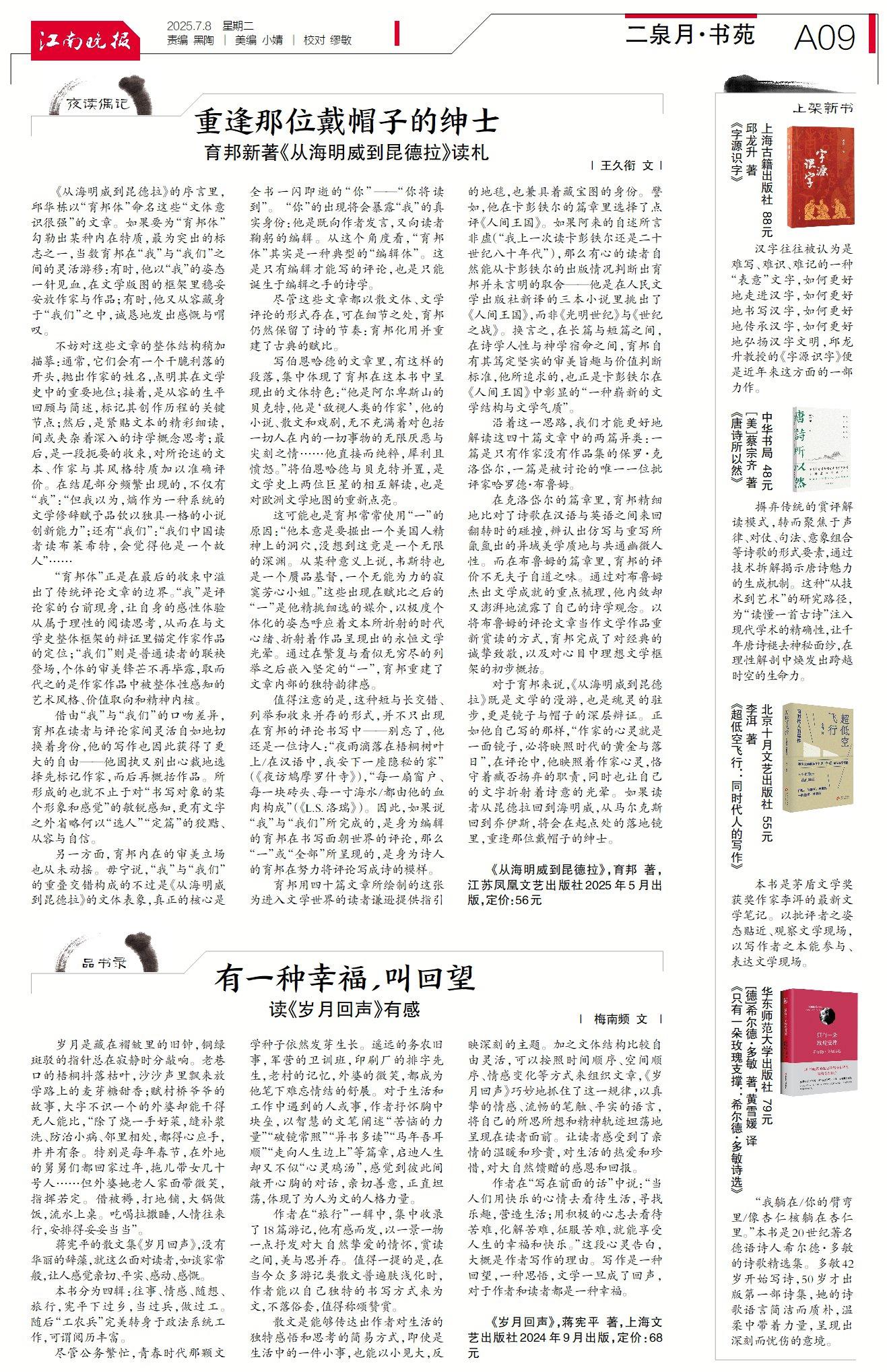| 王久衔 文 |
《从海明威到昆德拉》的序言里,邱华栋以“育邦体”命名这些“文体意识很强”的文章。如果要为“育邦体”勾勒出某种内在特质,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当数育邦在“我”与“我们”之间的灵活游移:有时,他以“我”的姿态一针见血,在文学版图的框架里稳妥安放作家与作品;有时,他又从容藏身于“我们”之中,诚恳地发出感慨与喟叹。
不妨对这些文章的整体结构稍加描摹:通常,它们会有一个干脆利落的开头,抛出作家的姓名,点明其在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接着,是从容的生平回顾与简述,标记其创作历程的关键节点;然后,是紧贴文本的精彩细读,间或夹杂着深入的诗学概念思考;最后,是一段扼要的收束,对所论述的文本、作家与其风格特质加以准确评价。在结尾部分频繁出现的,不仅有“我”:“但我以为,熵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学修辞赋予品钦以独具一格的小说创新能力”;还有“我们”:“我们中国读者读布莱希特,会觉得他是一个故人”……
“育邦体”正是在最后的收束中溢出了传统评论文章的边界。“我”是评论家的台前现身,让自身的感性体验从属于理性的阅读思考,从而在与文学史整体框架的辩证里锚定作家作品的定位;“我们”则是普通读者的联袂登场,个体的审美锋芒不再毕露,取而代之的是作家作品中被整体性感知的艺术风格、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
借由“我”与“我们”的口吻差异,育邦在读者与评论家间灵活自如地切换着身份,他的写作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固执又别出心裁地选择先标记作家,而后再概括作品。所形成的也就不止于对“书写对象的某个形象和感觉”的敏锐感知,更有文字之外省略何以“选人”“定篇”的狡黠、从容与自信。
另一方面,育邦内在的审美立场也从未动摇。毋宁说,“我”与“我们”的重叠交错构成的不过是《从海明威到昆德拉》的文体表象,真正的核心是全书一闪即逝的“你”——“你将读到”。 “你”的出现将会暴露“我”的真实身份:他是既向作者发言,又向读者鞠躬的编辑。从这个角度看,“育邦体”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编辑体”。这是只有编辑才能写的评论,也是只能诞生于编辑之手的诗学。
尽管这些文章都以散文体、文学评论的形式存在,可在细节之处,育邦仍然保留了诗的节奏:育邦化用并重建了古典的赋比。
写伯恩哈德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段落,集中体现了育邦在这本书中呈现出的文体特色:“他是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他是‘敌视人类的作家’,他的小说、散文和戏剧,无不充满着对包括一切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无限厌恶与尖刻之情……他直接而纯粹,犀利且愤怒。”将伯恩哈德与贝克特并置,是文学史上两位巨星的相互解读,也是对欧洲文学地图的重新点亮。
这可能也是育邦常常使用“一”的原因:“他本意是要掘出一个美国人精神上的洞穴,没想到这竟是一个无限的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说,韦斯特也是一个赝品基督,一个无能为力的寂寞芳心小姐。”这些出现在赋比之后的“一”是他精挑细选的媒介,以极度个体化的姿态呼应着文本所折射的时代心绪、折射着作品呈现出的永恒文学光晕。通过在繁复与看似无穷尽的列举之后嵌入坚定的“一”,育邦重建了文章内部的独特韵律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短与长交错、列举和收束并存的形式,并不只出现在育邦的评论书写中——别忘了,他还是一位诗人:“夜雨滴落在梧桐树叶上/在汉语中,我安下一座隐秘的家”(《夜访鸠摩罗什寺》),“每一扇窗户、每一块砖头、每一寸海水/都由他的血肉构成”(《L.S.洛瑞》)。因此,如果说“我”与“我们”所完成的,是身为编辑的育邦在书写面朝世界的评论,那么“一”或“全部”所呈现的,是身为诗人的育邦在努力将评论写成诗的模样。
育邦用四十篇文章所绘制的这张为进入文学世界的读者谦逊提供指引的地毯,也兼具着藏宝图的身份。譬如,他在卡彭铁尔的篇章里选择了点评《人间王国》。如果阿来的自述所言非虚(“我上一次读卡彭铁尔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么有心的读者自然能从卡彭铁尔的出版情况判断出育邦并未言明的取舍——他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译的三本小说里挑出了《人间王国》,而非《光明世纪》与《世纪之战》。换言之,在长篇与短篇之间,在诗学人性与神学宿命之间,育邦自有其笃定坚实的审美旨趣与价值判断标准,他所追求的,也正是卡彭铁尔在《人间王国》中彰显的“一种崭新的文学结构与文学气质”。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才能更好地解读这四十篇文章中的两篇异类:一篇是只有作家没有作品集的保罗·克洛岱尔,一篇是被讨论的唯一一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在克洛岱尔的篇章里,育邦精细地比对了诗歌在汉语与英语之间来回翻转时的碰撞,辨认出仿写与重写所氤氲出的异域美学质地与共通幽微人性。而在布鲁姆的篇章里,育邦的评价不无夫子自道之味。通过对布鲁姆杰出文学成就的重点梳理,他内敛却又澎湃地流露了自己的诗学观念。以将布鲁姆的评论文章当作文学作品重新赏读的方式,育邦完成了对经典的诚挚致敬,以及对心目中理想文学框架的初步概括。
对于育邦来说,《从海明威到昆德拉》既是文学的漫游,也是魂灵的驻步,更是镜子与帽子的深层辩证。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作家的心灵就是一面镜子,必将映照时代的黄金与落日”,在评论中,他映照着作家心灵,恪守着臧否扬弃的职责,同时也让自己的文字折射着诗意的光晕。如果读者从昆德拉回到海明威,从马尔克斯回到乔伊斯,将会在起点处的落地镜里,重逢那位戴帽子的绅士。
《从海明威到昆德拉》,育邦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定价:5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