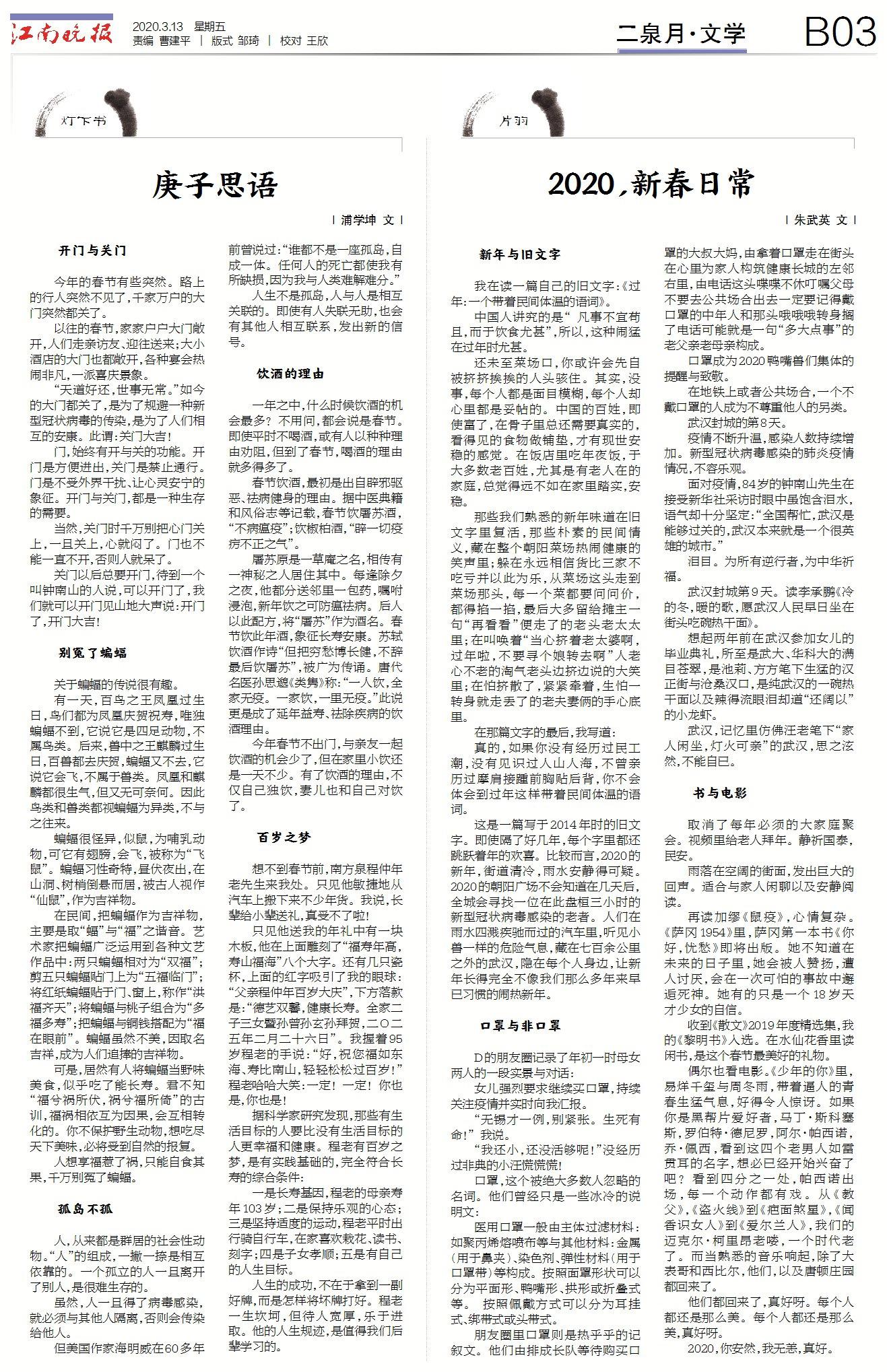| 朱武英 文 |
新年与旧文字
我在读一篇自己的旧文字:《过年:一个带着民间体温的语词》。
中国人讲究的是“ 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所以,这种闹猛在过年时尤甚。
还未至菜场口,你或许会先自被挤挤挨挨的人头骇住。其实,没事,每个人都是面目模糊,每个人却心里都是妥帖的。中国的百姓,即使富了,在骨子里总还需要真实的,看得见的食物做铺垫,才有现世安稳的感觉。在饭店里吃年夜饭,于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有老人在的家庭,总觉得远不如在家里踏实,安稳。
那些我们熟悉的新年味道在旧文字里复活,那些朴素的民间情义,藏在整个朝阳菜场热闹健康的笑声里;躲在永远相信货比三家不吃亏并以此为乐,从菜场这头走到菜场那头,每一个菜都要问问价,都得掐一掐,最后大多留给摊主一句“再看看”便走了的老头老太太里;在叫唤着“当心挤着老太婆啊,过年啦,不要寻个娘转去啊”人老心不老的淘气老头边挤边说的大笑里;在怕挤散了,紧紧牵着,生怕一转身就走丢了的老夫妻俩的手心底里。
在那篇文字的最后,我写道:
真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民工潮,没有见识过人山人海,不曾亲历过摩肩接踵前胸贴后背,你不会体会到过年这样带着民间体温的语词。
这是一篇写于2014年时的旧文字。即使隔了好几年,每个字里都还跳跃着年的欢喜。比较而言,2020的新年,街道清冷,雨水安静得可疑。2020的朝阳广场不会知道在几天后,全城会寻找一位在此盘桓三小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老者。人们在雨水四溅疾驰而过的汽车里,听见小兽一样的危险气息,藏在七百余公里之外的武汉,隐在每个人身边,让新年长得完全不像我们那么多年来早已习惯的闹热新年。
口罩与非口罩
D的朋友圈记录了年初一时母女两人的一段实景与对话:
女儿强烈要求继续买口罩,持续关注疫情并实时向我汇报。
“无锡才一例,别紧张。生死有命!” 我说。
“我还小,还没活够呢!”没经历过非典的小汪慌慌慌!
口罩,这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名词。他们曾经只是一些冰冷的说明文:
医用口罩一般由主体过滤材料:如聚丙烯熔喷布等与其他材料:金属(用于鼻夹)、染色剂、弹性材料(用于口罩带)等构成。按照面罩形状可以分为平面形、鸭嘴形、拱形或折叠式等。 按照佩戴方式可以分为耳挂式、绑带式或头带式。
朋友圈里口罩则是热乎乎的记叙文。他们由排成长队等待购买口罩的大叔大妈,由拿着口罩走在街头在心里为家人构筑健康长城的左邻右里,由电话这头喋喋不休叮嘱父母不要去公共场合出去一定要记得戴口罩的中年人和那头哦哦哦转身搁了电话可能就是一句“多大点事”的老父亲老母亲构成。
口罩成为2020鸭嘴兽们集体的提醒与致敬。
在地铁上或者公共场合,一个不戴口罩的人成为不尊重他人的另类。
武汉封城的第8天。
疫情不断升温,感染人数持续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不容乐观。
面对疫情,84岁的钟南山先生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眼中虽饱含泪水,语气却十分坚定:“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泪目。为所有逆行者,为中华祈福。
武汉封城第9天。读李承鹏《冷的冬,暖的歌,愿武汉人民早日坐在街头吃碗热干面》。
想起两年前在武汉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所至是武大、华科大的满目苍翠,是池莉、方方笔下生猛的汉正街与沧桑汉口,是纯武汉的一碗热干面以及辣得流眼泪却道“还阔以”的小龙虾。
武汉,记忆里仿佛汪老笔下“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武汉,思之泫然,不能自已。
书与电影
取消了每年必须的大家庭聚会。视频里给老人拜年。静祈国泰,民安。
雨落在空阔的街面,发出巨大的回声。适合与家人闲聊以及安静阅读。
再读加缪《鼠疫》,心情复杂。《萨冈1954》里,萨冈第一本书《你好,忧愁》即将出版。她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被人赞扬,遭人讨厌,会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中邂逅死神。她有的只是一个18岁天才少女的自信。
收到《散文》2019年度精选集,我的《黎明书》入选。在水仙花香里读闲书,是这个春节最美好的礼物。
偶尔也看电影。《少年的你》里,易烊千玺与周冬雨,带着逼人的青春生猛气息,好得令人惊讶。如果你是黑帮片爱好者,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乔·佩西,看到这四个老男人如雷贯耳的名字,想必已经开始兴奋了吧?看到四分之一处,帕西诺出场,每一个动作都有戏。从《教父》,《盗火线》到《疤面煞星》,《闻香识女人》到《爱尔兰人》,我们的迈克尔·柯里昂老喽,一个时代老了。而当熟悉的音乐响起,除了大表哥和西比尔,他们,以及唐顿庄园都回来了。
他们都回来了,真好呀。每个人都还是那么美。每个人都还是那么美,真好呀。
2020,你安然,我无恙,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