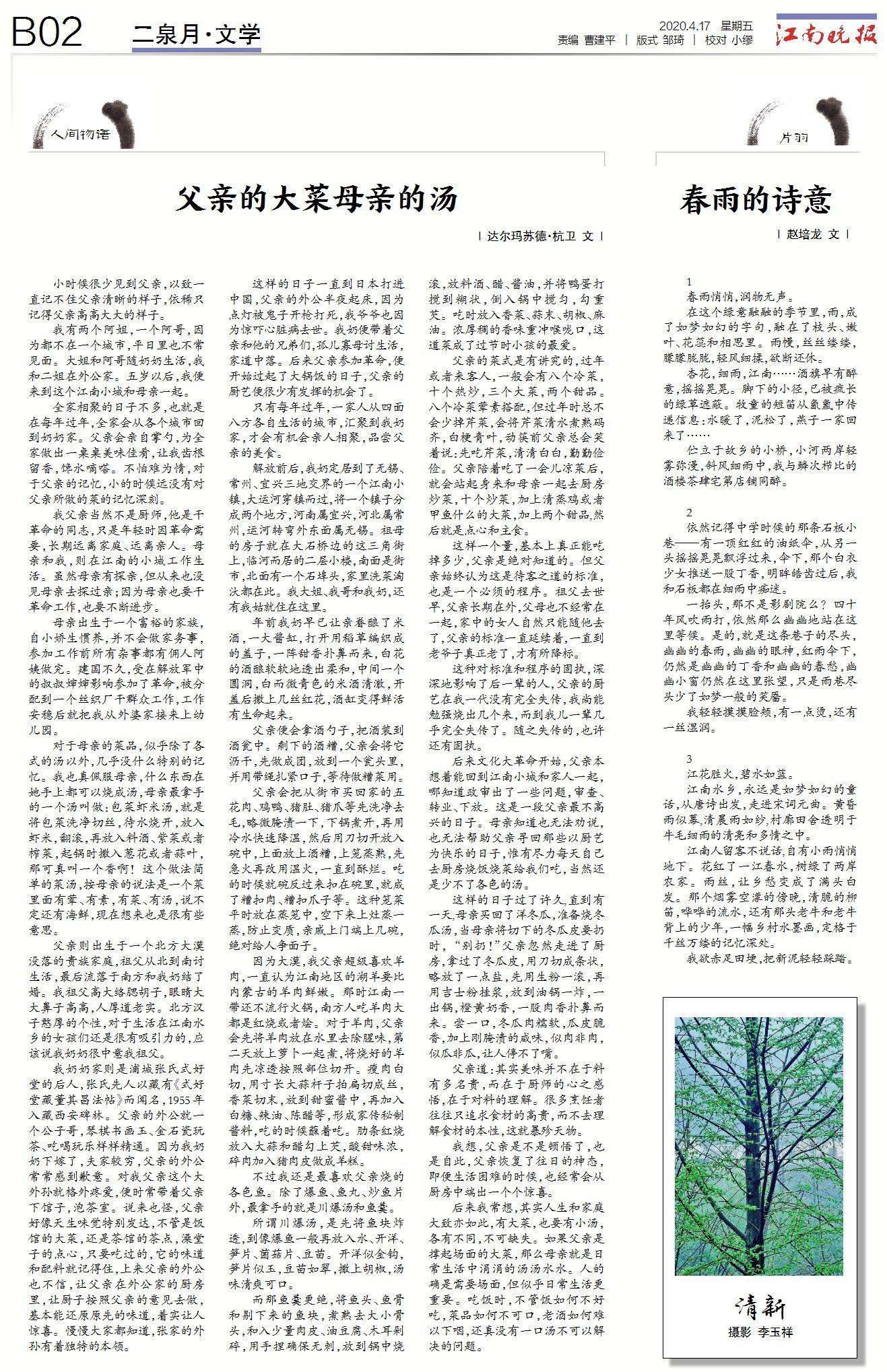| 达尔玛苏德·杭卫 文 |
小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以致一直记不住父亲清晰的样子,依稀只记得父亲高高大大的样子。
我有两个阿姐,一个阿哥,因为都不在一个城市,平日里也不常见面。大姐和阿哥随奶奶生活,我和二姐在外公家。五岁以后,我便来到这个江南小城和母亲一起。
全家相聚的日子不多,也就是在每年过年,全家会从各个城市回到奶奶家。父亲会亲自掌勺,为全家做出一桌桌美味佳肴,让我齿根留香,馋水嘀嗒。不怕难为情,对于父亲的记忆,小的时候远没有对父亲所做的菜的记忆深刻。
我父亲当然不是厨师,他是干革命的同志,只是年轻时因革命需要,长期远离家庭、远离亲人。母亲和我,则在江南的小城工作生活。虽然母亲有探亲,但从来也没见母亲去探过亲;因为母亲也要干革命工作,也要不断进步。
母亲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族,自小娇生惯养,并不会做家务事,参加工作前所有杂事都有佣人阿姨做完。建国不久,受在解放军中的叔叔婶婶影响参加了革命,被分配到一个丝织厂干群众工作,工作安稳后就把我从外婆家接来上幼儿园。
对于母亲的菜品,似乎除了各式的汤以外,几乎没什么特别的记忆。我也真佩服母亲,什么东西在她手上都可以烧成汤,母亲最拿手的一个汤叫做:包菜虾米汤,就是将包菜洗净切丝,待水烧开,放入虾米,翻滚,再放入料酒、紫菜或者榨菜,起锅时撒入葱花或者蒜叶,那可真叫一个香啊!这个做法简单的菜汤,按母亲的说法是一个菜里面有荤、有素,有菜、有汤,说不定还有海鲜,现在想来也是很有些意思。
父亲则出生于一个北方大漠没落的贵族家庭,祖父从北到南讨生活,最后流落于南方和我奶结了婚。我祖父高大络腮胡子,眼睛大大鼻子高高,人厚道老实。北方汉子憨厚的个性,对于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女孩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应该说我奶奶很中意我祖父。
我奶奶家则是浦城张氏式好堂的后人,张氏先人以藏有《式好堂藏董其昌法帖》而闻名,1955年入藏西安碑林。父亲的外公就一个公子哥,琴棋书画玉、金石瓷玩茶、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因为我奶奶下嫁了,夫家较穷,父亲的外公常常感到歉意。对我父亲这个大外孙就格外疼爱,便时常带着父亲下馆子,泡茶室。说来也怪,父亲好像天生味觉特别发达,不管是饭馆的大菜,还是茶馆的茶点,澡堂子的点心,只要吃过的,它的味道和配料就记得住,上来父亲的外公也不信,让父亲在外公家的厨房里,让厨子按照父亲的意见去做,基本能还原原先的味道,着实让人惊喜。慢慢大家都知道,张家的外孙有着独特的本领。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日本打进中国,父亲的外公半夜起床,因为点灯被鬼子开枪打死,我爷爷也因为惊吓心脏病去世。我奶便带着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孤儿寡母讨生活,家道中落。后来父亲参加革命,便开始过起了大锅饭的日子,父亲的厨艺便很少有发挥的机会了。
只有每年过年,一家人从四面八方各自生活的城市,汇聚到我奶家,才会有机会亲人相聚,品尝父亲的美食。
解放前后,我奶定居到了无锡、常州、宜兴三地交界的一个江南小镇,大运河穿镇而过,将一个镇子分成两个地方,河南属宜兴,河北属常州,运河转弯外东面属无锡。祖母的房子就在大石桥边的这三角街上,临河而居的二层小楼,南面是街市,北面有一个石埠头,家里洗菜淘汏都在此。我大姐、我哥和我奶,还有我姑就住在这里。
年前我奶早已让亲眷酿了米酒,一大酱缸,打开用稻草编织成的盖子,一阵甜香扑鼻而来,白花的酒酿软软地透出柔和,中间一个圆洞,白而微青色的米酒清澈,开盖后撒上几丝红花,酒缸变得鲜活有生命起来。
父亲便会拿酒勺子,把酒装到酒瓮中。剩下的酒糟,父亲会将它沥干,先做成团,放到一个瓮头里,并用带绳扎紧口子,等待做糟菜用。
父亲会把从街市买回家的五花肉、鸡鸭、猪肚、猪爪等先洗净去毛,略微腌渍一下,下锅煮开,再用冷水快速降温,然后用刀切开放入碗中,上面放上酒糟,上笼蒸熟,先急火再改用温火,一直到酥烂。吃的时候就碗反过来扣在碗里,就成了糟扣肉、糟扣爪子等。这种笼菜平时放在蒸笼中,空下来上灶蒸一蒸,防止变质,亲戚上门端上几碗,绝对给人争面子。
因为大漠,我父亲超级喜欢羊肉,一直认为江南地区的湖羊要比内蒙古的羊肉鲜嫩。那时江南一带还不流行火锅,南方人吃羊肉大都是红烧或者烩。对于羊肉,父亲会先将羊肉放在水里去除腥味,第二天放上萝卜一起煮,将烧好的羊肉先凉透按照部位切开。瘦肉白切,用寸长大蒜杆子拍扁切成丝,香菜切末,放到甜蜜酱中,再加入白糖、辣油、陈醋等,形成家传秘制酱料,吃的时候蘸着吃。肋条红烧放入大蒜和醋勾上芡,酸甜味浓,碎肉加入猪肉皮做成羊糕。
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父亲烧的各色鱼。除了爆鱼、鱼丸、炒鱼片外,最拿手的就是川爆汤和鱼羹。
所谓川爆汤,是先将鱼块炸透,到像爆鱼一般再放入水、开洋、笋片、菌菇片、豆苗。开洋似金钩,笋片似玉,豆苗如翠,撒上胡椒,汤味清爽可口。
而那鱼羹更绝,将鱼头、鱼骨和剔下来的鱼块,煮熟去大小骨头,和入少量肉皮、油豆腐、木耳剁碎,用手捏确保无刺,放到锅中烧滚,放料酒、醋、酱油,并将鸭蛋打搅到糊状,倒入锅中搅匀,勾重芡。吃时放入香菜、蒜末、胡椒、麻油。浓厚稠的香味重冲喉咙口,这道菜成了过节时小孩的最爱。
父亲的菜式是有讲究的,过年或者来客人,一般会有八个冷菜,十个热炒,三个大菜,两个甜品。八个冷菜荤素搭配,但过年时总不会少掉芹菜,会将芹菜清水煮熟码齐,白梗青叶,动筷前父亲总会笑着说:先吃芹菜,清清白白,勤勤俭俭。父亲陪着吃了一会儿凉菜后,就会站起身来和母亲一起去厨房炒菜,十个炒菜,加上清蒸鸡或者甲鱼什么的大菜,加上两个甜品,然后就是点心和主食。
这样一个量,基本上真正能吃掉多少,父亲是绝对知道的。但父亲始终认为这是待客之道的标准,也是一个必须的程序。祖父去世早,父亲长期在外,父母也不经常在一起,家中的女人自然只能随他去了,父亲的标准一直延续着,一直到老爷子真正老了,才有所降标。
这种对标准和程序的固执,深深地影响了后一辈的人,父亲的厨艺在我一代没有完全失传,我尚能勉强烧出几个来,而到我儿一辈几乎完全失传了。随之失传的,也许还有固执。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本想着能回到江南小城和家人一起,哪知道政审出了一些问题,审查、转业、下放。这是一段父亲最不高兴的日子。母亲知道也无法劝说,也无法帮助父亲寻回那些以厨艺为快乐的日子,惟有尽力每天自己去厨房烧饭烧菜给我们吃,当然还是少不了各色的汤。
这样的日子过了许久,直到有一天,母亲买回了洋冬瓜,准备烧冬瓜汤,当母亲将切下的冬瓜皮要扔时, “别扔!”父亲忽然走进了厨房,拿过了冬瓜皮,用刀切成条状,略放了一点盐,先用生粉一滚,再用吉士粉挂浆,放到油锅一炸,一出锅,橙黄奶香,一股肉香扑鼻而来。尝一口,冬瓜肉糯软,瓜皮脆香,加上刚腌渍的咸味,似肉非肉,似瓜非瓜,让人停不了嘴。
父亲道:其实美味并不在于料有多名贵,而在于厨师的心之感悟,在于对料的理解。很多烹饪者往往只追求食材的高贵,而不去理解食材的本性,这就暴殄天物。
我想,父亲是不是顿悟了,也是自此,父亲恢复了往日的神态,即便生活困难的时候,也经常会从厨房中端出一个个惊喜。
后来我常想,其实人生和家庭大致亦如此,有大菜,也要有小汤,各有不同,不可缺失。如果父亲是撑起场面的大菜,那么母亲就是日常生活中涓涓的汤汤水水。人的确是需要场面,但似乎日常生活更重要。吃饭时,不管饭如何不好吃,菜品如何不可口,老酒如何难以下咽,还真没有一口汤不可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