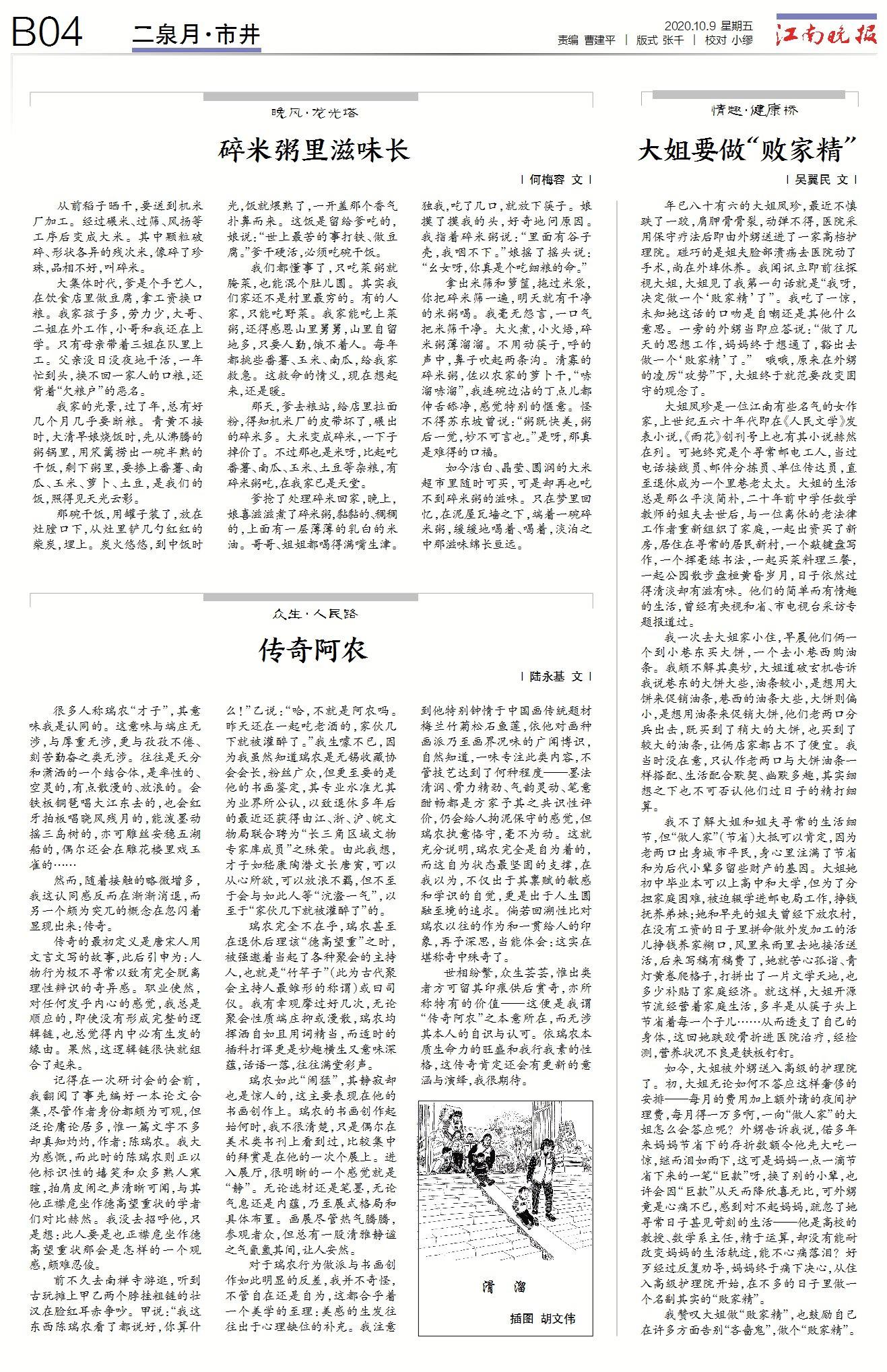| 陆永基 文 |
很多人称瑞农“才子”,其意味我是认同的。这意味与端庄无涉,与厚重无涉,更与孜孜不倦、刻苦勤奋之类无涉。往往是天分和潇洒的一个结合体,是率性的、空灵的,有点散漫的、放浪的。会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也会红牙拍板唱晓风残月的,能泼墨动摇三岛树的,亦可雕丝安稳五湖船的,偶尔还会在雕花楼里戏玉雀的……
然而,随着接触的略微增多,我这认同感反而在渐渐消退,而另一个颇为突兀的概念在忽闪着显现出来:传奇。
传奇的最初定义是唐宋人用文言文写的故事,此后引申为:人物行为极不寻常以致有完全脱离理性辨识的奇异感。职业使然,对任何发乎内心的感觉,我总是顺应的,即使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链,也总觉得内中必有生发的缘由。果然,这逻辑链很快就组合了起来。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的会前,我翻阅了事先编好一本论文合集,尽管作者身份都颇为可观,但泛论庸论居多,惟一篇文字不多却真知灼灼,作者:陈瑞农。我大为感慨,而此时的陈瑞农则正以他标识性的嬉笑和众多熟人寒暄,拍肩皮闹之声清晰可闻,与其他正襟危坐作德高望重状的学者们对比赫然。我没去招呼他,只是想:此人要是也正襟危坐作德高望重状那会是怎样的一个观感,颇难忍俊。
前不久去南禅寺游逛,听到古玩摊上甲乙两个脖挂粗链的壮汉在脸红耳赤争吵。甲说:“我这东西陈瑞农看了都说好,你算什么!”乙说:“哈,不就是阿农吗。昨天还在一起吃老酒的,家伙几下就被灌醉了。”我生噱不已,因为我虽然知道瑞农是无锡收藏协会会长,粉丝广众,但更至要的是他的书画鉴定,其专业水准尤其为业界所公认,以致退休多年后的最近还获得由江、浙、沪、皖文物局联合聘为“长三角区域文物专家库成员”之殊荣。由此我想,才子如嵇康陶潜文长唐寅,可以从心所欲,可以放浪不羁,但不至于会与如此人等“沆瀣一气”,以至于“家伙几下就被灌醉了”的。
瑞农完全不在乎,瑞农甚至在退休后理该“德高望重”之时,被强邀着当起了各种聚会的主持人,也就是“竹竿子”(此为古代聚会主持人最雏形的称谓)或曰司仪。我有幸观摩过好几次,无论聚会性质端庄抑或漫散,瑞农均挥洒自如且用词精当,而适时的插科打诨更是妙趣横生又意味深蕴,话语一落,往往满堂彩声。
瑞农如此“闹猛”,其静寂却也是惊人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书画创作上。瑞农的书画创作起始何时,我不很清楚,只是偶尔在美术类书刊上看到过,比较集中的拜赏是在他的一次个展上。进入展厅,很明晰的一个感觉就是“静”。无论选材还是笔墨,无论气息还是内蕴,乃至展式格局和具体布置。画展尽管热气腾腾,参观者众,但总有一股清雅静谧之气氤氲其间,让人安然。
对于瑞农行为做派与书画创作如此明显的反差,我并不奇怪,不管自在还是自为,这都合乎着一个美学的至理:美感的生发往往出于心理缺位的补充。我注意到他特别钟情于中国画传统题材梅兰竹菊松石鱼莲,依他对画种画派乃至画界况味的广闻博识,自然知道,一味专注此类内容,不管技艺达到了何种程度——墨法清润、骨力精劲、气韵灵动、笔意酣畅都是方家予其之共识性评价,仍会给人拘泥保守的感觉,但瑞农执意恪守,毫不为动。这就充分说明,瑞农完全是自为着的,而这自为状态最坚固的支撑,在我以为,不仅出于其禀赋的敏感和学识的自觉,更是出于人生圆融至境的追求。倘若回溯性比对瑞农以往的作为和一贯给人的印象,再予深思,当能体会:这实在堪称奇中殊奇了。
世相纷繁,众生芸芸,惟出类者方可留其印痕供后赏奇,亦所称特有的价值——这便是我谓“传奇阿农”之本意所在,而无涉其本人的自识与认可。依瑞农本质生命力的旺盛和我行我素的性格,这传奇肯定还会有更新的意涵与演绎,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