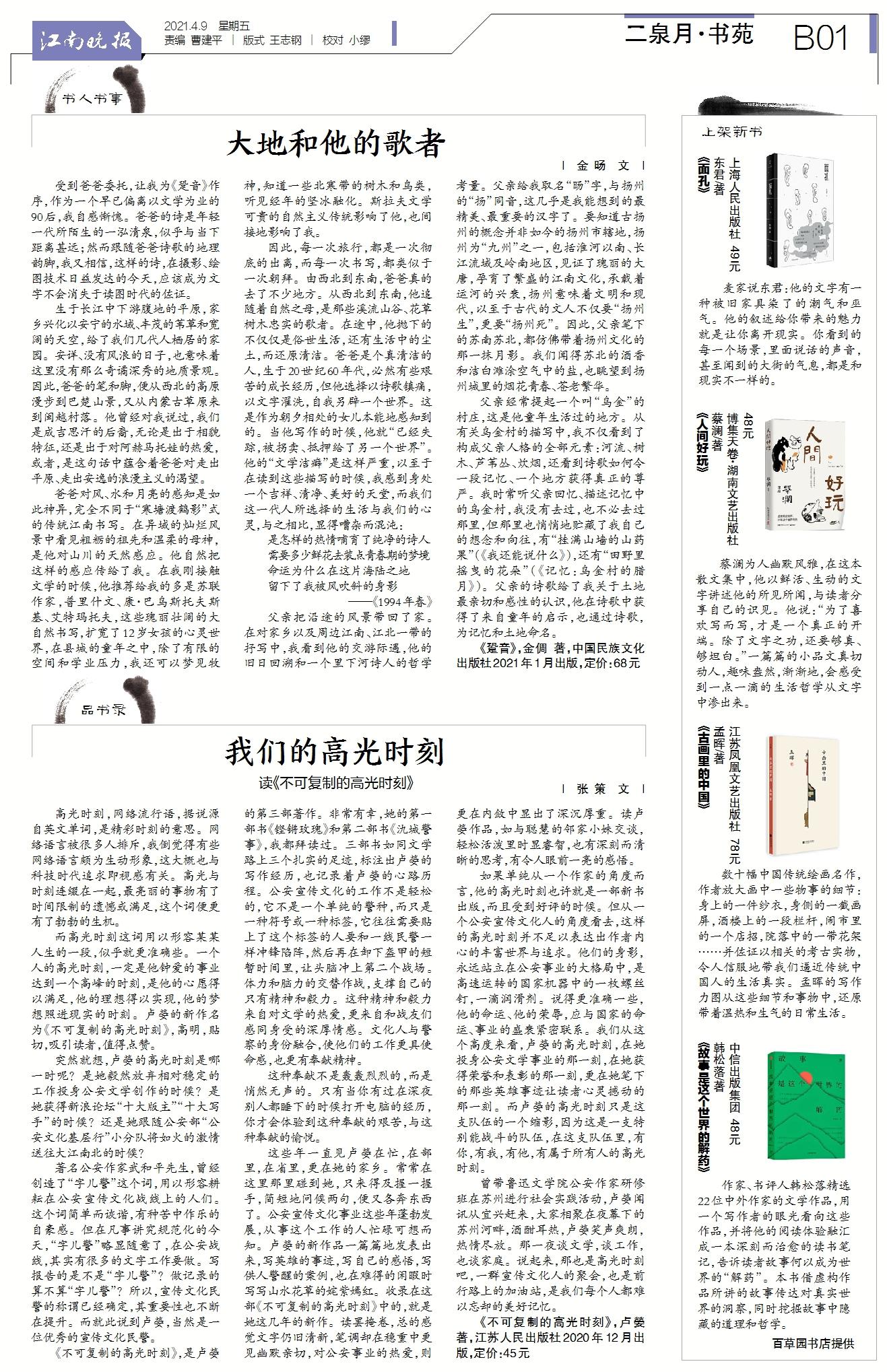| 金 旸 文 |
受到爸爸委托,让我为《跫音》作序,作为一个早已偏离以文学为业的 90后,我自感惭愧。爸爸的诗是年轻一代所陌生的一泓清泉,似乎与当下距离甚远;然而跟随爸爸诗歌的地理韵脚,我又相信,这样的诗,在摄影、绘图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应该成为文字不会消失于读图时代的佐证。
生于长江中下游腹地的平原,家乡兴化以安宁的水域、丰茂的苇草和宽阔的天空,给了我们几代人栖居的家园。安详、没有风浪的日子,也意味着这里没有那么奇谲深秀的地质景观。因此,爸爸的笔和脚,便从西北的高原漫步到巴楚山景,又从内蒙古草原来到闽越村落。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无论是出于相貌特征,还是出于对阿赫马托娃的热爱,或者,是这句话中蕴含着爸爸对走出平原、走出安逸的浪漫主义的渴望。
爸爸对风、水和月亮的感知是如此神异,完全不同于“寒塘渡鹤影”式的传统江南书写。在异域的灿烂风景中看见粗粝的祖先和温柔的母神,是他对山川的天然感应。他自然把这样的感应传给了我。在我刚接触文学的时候,他推荐给我的多是苏联作家,普里什文、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艾特玛托夫,这些瑰丽壮阔的大自然书写,扩宽了12岁女孩的心灵世界,在县城的童年之中,除了有限的空间和学业压力,我还可以梦见牧神,知道一些北寒带的树木和鸟类,听见经年的坚冰融化。斯拉夫文学可贵的自然主义传统影响了他,也间接地影响了我。
因此,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彻底的出离,而每一次书写,都类似于一次朝拜。由西北到东南,爸爸真的去了不少地方。从西北到东南,他追随着自然之母,是那些溪流山谷、花草树木忠实的歌者。在途中,他抛下的不仅仅是俗世生活,还有生活中的尘土,而还原清洁。爸爸是个真清洁的人,生于20世纪60年代,必然有些艰苦的成长经历,但他选择以诗歌镇痛,以文字濯洗,自我另辟一个世界。这是作为朝夕相处的女儿本能地感知到的。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踪,被拐卖、抵押给了另一个世界”。他的“文学洁癖”是这样严重,以至于在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我感到身处一个吉祥、清净、美好的天堂,而我们这一代人所选择的生活与我们的心灵,与之相比,显得嘈杂而混沌:
是怎样的热情哺育了纯净的诗人
需要多少鲜花去装点青春期的梦境
命运为什么在这片海陆之地
留下了我被风吹斜的身影
——《1994年春》
父亲把沿途的风景带回了家。在对家乡以及周边江南、江北一带的抒写中,我看到他的交游际遇,他的旧日回溯和一个里下河诗人的哲学考量。父亲给我取名“旸”字,与扬州的“扬”同音,这几乎是我能想到的最精美、最重要的汉字了。要知道古扬州的概念并非如今的扬州市辖地,扬州为“九州”之一,包括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见证了瑰丽的大唐,孕育了繁盛的江南文化,承载着运河的兴衰,扬州意味着文明和现代,以至于古代的文人不仅要“扬州生”,更要“扬州死”。因此,父亲笔下的苏南苏北,都仿佛带着扬州文化的那一抹月影。我们闻得苏北的酒香和洁白滩涂空气中的盐,也眺望到扬州城里的烟花青春、苍老繁华。
父亲经常提起一个叫“乌金”的村庄,这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从有关乌金村的描写中,我不仅看到了构成父亲人格的全部元素:河流、树木、芦苇丛、炊烟,还看到诗歌如何令一段记忆、一个地方获得真正的尊严。我时常听父亲回忆、描述记忆中的乌金村,我没有去过,也不必去过那里,但那里也悄悄地贮藏了我自己的想念和向往,有“挂满山墙的山药果”(《我还能说什么》),还有“田野里摇曳的花朵”(《记忆:乌金村的腊月》)。父亲的诗歌给了我关于土地最亲切和感性的认识,他在诗歌中获得了来自童年的启示,也通过诗歌,为记忆和土地命名。
《跫音》,金倜 著,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