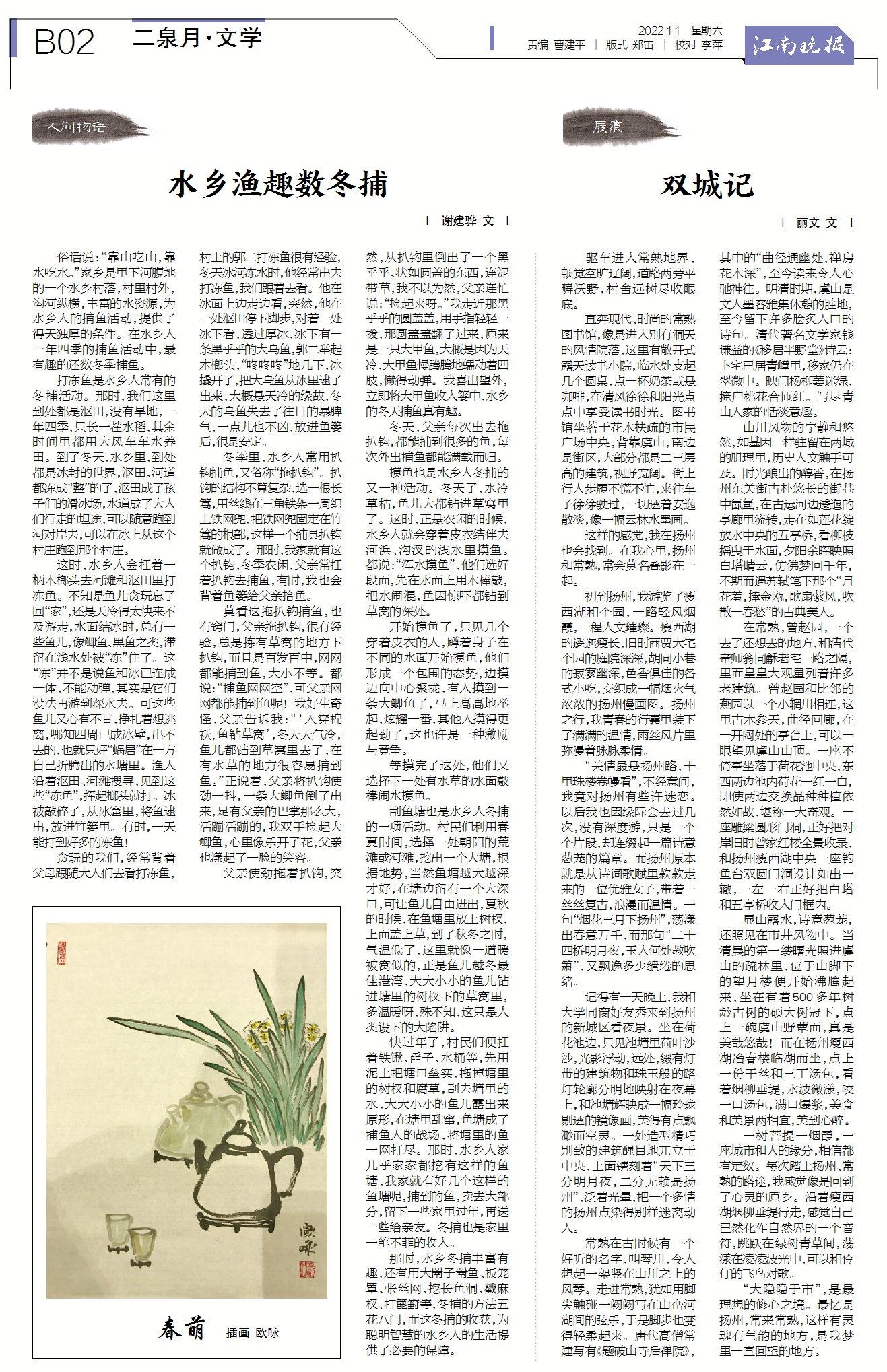| 丽文 文 |
驱车进入常熟地界,顿觉空旷辽阔,道路两旁平畴沃野,村舍远树尽收眼底。
直奔现代、时尚的常熟图书馆,像是进入别有洞天的风情院落,这里有敞开式露天读书小院,临水处支起几个圆桌,点一杯奶茶或是咖啡,在清风徐徐和阳光点点中享受读书时光。图书馆坐落于花木扶疏的市民广场中央,背靠虞山,南边是街区,大部分都是二三层高的建筑,视野宽阔。街上行人步履不慌不忙,来往车子徐徐驶过,一切透着安逸散淡,像一幅云林水墨画。
这样的感觉,我在扬州也会找到。在我心里,扬州和常熟,常会莫名叠影在一起。
初到扬州,我游览了瘦西湖和个园,一路轻风烟霞,一程人文璀璨。瘦西湖的逶迤瘦长,旧时商贾大宅个园的庭院深深,胡同小巷的寂寥幽深,色香俱佳的各式小吃,交织成一幅烟火气浓浓的扬州慢画图。扬州之行,我青春的行囊里装下了满满的温情,雨丝风片里弥漫着脉脉柔情。
“关情最是扬州路,十里珠楼卷幔看”,不经意间,我竟对扬州有些许迷恋。以后我也因缘际会去过几次,没有深度游,只是一个个片段,却连缀起一篇诗意葱茏的篇章。而扬州原本就是从诗词歌赋里款款走来的一位优雅女子,带着一丝丝复古,浪漫而温情。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荡漾出春意万千,而那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又飘逸多少缱绻的思绪。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大学同窗好友秀来到扬州的新城区看夜景。坐在荷花池边,只见池塘里荷叶沙沙,光影浮动,远处,缀有灯带的建筑物和珠玉般的路灯轮廓分明地映射在夜幕上,和池塘辉映成一幅玲珑剔透的镜像画,美得有点飘渺而空灵。一处造型精巧别致的建筑醒目地兀立于中央,上面镌刻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泛着光晕,把一个多情的扬州点染得别样迷离动人。
常熟在古时候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琴川,令人想起一架竖在山川之上的风琴。走进常熟,犹如用脚尖触碰一阙阙写在山峦河湖间的弦乐,于是脚步也变得轻柔起来。唐代高僧常建写有《题破山寺后禅院》,其中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令人心驰神往。明清时期,虞山是文人墨客雅集休憩的胜地,至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清代著名文学家钱谦益的《移居半野堂》诗云:卜宅已居青嶂里,移家仍在翠微中。映门杨柳萋迷绿,掩户桃花合匝红。写尽青山人家的恬淡意趣。
山川风物的宁静和悠然,如基因一样驻留在两城的肌理里,历史人文触手可及。时光酿出的醇香,在扬州东关街古朴悠长的街巷中氤氲,在古运河边逶迤的亭廊里流转,走在如莲花绽放水中央的五亭桥,看柳枝摇曳于水面,夕阳余晖映照白塔晴云,仿佛梦回千年,不期而遇苏轼笔下那个“月花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的古典美人。
在常熟,曾赵园,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和清代帝师翁同龢老宅一路之隔,里面皇皇大观星列着许多老建筑。曾赵园和比邻的燕园以一个小辋川相连,这里古木参天,曲径回廊,在一开阔处的亭台上,可以一眼望见虞山山顶。一座不倚亭坐落于荷花池中央,东西两边池内荷花一红一白,即使两边交换品种种植依然如故,堪称一大奇观。一座雕梁圆形门洞,正好把对岸旧时曾家红楼全景收录,和扬州瘦西湖中央一座钓鱼台双圆门洞设计如出一辙,一左一右正好把白塔和五亭桥收入门框内。
显山露水,诗意葱茏,还照见在市井风物中。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照进虞山的疏林里,位于山脚下的望月楼便开始沸腾起来,坐在有着500多年树龄古树的硕大树冠下,点上一碗虞山野蕈面,真是美哉悠哉!而在扬州瘦西湖冶春楼临湖而坐,点上一份干丝和三丁汤包,看着烟柳垂堤,水波微漾,咬一口汤包,满口爆浆,美食和美景两相宜,美到心醉。
一树菩提一烟霞,一座城市和人的缘分,相信都有定数。每次踏上扬州、常熟的路途,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心灵的原乡。沿着瘦西湖烟柳垂堤行走,感觉自己已然化作自然界的一个音符,跳跃在绿树青草间,荡漾在凌凌波光中,可以和伶仃的飞鸟对歌。
“大隐隐于市”,是最理想的修心之境。最忆是扬州,常来常熟,这样有灵魂有气韵的地方,是我梦里一直回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