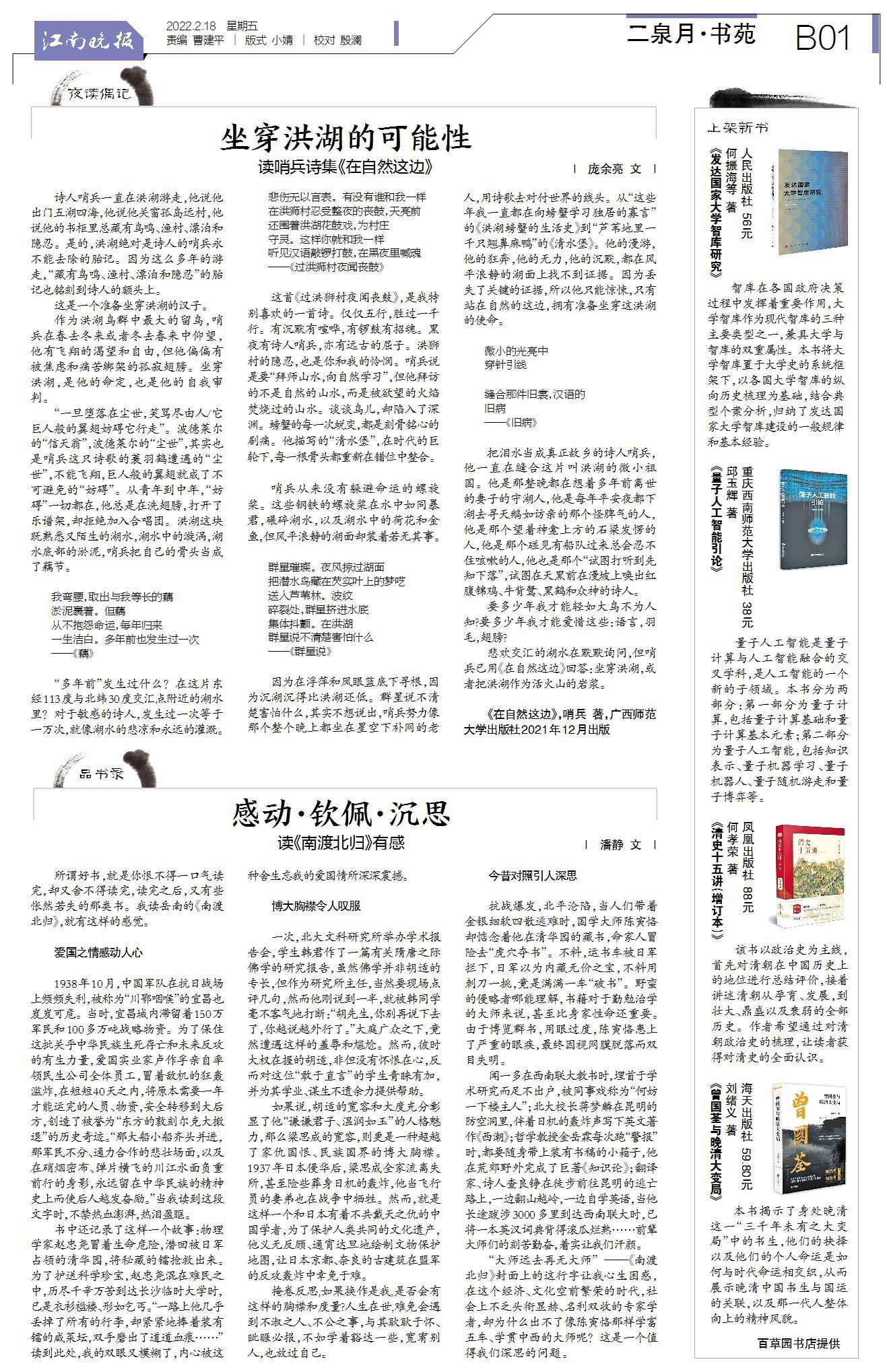| 潘静 文 |
所谓好书,就是你恨不得一口气读完,却又舍不得读完,读完之后,又有些怅然若失的那类书。我读岳南的《南渡北归》,就有这样的感觉。
爱国之情感动人心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频频失利,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也岌岌可危。当时,宜昌城内滞留着150万军民和100多万吨战略物资。为了保住这批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亲自率领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在短短40天之内,将原本需要一年才能运完的人员、物资,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创造了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历史奇迹。“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悲壮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禁热血澎湃,热泪盈眶。
书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潜回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将秘藏的镭抢救出来。为了护送科学珍宝,赵忠尧混在难民之中,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时,已是衣衫褴褛、形如乞丐。“一路上他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却紧紧地捧着装有镭的咸菜坛,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读到此处,我的双眼又模糊了,内心被这种舍生忘我的爱国情所深深震撼。
博大胸襟令人叹服
一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办学术报告会,学生韩君作了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虽然佛学并非胡适的专长,但作为研究所主任,当然要现场点评几句,然而他刚说到一半,就被韩同学毫不客气地打断:“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大庭广众之下,竟然遭遇这样的羞辱和尴尬。然而,彼时大权在握的胡适,非但没有怀恨在心,反而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学生青睐有加,并为其学业、谋生不遗余力提供帮助。
如果说,胡适的宽容和大度充分彰显了他“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那么梁思成的宽容,则更是一种超越了家仇国恨、民族国界的博大胸襟。1937年日本侵华后,梁思成全家流离失所,甚至险些葬身日机的轰炸,他当飞行员的妻弟也在战争中牺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和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学者,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他义无反顾、通宵达旦地绘制文物保护地图,让日本京都、奈良的古建筑在盟军的反攻轰炸中幸免于难。
掩卷反思,如果换作是我,是否会有这样的胸襟和度量?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淑之人、不公之事,与其耿耿于怀、眦睚必报,不如学着豁达一些,宽宥别人,也放过自己。
今昔对照引人深思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当人们带着金银细软四散逃难时,国学大师陈寅恪却惦念着他在清华园的藏书,命家人冒险去“虎穴夺书”。不料,运书车被日军拦下,日军以为内藏无价之宝,不料用刺刀一挑,竟是满满一车“破书”。野蛮的侵略者哪能理解,书籍对于勤勉治学的大师来说,甚至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由于博览群书,用眼过度,陈寅恪患上了严重的眼疾,最终因视网膜脱落而双目失明。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埋首于学术研究而足不出户,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昆明的防空洞里,伴着日机的轰炸声写下英文著作《西潮》;哲学教授金岳霖每次跑“警报”时,都要随身带上装有书稿的小箱子,他在荒郊野外完成了巨著《知识论》;翻译家、诗人查良铮在徒步前往昆明的逃亡路上,一边翻山越岭,一边自学英语,当他长途跋涉3000多里到达西南联大时,已将一本英汉词典背得滚瓜烂熟……前辈大师们的刻苦勤奋,着实让我们汗颜。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南渡北归》封面上的这行字让我心生困惑,在这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社会上不乏头衔显赫、名利双收的专家学者,却为什么出不了像陈寅恪那样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的大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