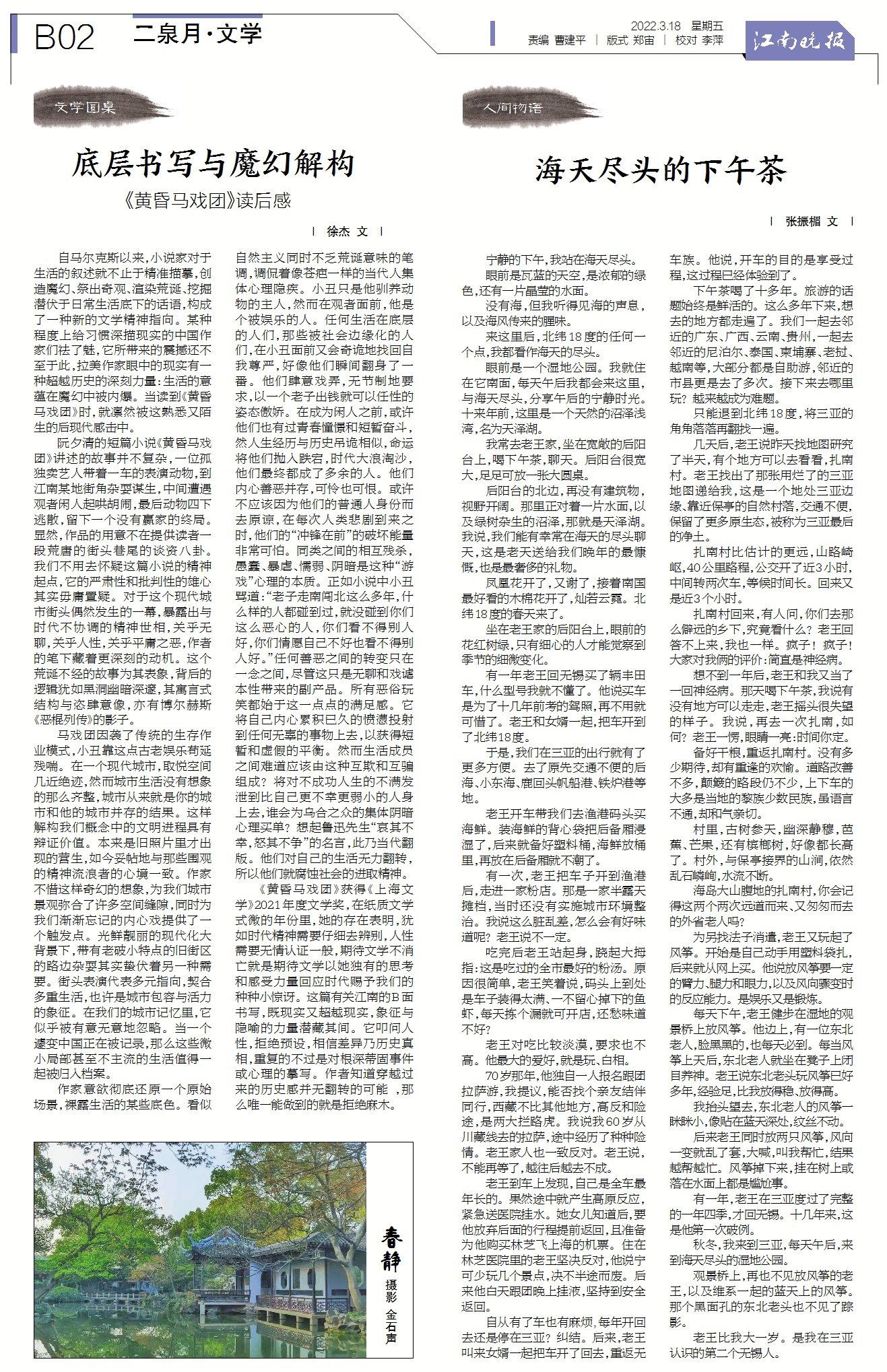| 徐杰 文 |
自马尔克斯以来,小说家对于生活的叙述就不止于精准描摹,创造魔幻、祭出奇观、渲染荒诞、挖掘潜伏于日常生活底下的话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指向。某种程度上给习惯深描现实的中国作家们祛了魅,它所带来的震撼还不至于此,拉美作家眼中的现实有一种超越历史的深刻力量:生活的意蕴在魔幻中被内爆。当读到《黄昏马戏团》时,就凛然被这熟悉又陌生的后现代感击中。
阮夕清的短篇小说《黄昏马戏团》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位孤独卖艺人带着一车的表演动物,到江南某地街角杂耍谋生,中间遭遇观者闲人起哄胡闹,最后动物四下逃散,留下一个没有赢家的终局。显然,作品的用意不在提供读者一段荒唐的街头巷尾的谈资八卦。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篇小说的精神起点,它的严肃性和批判性的雄心其实毋庸置疑。对于这个现代城市街头偶然发生的一幕,暴露出与时代不协调的精神世相,关乎无聊,关乎人性,关乎平庸之恶,作者的笔下藏着更深刻的动机。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为其表象,背后的逻辑犹如黑洞幽暗深邃,其寓言式结构与恣肆意像,亦有博尔赫斯《恶棍列传》的影子。
马戏团因袭了传统的生存作业模式,小丑靠这点古老娱乐苟延残喘。在一个现代城市,取悦空间几近绝迹,然而城市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齐整,城市从来就是你的城市和他的城市并存的结果。这样解构我们概念中的文明进程具有辩证价值。本来是旧照片里才出现的营生,如今妥帖地与那些围观的精神流浪者的心境一致。作家不惜这样奇幻的想象,为我们城市景观弥合了许多空间缝隙,同时为我们渐渐忘记的内心戏提供了一个触发点。光鲜靓丽的现代化大背景下,带有老破小特点的旧街区的路边杂耍其实蛰伏着另一种需要。街头表演代表多元指向,契合多重生活,也许是城市包容与活力的象征。在我们的城市记忆里,它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当一个遽变中国正在被记录,那么这些微小局部甚至不主流的生活值得一起被归入档案。
作家意欲彻底还原一个原始场景,裸露生活的某些底色。看似自然主义同时不乏荒诞意味的笔调,调侃着像苍疤一样的当代人集体心理隐疾。小丑只是他驯养动物的主人,然而在观者面前,他是个被娱乐的人。任何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在小丑面前又会奇诡地找回自我尊严,好像他们瞬间翻身了一番。他们肆意戏弄,无节制地要求,以一个老子出钱就可以任性的姿态傲娇。在成为闲人之前,或许他们也有过青春憧憬和短暂奋斗,然人生经历与历史吊诡相似,命运将他们抛入跌宕,时代大浪淘沙,他们最终都成了多余的人。他们内心善恶并存,可怜也可恨。或许不应该因为他们的普通人身份而去原谅,在每次人类悲剧到来之时,他们的“冲锋在前”的破坏能量非常可怕。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愚蠢、暴虐、懦弱、阴暗是这种“游戏”心理的本质。正如小说中小丑骂道:“老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都碰到过,就没碰到你们这么恶心的人,你们看不得别人好,你们情愿自己不好也看不得别人好。”任何善恶之间的转变只在一念之间,尽管这只是无聊和戏谑本性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恶俗玩笑都始于这一点点的满足感。它将自己内心累积已久的愤懑投射到任何无辜的事物上去,以获得短暂和虚假的平衡。然而生活成员之间难道应该由这种互欺和互骗组成?将对不成功人生的不满发泄到比自己更不幸更弱小的人身上去,谁会为乌合之众的集体阴暗心理买单?想起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名言,此乃当代翻版。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无力翻转,所以他们就腐蚀社会的进取精神。
《黄昏马戏团》获得《上海文学》2021年度文学奖,在纸质文学式微的年份里,她的存在表明,犹如时代精神需要仔细去辨别,人性需要无情认证一般,期待文学不消亡就是期待文学以她独有的思考和感受力量回应时代赐予我们的种种小惊讶。这篇有关江南的B面书写,既现实又超越现实,象征与隐喻的力量潜藏其间。它叩问人性,拒绝预设,相信差异乃历史真相,重复的不过是对根深蒂固事件或心理的摹写。作者知道穿越过来的历史感并无翻转的可能 ,那么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拒绝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