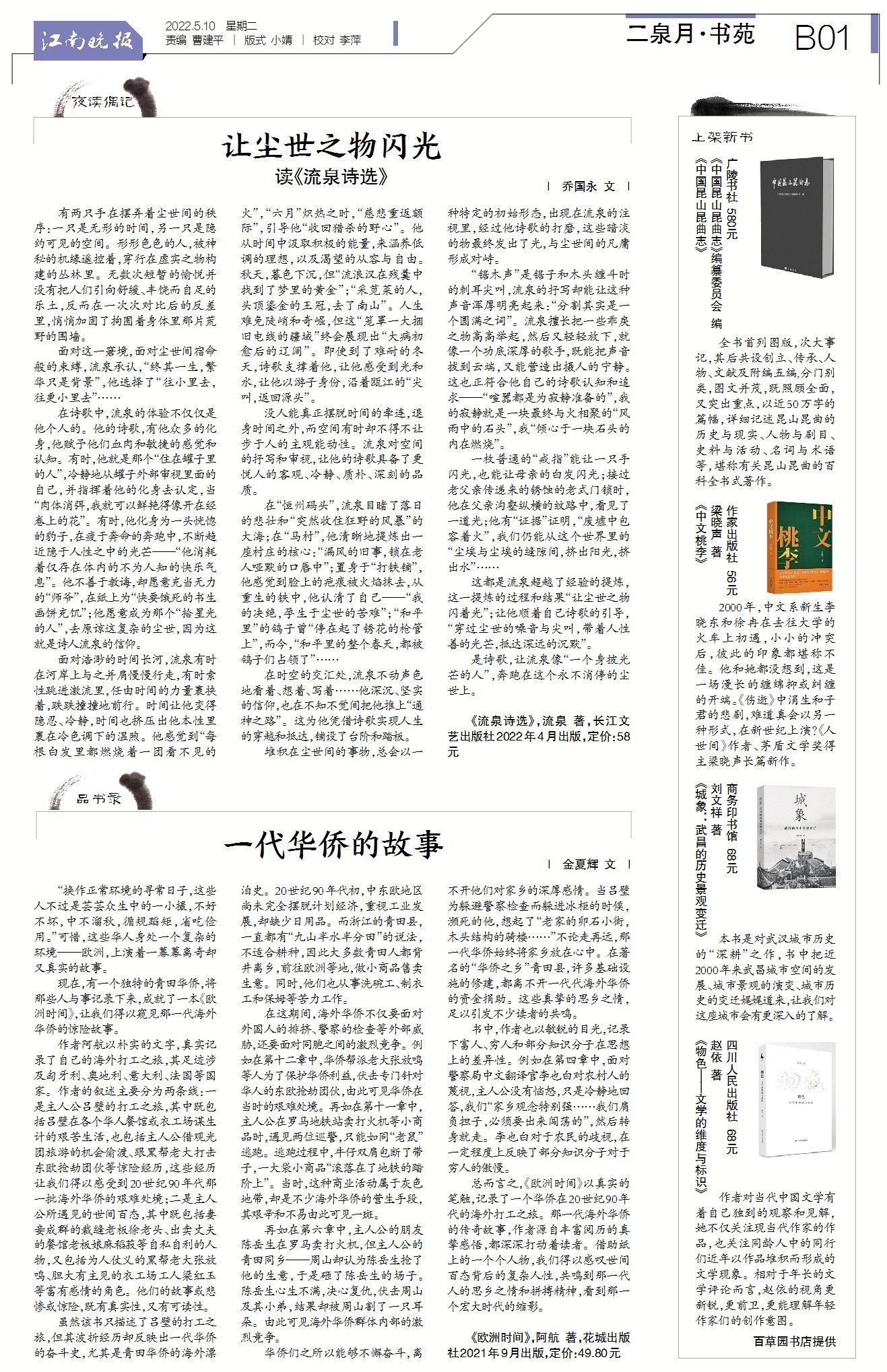| 乔国永 文 |
有两只手在摆弄着尘世间的秩序:一只是无形的时间,另一只是隐约可见的空间。形形色色的人,被神秘的机缘遥控着,穿行在虚实之物构建的丛林里。无数次短暂的愉悦并没有把人们引向舒缓、丰饶而自足的乐土,反而在一次次对比后的反差里,悄悄加固了拘囿着身体里那片荒野的围墙。
面对这一窘境,面对尘世间宿命般的束缚,流泉承认,“终其一生,繁华只是背景”,他选择了“往小里去,往更小里去”……
在诗歌中,流泉的体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他的诗歌,有他众多的化身,他赋予他们血肉和敏捷的感觉和认知。有时,他就是那个“住在罐子里的人”,冷静地从罐子外部审视里面的自己,并指挥着他的化身去认定,当“肉体消弭,我就可以鲜艳得像开在经卷上的花”。有时,他化身为一头恍惚的豹子,在疲于奔命的奔跑中,不断趋近隐于人性之中的光芒——“他消耗着仅存在体内的不为人知的快乐气息”。他不善于教诲,却愿意充当无力的“师爷”,在纸上为“快要饿死的书生画饼充饥”;他愿意成为那个“拾星光的人”,去原谅这复杂的尘世,因为这就是诗人流泉的信仰。
面对浩渺的时间长河,流泉有时在河岸上与之并肩慢慢行走,有时索性跳进激流里,任由时间的力量裹挟着,跌跌撞撞地前行。时间让他变得隐忍、冷静,时间也挤压出他本性里裹在冷色调下的温煦。他感觉到“每根白发里都燃烧着一团看不见的火”,“六月”炽热之时,“慈悲重返额际”,引导他“收回猎杀的野心”。他从时间中汲取积极的能量,来涵养低调的理想,以及渴望的从容与自由。秋天,暮色下沉,但“流浪汉在残羹中找到了梦里的黄金”;“采苋菜的人,头顶鎏金的王冠,去了南山”。人生难免陡峭和奇崛,但这“笼罩一大捆旧电线的疆域”终会展现出“大病初愈后的辽阔”。即使到了难耐的冬天,诗歌支撑着他,让他感受到光和水,让他以游子身份,沿着瓯江的“尖叫,返回源头”。
没人能真正摆脱时间的牵连,退身时间之外,而空间有时却不得不让步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流泉对空间的抒写和审视,让他的诗歌具备了更悦人的客观、冷静、质朴、深刻的品质。
在“恒州码头”,流泉目睹了落日的悲壮和“突然收住狂野的风暴”的大海;在“马村”,他清晰地提炼出一座村庄的核心:“漏风的旧事,锁在老人哑默的口唇中”;置身于“打铁铺”,他感觉到脸上的疤痕被火焰抹去,从重生的铁中,他认清了自己——“我的决绝,孕生于尘世的苦难”;“和平里”的鸽子曾“停在起了锈花的枪管上”,而今,“和平里的整个春天,都被鸽子们占领了”……
在时空的交汇处,流泉不动声色地看着、想着、写着……他深沉、坚实的信仰,也在不知不觉间把他推上“通神之路”。这为他凭借诗歌实现人生的穿越和抵达,铺设了台阶和踏板。
堆积在尘世间的事物,总会以一种特定的初始形态,出现在流泉的注视里,经过他诗歌的打磨,这些暗淡的物最终发出了光,与尘世间的凡庸形成对峙。
“锯木声”是锯子和木头缠斗时的刺耳尖叫,流泉的抒写却能让这种声音浑厚明亮起来:“分割其实是一个圆满之词”。流泉擅长把一些乖戾之物高高举起,然后又轻轻放下,就像一个功底深厚的歌手,既能把声音拔到云端,又能营造出摄人的宁静。这也正符合他自己的诗歌认知和追求——“喧嚣都是为寂静准备的”,我的寂静就是一块最终与火相聚的“风雨中的石头”,我“倾心于一块石头的内在燃烧”。
一枚普通的“戒指”能让一只手闪光,也能让母亲的白发闪光;接过老父亲传递来的锈蚀的老式门锁时,他在父亲沟壑纵横的纹路中,看见了一道光;他有“证据”证明,“废墟中包容着火”,我们仍能从这个世界里的“尘埃与尘埃的缝隙间,挤出阳光,挤出水”……
这都是流泉超越了经验的提炼,这一提炼的过程和结果“让尘世之物闪着光”;让他顺着自己诗歌的引导,“穿过尘世的噪音与尖叫,带着人性善的光芒,抵达深远的沉默”。
是诗歌,让流泉像“一个身披光芒的人”,奔跑在这个永不消停的尘世上。
《流泉诗选》,流泉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定价: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