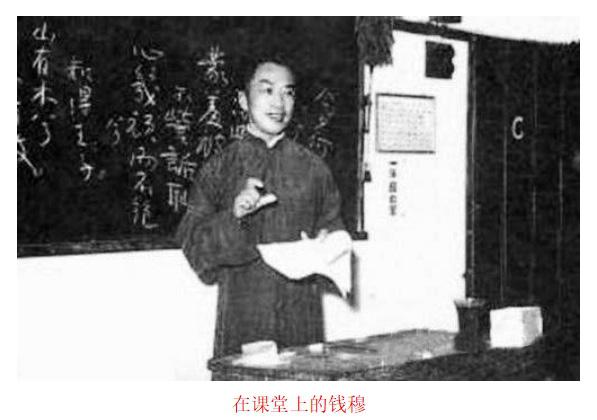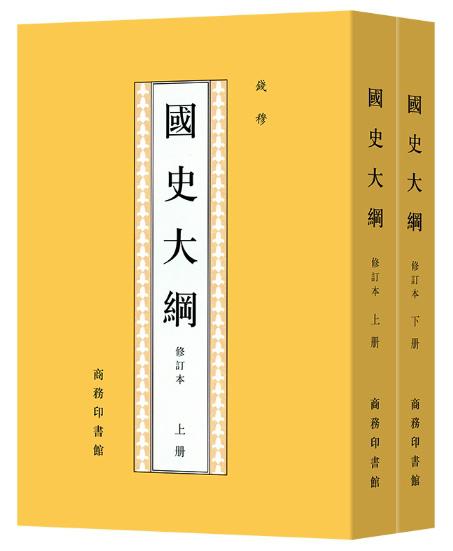| 陆阳 文|
今年7月30日,是钱穆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日。1912年,18岁的钱穆以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为起点,开启了自己在无锡乡间小学十年的教学生涯。此后,从荡口的鸿模学校,到梅村的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再至后宅的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钱穆的“乡教十年”,正值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型的关键期,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萌芽到爆发的十年。作为身处无锡的青年教师,钱穆既被时代浪潮推向思想革新的前沿,又在传统学术根系与现代思潮冲击之间艰难寻觅,成为近代中国知识青年在文化转型期的典型缩影。
迎新:
拥抱新文化的时代姿态
钱穆的故乡无锡,因沪宁铁路贯通而成为新旧文化交汇的前沿。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新青年》被摆上了书铺的柜面。钱穆回忆:“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热点,钱穆通过撰文的形式积极参与讨论,展现出鲜明的“迎新”立场。从1919年年末起,钱穆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研究白话文之两面》《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等文章,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等文章。细绎这些文章的内容,钱穆表达的意见主要集中于“国文该如何教”这一问题。
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主张推翻旧文学、建立白话文。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中国传统文风提出疑问;钱玄同更是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激进口号批判旧文学流派。1920年,钱穆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也批评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常有求“私人利禄地位之臭味”,又爱“虚张卫道之旗”,字句间皆有“富贵骄汰之气”,直指桐城派古文“空论史籍陈账”“弄巧酬俗”的流弊。钱穆的观点虽然不及“五四”健将们那般激进,但在反对将古文经典神圣化方面与他们有着相近的旨趣。
1923年,钱穆发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国文教学“绝对应该取‘迎新’的态度,而不应该‘恋旧’”。他说:“理想中的高级中学校的国文教材是一部完全新文学史中重要的史料。”“抱新文学者的态度的国文教授应该使学生有迎新的态度,而进层有创新的能力,这才是他的成功。”对于南开学校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展开的“读经”,他表达了极不赞成的态度,说:如拿着“圣”“经”两个观念来读古书,“我是绝对否认的”。这些观点,展现出他与新文化派同步的批判精神。
在教学实践中,钱穆积极尝试白话文的教育改革。他组织学生到郊外采风,命学生留意松间风声、观察梅雨,又令学生“各述故事”,用白话文写作。这种“从生活中找素材”的教学法,暗合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也体现他对“文学革命”的实质响应。这一教学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如是半年,四年级生毕业,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
就治学重点而言,青年时期的钱穆最初以古文辞为主。但是,从1920年起其治学重点逐步偏向于子学和理学。他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就是他在此后阶段研究子学的成果。那么,他何以舍古文辞而转向子学?“五四”期间,他对“古文”作如此明显的批评,正是其中最深层的原因。不过,后来,他对古文的态度又有了“反正”。1953年他在《宋明理学概述》所撰序言中,提及在乡教时期受三兼小学秦仲立鼓励而“留心于文章分类选纂之义法”,后“于是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遂看《传习录》《近思录》及黄、全两《学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经》,治先秦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订训诂”。此后,他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上溯先秦《五经》与诸子百家,下探清代学者的考订训诂之学,构建起贯通古今的学术体系。
耄耋之年钱穆曾经有过一段坦诚的“夫子自道”:“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寥寥数语,道出了他早年“迎新”取向的缘由。
守正:
对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反思
与胡适、陈独秀等激进派不同,钱穆的“迎新”始终伴随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对“全盘西化”的警惕。胡适在说到中学古文教材的选择时,提出“第一年级读近人的文章,如梁任公、康有为、章太炎、章行严、严几道的散文”。钱穆对此并不苟同,在1920年的《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中予以反驳:“严(复)译诸书故走僻涩,一不宜,章太炎文亦有之。……梁任公文多空套,太冗长,三不宜。报章杂志此病多有之。最近新文体中嘲笑谩骂,意主争论,以应教授文学之选择,四不宜。因时因人立论之文,事过境迁,以入选材,恐滋误会,五不宜。浅显平常之作可以浏览,以入教材,六不宜。”在1924年的文章《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中,钱穆的观点有了调整。他说:“各级国文,除精读选文外,每学年由校指定课外读书一种,为共同之研究。……前期第一年读《论语》,第二年《孟子》,第三年《史记》;后期第一年《左传》,第二年《诗经》,第三年诸子,规定老、墨、庄、荀、韩、吕、淮南、小戴礼、《论衡》九部,由学生选其一部或两部。”
钱穆这种对新文体流弊的清醒认知,源于他对传统文学审美特质的深刻体认——
他回忆:“又一日,余选林纾《技击余谈》中一故事,由余口述,命诸生记下。今此故事已忘,姑以意说之。有五兄弟,大哥披挂上阵,二哥又披挂上阵,三哥亦披挂上阵,四哥还披挂上阵,五弟随之仍然披挂上阵。诸生皆如所言记下。余告诸生,作文固如同说话,但有时说话可如此,作文却宜求简洁。因在黑板上写林纾原文,虽系文言,诸生一见,皆明其义。余曰:如此写,只一语可尽,你们却写了五句,便太啰嗦了。”他以林纾文言改写学生白话作文为例,指出“说话可啰嗦,作文须简洁”,揭示文言与白话在表达功能上的本质差异。
钱穆还以白话文编写历史教科书,尝试以通俗语言重构历史叙事,但仅完成五课便戛然而止。这种半途而废,既非保守,也非趋新乏力,而是出自他的自觉审慎——他意识到白话文难以完全承载传统史学的义法精神。
对“新旧之争”,年轻的钱穆就持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就在那篇表明鲜明“迎新”态度的《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一文中,他指出:“新文化不是‘发生’在最近的五六年,他有他二千年来文学史上的根据,而为一种自然的趋势。”他将白话文运动视为中国文学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与传统割裂的断裂式革命。后来,钱穆在其名著《国史大纲》中强调中国历史存在“演进”之趋向,却也存“连续”之认同。这一理念,早在他“乡教十年”阶段已埋下思想伏笔。
调适:
对学术取向的新旧融合
“乡教十年”,同样是钱穆学术的奠基起步之期。这一时期钱穆对于学术路向的探索,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新旧融合的探索。
钱穆效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早晨读经籍诸子,如《易经》《尚书》等较艰深者为精读,晚间治史籍如《汉书》《资治通鉴》等为泛览。下午课余读诗文集,如《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等为转换与发舒”。但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对《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新书杂志的涉猎,“其他不成整段之时间,乃至每日上厕苟有五分、十分之空隙,则浏览新书杂志及旧小说笔记等为博闻”。这样的阅读,暗合“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传统为学之道。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他与学生的互动:既鼓励学生用白话记录生活,又以文言名篇示范文字精练之美;既允许学生赴乡村演讲传播新思想,又在课余为他们讲解传统古籍的义理。后来,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论述中西文化的特性及对待态度之时,指出:“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的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文化。”这种“会通”思想,最初的启蒙或许就来自于当初他这种“双线并行”的教育实践。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钱穆在这一阶段也呈现出“会通新旧”的特征。1918年钱穆撰成其生平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此后又于1924年撰成《论语要略》,在这两部作品中钱穆以明确的思想史、儒学史视野解读《论语》,试图重新回归孔子之本真,体现其“兼采汉宋”的治经路径。在乡教期间,他系统研读清代孙诒让《墨子间诂》,既折服于乾嘉考据之严谨,又“逐条改写孙解之未惬意”,撰述《墨经闇解》(闇àn,晦暗的意思),初显“考据与义理兼重”的学术风格。他说:“余之游情于清代乾嘉以来校勘考据训诂学之藩篱,盖自孙氏此书始。”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其中年以后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守护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无论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学“内在理路”的发掘,还是《文化与教育》对“全盘西化”的批评,皆可视为乡教时期对新文化运动的“迎新”与“守正”的延续。回忆起当年,他不由感慨:“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钱穆的乡教岁月,是一代知识青年在“古今中西”困境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缩影。他既非固守旧垒的遗老,也非决裂传统的狂飙派,而是以“日知其所无”的开放心态吸纳新思想,同时以“温故而知新”的定力守护文化根脉。从无锡乡间的小学讲台到北大的学术殿堂,钱穆始终在做一位文化转型的“摆渡人”——他的价值,或许在于证明传统与现代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在创造性转化中实现“旧邦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