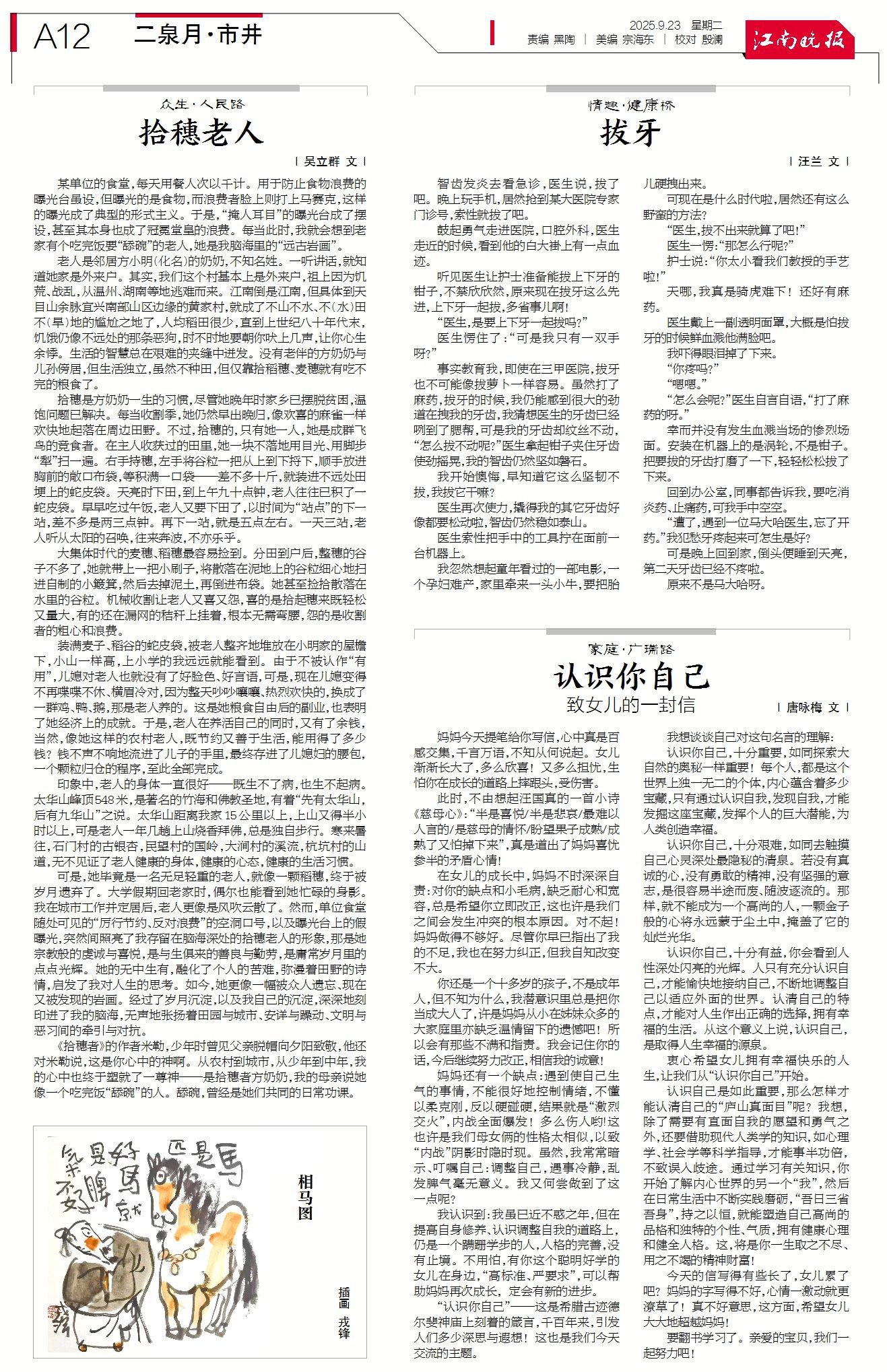| 吴立群 文 |
某单位的食堂,每天用餐人次以千计。用于防止食物浪费的曝光台虽设,但曝光的是食物,而浪费者脸上则打上马赛克,这样的曝光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于是,“掩人耳目”的曝光台成了摆设,甚至其本身也成了冠冕堂皇的浪费。每当此时,我就会想到老家有个吃完饭要“舔碗”的老人,她是我脑海里的“远古岩画”。
老人是邻居方小明(化名)的奶奶,不知名姓。一听讲话,就知道她家是外来户。其实,我们这个村基本上是外来户,祖上因为饥荒、战乱,从温州、湖南等地逃难而来。江南倒是江南,但具体到天目山余脉宜兴南部山区边缘的黄家村,就成了不山不水、不(水)田不(旱)地的尴尬之地了,人均稻田很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饥饿仍像不远处的那条恶狗,时不时地要朝你吠上几声,让你心生余悸。生活的智慧总在艰难的夹缝中迸发。没有老伴的方奶奶与儿孙傍居,但生活独立,虽然不种田,但仅靠拾稻穗、麦穗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了。
拾穗是方奶奶一生的习惯,尽管她晚年时家乡已摆脱贫困,温饱问题已解决。每当收割季,她仍然早出晚归,像欢喜的麻雀一样欢快地起落在周边田野。不过,拾穗的,只有她一人,她是成群飞鸟的竞食者。在主人收获过的田里,她一块不落地用目光、用脚步“犁”扫一遍。右手持穗,左手将谷粒一把从上到下捋下,顺手放进胸前的敞口布袋,等积满一口袋——差不多十斤,就装进不远处田埂上的蛇皮袋。天亮时下田,到上午九十点钟,老人往往已积了一蛇皮袋。早早吃过午饭,老人又要下田了,以时间为“站点”的下一站,差不多是两三点钟。再下一站,就是五点左右。一天三站,老人听从太阳的召唤,往来奔波,不亦乐乎。
大集体时代的麦穗、稻穗最容易捡到。分田到户后,整穗的谷子不多了,她就带上一把小刷子,将散落在泥地上的谷粒细心地扫进自制的小簸箕,然后去掉泥土,再倒进布袋。她甚至捡拾散落在水里的谷粒。机械收割让老人又喜又怨,喜的是拾起穗来既轻松又量大,有的还在漏网的秸秆上挂着,根本无需弯腰,怨的是收割者的粗心和浪费。
装满麦子、稻谷的蛇皮袋,被老人整齐地堆放在小明家的屋檐下,小山一样高,上小学的我远远就能看到。由于不被认作“有用”,儿媳对老人也就没有了好脸色、好言语,可是,现在儿媳变得不再喋喋不休、横眉冷对,因为整天吵吵嚷嚷、热烈欢快的,换成了一群鸡、鸭、鹅,那是老人养的。这是她粮食自由后的副业,也表明了她经济上的成就。于是,老人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又有了余钱,当然,像她这样的农村老人,既节约又善于生活,能用得了多少钱?钱不声不响地流进了儿子的手里,最终存进了儿媳妇的腰包,一个颗粒归仓的程序,至此全部完成。
印象中,老人的身体一直很好——既生不了病,也生不起病。太华山峰顶548米,是著名的竹海和佛教圣地,有着“先有太华山,后有九华山”之说。太华山距离我家15公里以上,上山又得半小时以上,可是老人一年几趟上山烧香拜佛,总是独自步行。寒来暑往,石门村的古银杏,民望村的国岭,大涧村的溪流,杭坑村的山道,无不见证了老人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态,健康的生活习惯。
可是,她毕竟是一名无足轻重的老人,就像一颗稻穗,终于被岁月遗弃了。大学假期回老家时,偶尔也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我在城市工作并定居后,老人更像是风吹云散了。然而,单位食堂随处可见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空洞口号,以及曝光台上的假曝光,突然间照亮了我存留在脑海深处的拾穗老人的形象,那是她宗教般的虔诚与喜悦,是与生俱来的善良与勤劳,是庸常岁月里的点点光辉。她的无中生有,融化了个人的苦难,弥漫着田野的诗情,启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如今,她更像一幅被众人遗忘、现在又被发现的岩画。经过了岁月沉淀,以及我自己的沉淀,深深地刻印进了我的脑海,无声地张扬着田园与城市、安详与躁动、文明与恶习间的牵引与对抗。
《拾穗者》的作者米勒,少年时曾见父亲脱帽向夕阳致敬,他还对米勒说,这是你心中的神啊。从农村到城市,从少年到中年,我的心中也终于塑就了一尊神——是拾穗者方奶奶,我的母亲说她像一个吃完饭“舔碗”的人。舔碗,曾经是她们共同的日常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