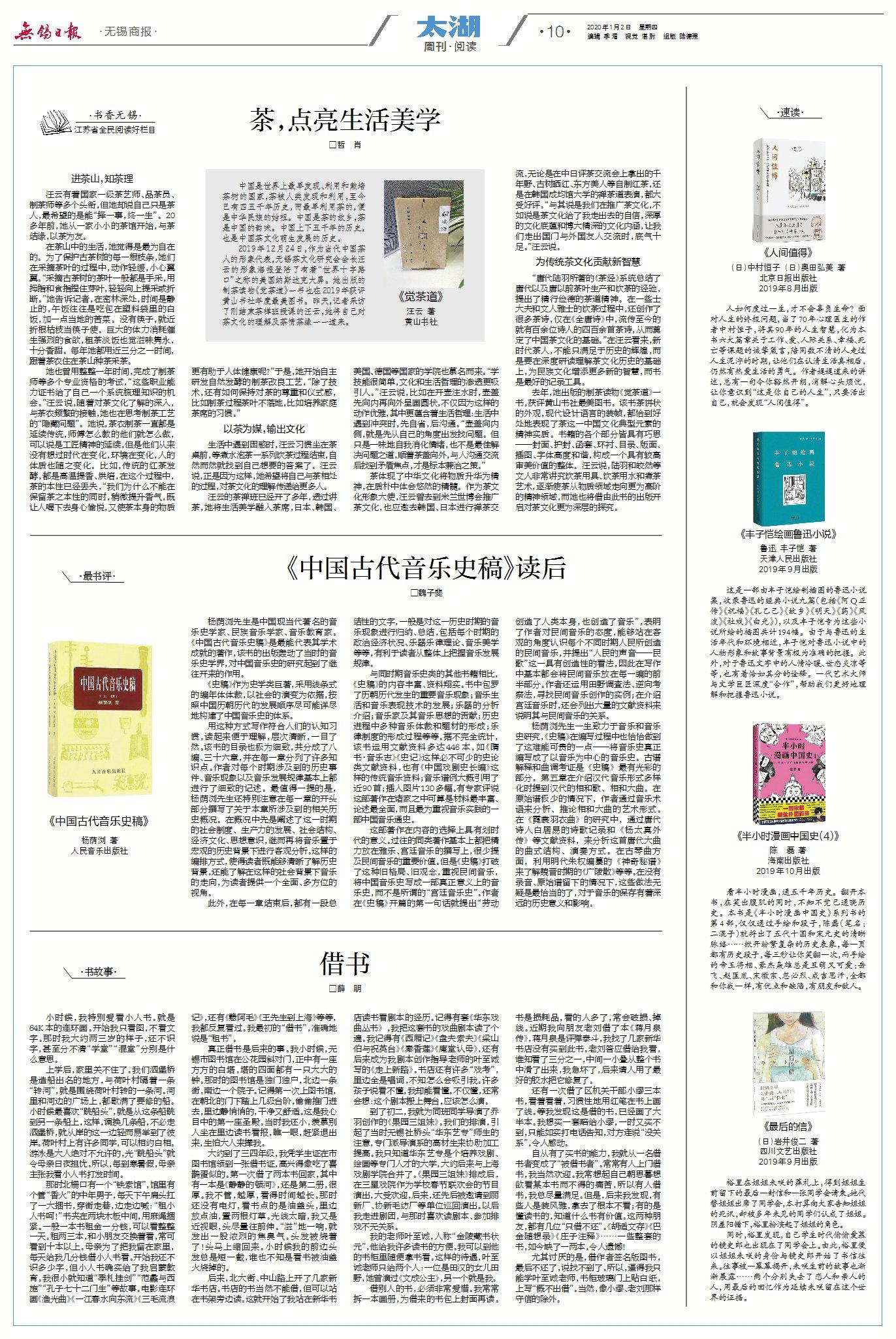□薛 明
小时候,我特別爱看小人书。就是64K本的连环画。开始我只看图,不看文字。那时我大约两三岁的样子,还不识字,甚至分不清“学堂”“混堂”分别是什么意思。
上学后,家里关不住了。我们泗堡桥是造船出名的地方,与荷叶村隔着一条“转河”,就是围绕荷叶村转的一条河。河里和河边的广场上,都歇满了要修的船。小时候最喜欢“跳船头”,就是从这条船跳到另一条船上,这样,调换几条船,不必走泗堡桥,就从岸的这一边轻而易举到了彼岸。荷叶村上有许多同学,可以相约白相。游泳是大人绝对不允许的,光“跳船头”就令母亲日夜担忧。所以,每到寒暑假,母亲主张我看小人书打发时间。
那时北柵口有一个“铁索馆”,馆里有个管“香火”的中年男子,每天下午肩头扛了一大捆书,穿街走巷,边走边喊:“租小人书呵!”书夹在两块木板中间,用麻绳捆紧。一般一本书租金一分钱,可以看整整一天。租两三本,和小朋友交换着看,常可看到十本以上。母亲为了把我留在家里,每天给我几分钱借小人书看。开始我还不识多少字,但小人书确实给了我启蒙教育。我很小就知道“季札挂剑”“范蠡与西施”“孔子七十二门生”等故事。电影连环画《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还有《戆阿毛》《王先生到上海》等等,我都反复看过。我最初的“借书”,准确地说是“租书”。
真正借书是后来的事。我小时候,无锡市图书馆在公花园斜对门,正中有一座方方的白塔,塔的四面都有一只大大的钟。那时的图书馆是独门独户,北边一条街,南边一个院子。记得第一次上图书馆,在朝北的门下踏上几级台阶,偷偷推门进去,里边静悄悄的,干净又舒适。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座圣殿。当时我还小,羡慕别人坐在里边读书看报,瞧一眼,赶紧退出来,生怕大人来撵我。
大约到了三四年级,我凭学生证在市图书馆领到一张借书证,高兴得像吃了喜鹊蛋似的。第一次借了两本书回家,其中有一本是《静静的顿河》,还是第二册,很厚。我不管,越厚,看得时间越长。那时还没有电灯,看书点的是油盏头,里边放点油,置两根灯草。光线太暗,我又是近视眼,头尽量往前伸。“滋”地一响,就发出一股浓烈的焦臭气。头发被烧着了!头马上缩回来。小时候我的前边头发总是短一截,谁也不知是看书被油盏火烧掉的。
后来,北大街、中山路上开了几家新华书店。书店的书当然不能借,但可以站在书架旁边读。这就开始了我站在新华书店读书看剧本的经历。记得有套《华东戏曲丛书》 ,我把这套书的戏曲剧本读了个遍。我记得有《西厢记》《盘夫索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庵堂认母》,还有后来成为我剧本创作指导老师的叶至诚写的《走上新路》。书店还有许多“戏考”,里边全是唱词,不知怎么会吸引我。许多孩子说看不懂,我却能看懂。不仅懂,还常会想:这个剧本搬上舞台,应该怎么演。
到了初二,我就为同班同学导演了乔羽创作的《果园三姐妹》。我们的排演,引起了当时无锡社桥头“华东艺专”师生的注意,专门派导演系的高材生来协助加工提高。我只知道华东艺专是个培养戏剧、绘画等专门人才的大学,大约后来与上海戏剧学院合并了。《果园三姐妹》排成后,在三星戏院作为学校春节联欢会的节目演出,大受欢迎,后来,还先后被邀请到丽新厂、协新毛纺厂等单位巡回演出。以后我走进剧团,与那时喜欢读剧本、参加排戏不无关系。
我的老师叶至诚,人称“金陵藏书状元”,他给我许多读书的方便。我可以到他的书柜里随便拿书看。这样的待遇,叶至诚老师只给两个人:一位是田汉的女儿田野,她曾演过《文成公主》,另一个就是我。
借别人的书,必须非常爱惜。我常常拆一本画册,为借来的书包上封面再读。书是损耗品,看的人多了,常会破损、掉线。近期我向朋友老刘借了本《蒋月泉传》,蒋月泉是评弹泰斗,我找了几家新华书店没有买到此书。老刘答应借给我看,谁知看了三分之一,中间一小叠从整个书中滑了出来,我急坏了,后来请人用了最好的胶水把它修复了。
还有一次借了区机关干部小缪三本书,看着看着,习惯性地用红笔在书上画了线。等我发现这是借的书,已经画了大半本。我想买一套赔给小缪,一时又买不到,只能如实打电话告知,对方连说“没关系”,令人感动。
自从有了买书的能力,我就从一名借书者变成了“被借书者”。常常有人上门借书,我当然欢迎。我常想起自己朝思暮想欲看某本书而不得的痛苦,所以有人借书,我总尽量满足。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是装风雅,拿去了根本不看;有的是懂读书的,知道什么书有价值。这两种朋友,都有几位“只借不还”。《胡适文存》《巴金随想录》《庄子注释》……一些整套的书,如今缺了一两本,令人遗憾!
尤其讨厌的是,借作者签名版图书,最后不还了,说找不到了。所以,逼得我只能学叶至诚老师,书柜玻璃门上贴白纸,上写“概不出借”。当然,像小缪、老刘那样守信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