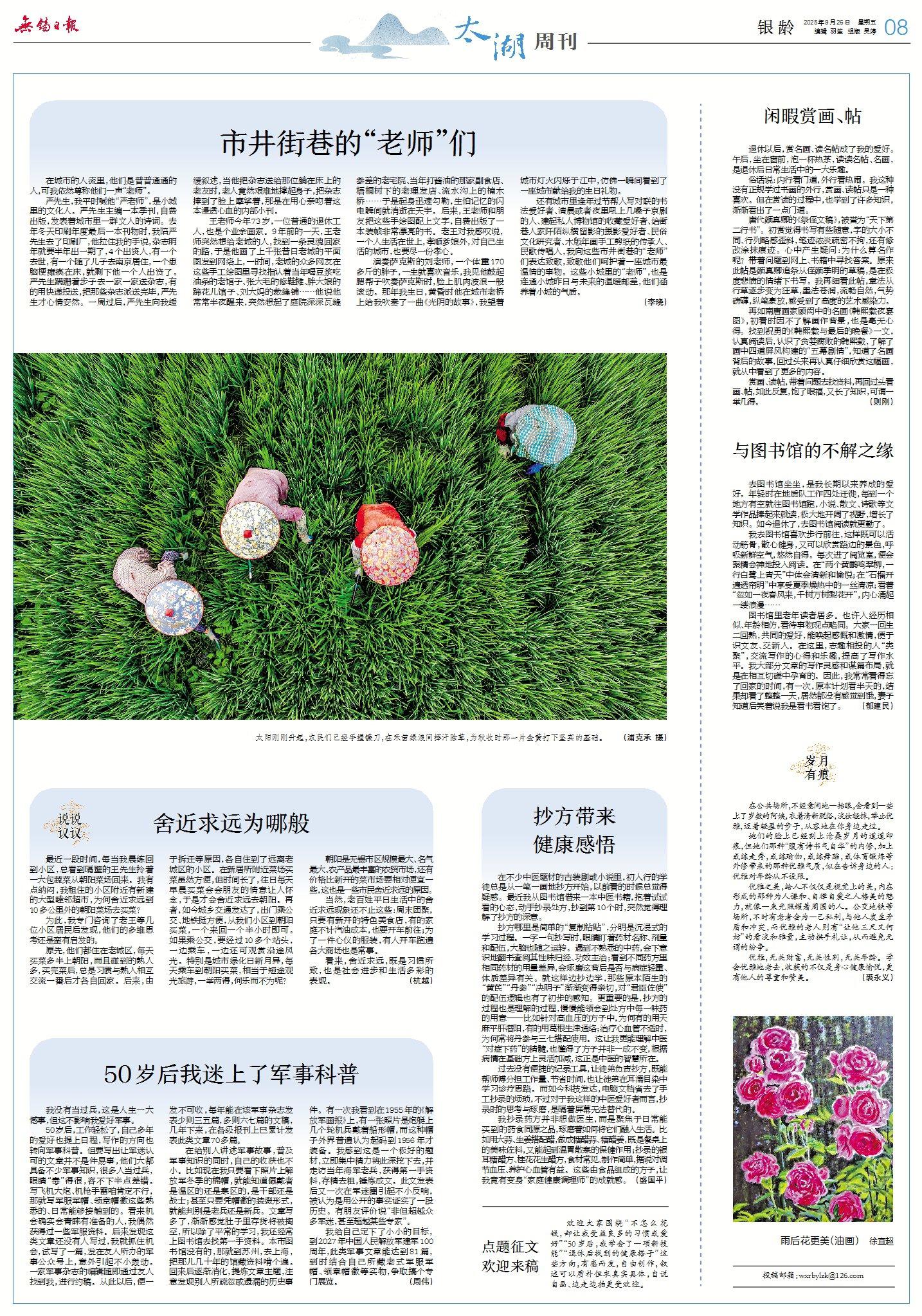在城市的人流里,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可我依然尊称他们一声“老师”。
严先生,我平时喊他“严老师”,是小城里的文化人。严先生主编一本季刊,自费出版,发表着城市里一群文人的诗词。去年冬天印刷年度最后一本刊物时,我陪严先生去了印刷厂,他拉住我的手说,杂志明年就要半年出一期了,4个出资人,有一个去世,有一个随了儿子去南京居住,一个患脑梗瘫痪在床,就剩下他一个人出资了。严先生蹒跚着步子去一家一家送杂志,有的用快递投送,把那些杂志派送完毕,严先生才心情安然。一周过后,严先生向我缓缓叙述,当他把杂志送给那位躺在床上的老友时,老人竟然艰难地撑起身子,把杂志捧到了脸上摩挲着,那是在用心亲吻着这本浸透心血的内部小刊。
王老师今年73岁,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也是个业余画家。9年前的一天,王老师突然想给老城的人,找到一条灵魂回家的路,于是他画了上千张昔日老城的平面图发到网络上,一时间,老城的众多网友在这些手工绘图里寻找指认着当年喝豆浆吃油条的老馆子、张大毛的修鞋摊、胖大娘的蹄花儿馆子、刘大妈的裁缝铺……他说他常常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了庭院深深瓦缝参差的老宅院、当年打酱油的那家副食店、梧桐树下的老理发店、流水沟上的楠木桥……于是起身迅速勾勒,生怕记忆的闪电瞬间就消逝在天宇。后来,王老师和朋友把这些手绘图配上文字,自费出版了一本装帧非常漂亮的书。老王对我感叹说,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孝顺爹娘外,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也要尽一份孝心。
演奏萨克斯的刘老师,一个体重170多斤的胖子,一生就喜欢音乐,我见他鼓起腮帮子吹奏萨克斯时,脸上肌肉波浪一般滚动。那年我生日,黄昏时他在城市老桥上给我吹奏了一曲《光阴的故事》,我望着城市灯火闪烁于江中,仿佛一瞬间看到了一座城市献给我的生日礼物。
还有城市里逢年过节帮人写对联的书法爱好者、清晨或者夜里吼上几嗓子京剧的人、建起私人博物馆的收藏爱好者、给街巷人家阡陌纵横留影的摄影爱好者、民俗文化研究者、木版年画手工剪纸的传承人、民歌传唱人,我向这些市井街巷的“老师”们表达致敬,致敬他们呵护着一座城市最温情的事物。这些小城里的“老师”,也是连通小城昨日与未来的温暖邮差,他们涵养着小城的气质。
(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