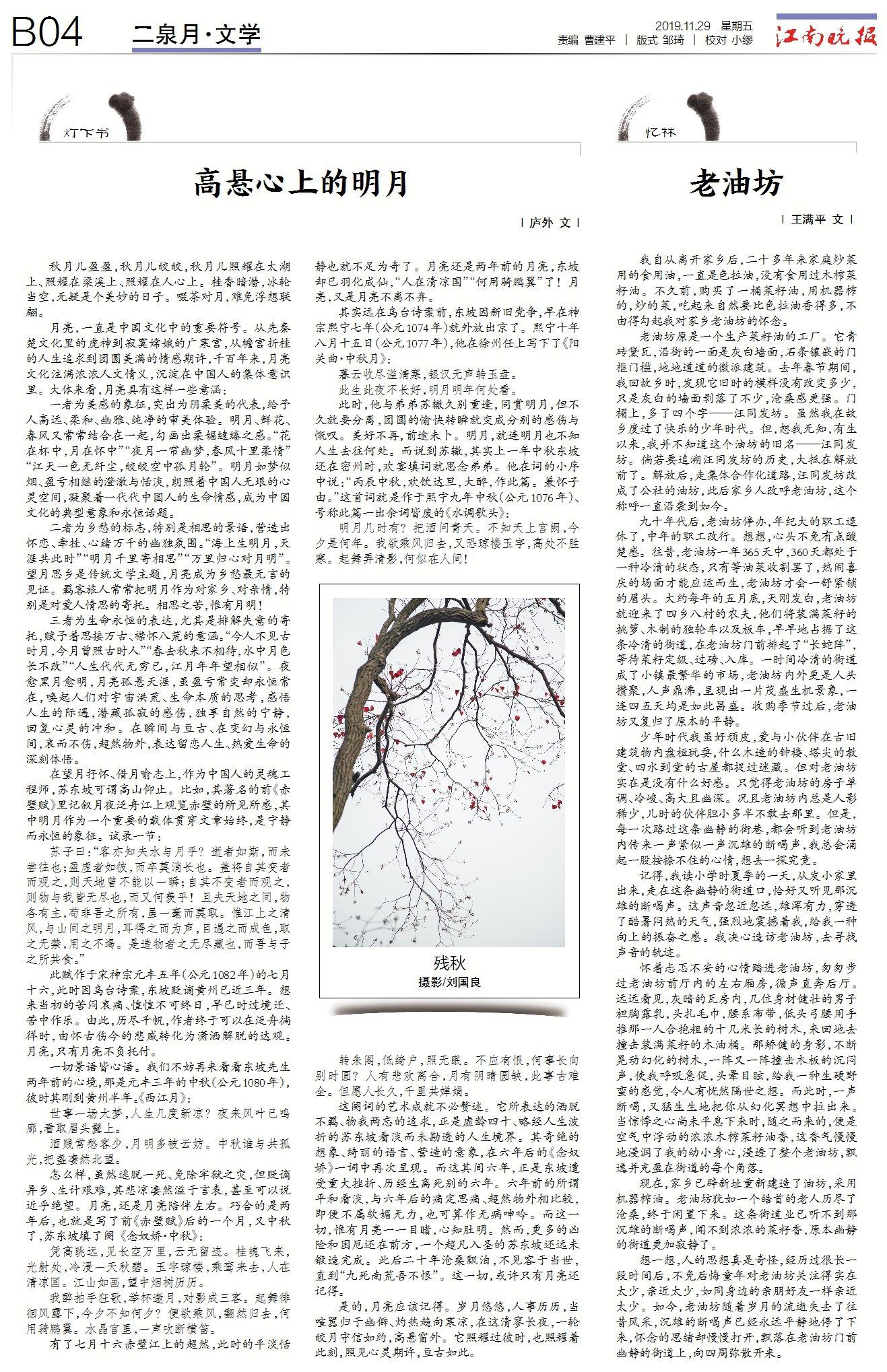| 庐外 文 |
秋月儿盈盈,秋月儿皎皎,秋月儿照耀在太湖上、照耀在梁溪上、照耀在人心上。桂香暗潜,冰轮当空,无疑是个美妙的日子。啜茶对月,难免浮想联翩。
月亮,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符号。从先秦楚文化里的虎神到寂寞嫦娥的广寒宫,从蟾宫折桂的人生追求到团圆美满的情感期许,千百年来,月亮文化注满浓浓人文情义,沉淀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里。大体来看,月亮具有这样一些意涵:
一者为美感的象征,突出为阴柔美的代表,给予人高远、柔和、幽雅、纯净的审美体验。明月、鲜花、春风又常常结合在一起,勾画出柔媚缱绻之感。“花在杯中,月在怀中”“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明月如梦似烟、盈亏相继的澄澈与恬淡,朗照着中国人无垠的心灵空间,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命情感,成为中国文化的典型意象和永恒话题。
二者为乡愁的标志,特别是相思的景语,营造出怀恋、牵挂、心绪万千的幽独氛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千里寄相思”“万里归心对月明”。望月思乡是传统文学主题,月亮成为乡愁最无言的见证。羁客旅人常常把明月作为对家乡、对亲情,特别是对爱人情思的寄托。相思之苦,惟有月明!
三者为生命永恒的表达,尤其是排解失意的寄托,赋予着思接万古、襟怀八荒的意涵。“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春去秋来不相待,水中月色长不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夜愈黑月愈明,月亮孤悬天涯,虽盈亏常变却永恒常在,唤起人们对宇宙洪荒、生命本质的思考,感悟人生的际遇,潜藏孤寂的感伤,独享自然的宁静,回复心灵的冲和。在瞬间与亘古、在变幻与永恒间,哀而不伤,超然物外,表达留恋人生、热爱生命的深刻体悟。
在望月抒怀、借月喻志上,作为中国人的灵魂工程师,苏东坡可谓高山仰止。比如,其著名的前《赤壁赋》里记叙月夜泛舟江上观览赤壁的所见所感,其中明月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贯穿文章始终,是宁静而永恒的象征。试录一节: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此赋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的七月十六,此时因乌台诗案,东坡贬谪黄州已近三年。想来当初的苦闷哀痛、惶惶不可终日,早已时过境迁、苦中作乐。由此,历尽千帆,作者终于可以在泛舟徜徉时,由怀古伤今的悲戚转化为潇洒解脱的达观。月亮,只有月亮不负托付。
一切景语皆心语。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东坡先生两年前的心境,那是元丰三年的中秋(公元1080年),彼时其刚到黄州半年。《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怎么样,虽然逃脱一死、免除牢狱之灾,但贬谪异乡、生计艰难,其悲凉凄然溢于言表,甚至可以说近乎绝望。月亮,还是月亮陪伴左右。巧合的是两年后,也就是写了前《赤壁赋》后的一个月,又中秋了,苏东坡填了阕 《念奴娇·中秋》: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有了七月十六赤壁江上的超然,此时的平淡恬静也就不足为奇了。月亮还是两年前的月亮,东坡却已羽化成仙,“人在清凉国”“何用骑鹏翼”了!月亮,又是月亮不离不弃。
其实远在乌台诗案前,东坡因新旧党争,早在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就外放出京了。熙宁十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077年),他在徐州任上写下了《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此时,他与弟弟苏辙久别重逢,同赏明月,但不久就要分离,团圆的愉快转瞬就变成分别的感伤与慨叹。美好不再,前途未卜。明月,就连明月也不知人生去往何处。而说到苏辙,其实上一年中秋东坡还在密州时,欢宴填词就思念弟弟。他在词的小序中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首词就是作于熙宁九年中秋(公元1076年)、号称此篇一出余词皆废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阕词的艺术成就不必赘述。它所表达的洒脱不羁、物我两忘的追求,正是虚龄四十、略经人生波折的苏东坡看淡而未勘透的人生境界。其奇绝的想象、绮丽的语言、营造的意象,在六年后的《念奴娇》一词中再次呈现。而这其间六年,正是东坡遭受重大挫折、历经生离死别的六年。六年前的所谓平和看淡,与六年后的痛定思痛、超然物外相比较,即便不属软媚无力,也可算作无病呻吟。而这一切,惟有月亮一一目睹,心知肚明。然而,更多的凶险和困厄还在前方,一个超凡入圣的苏东坡还远未锻造完成。此后二十年沧桑飘泊,不见容于当世,直到“九死南荒吾不恨”。这一切,或许只有月亮还记得。
是的,月亮应该记得。岁月悠悠,人事历历,当喧嚣归于幽僻、灼热趋向寒凉,在这清寥长夜,一轮皎月守信如约,高悬窗外。它照耀过彼时,也照耀着此刻,照见心灵期许,亘古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