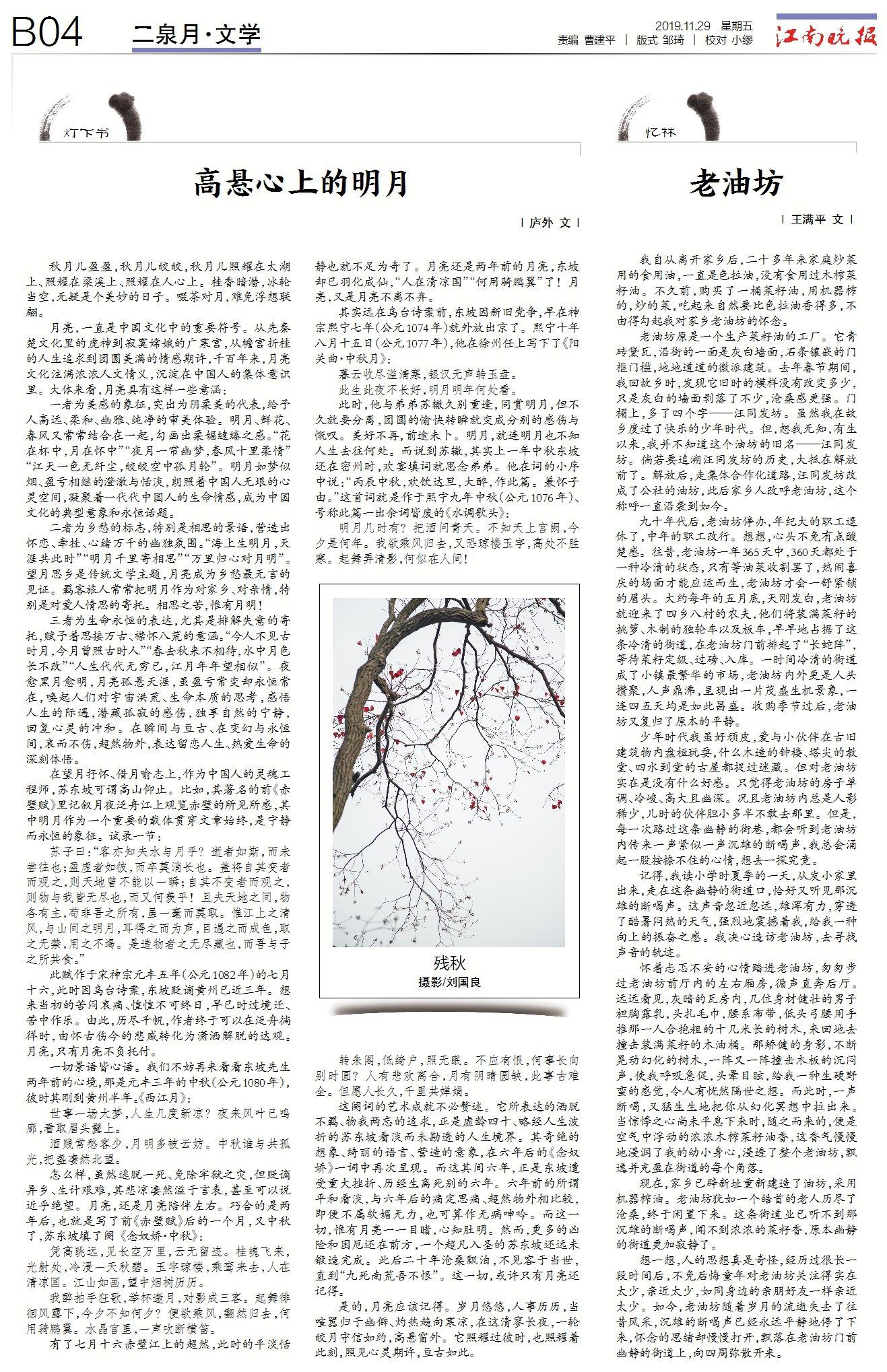| 王满平 文 |
我自从离开家乡后,二十多年来家庭炒菜用的食用油,一直是色拉油,没有食用过木榨菜籽油。不久前,购买了一桶菜籽油,用机器榨的,炒的菜,吃起来自然要比色拉油香得多,不由得勾起我对家乡老油坊的怀念。
老油坊原是一个生产菜籽油的工厂。它青砖黛瓦,沿街的一面是灰白墙面,石条镶嵌的门框门槛,地地道道的徽派建筑。去年春节期间,我回故乡时,发现它旧时的模样没有改变多少,只是灰白的墙面剥落了不少,沧桑感更强。门楣上,多了四个字——汪同发坊。虽然我在故乡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代。但,恕我无知,有生以来,我并不知道这个油坊的旧名——汪同发坊。倘若要追溯汪同发坊的历史,大抵在解放前了。解放后,走集体合作化道路,汪同发坊改成了公社的油坊,此后家乡人改呼老油坊,这个称呼一直沿袭到如今。
九十年代后,老油坊停办,年纪大的职工退休了,中年的职工改行。想想,心头不免有点酸楚感。往昔,老油坊一年365天中,360天都处于一种冷清的状态,只有等油菜收割罢了,热闹喜庆的场面才能应运而生,老油坊才会一舒紧锁的眉头。大约每年的五月底,天刚发白,老油坊就迎来了四乡八村的农夫,他们将装满菜籽的挑箩、木制的独轮车以及板车,早早地占据了这条冷清的街道,在老油坊门前排起了“长蛇阵”,等待菜籽定级、过磅、入库。一时间冷清的街道成了小镇最繁华的市场,老油坊内外更是人头攒聚,人声鼎沸,呈现出一片茂盛生机景象,一连四五天均是如此昌盛。收购季节过后,老油坊又复归了原本的平静。
少年时代我虽好顽皮,爱与小伙伴在古旧建筑物内盘桓玩耍,什么木造的钟楼、塔尖的教堂、四水到堂的古屋都捉过迷藏。但对老油坊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只觉得老油坊的房子单调、冷峻、高大且幽深。况且老油坊内总是人影稀少,儿时的伙伴胆小多半不敢去那里。但是,每一次路过这条幽静的街巷,都会听到老油坊内传来一声紧似一声沉雄的断喝声,我总会涌起一股按捺不住的心情,想去一探究竟。
记得,我读小学时夏季的一天,从发小家里出来,走在这条幽静的街道口,恰好又听见那沉雄的断喝声。这声音忽近忽远,雄浑有力,穿透了酷暑闷热的天气,强烈地震撼着我,给我一种向上的振奋之感。我决心造访老油坊,去寻找声音的轨迹。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老油坊,匆匆步过老油坊前厅内的左右厢房,循声直奔后厅。远远看见,灰暗的瓦房内,几位身材健壮的男子袒胸露乳,头扎毛巾,腰系布带,低头弓腰用手推那一人合抱粗的十几米长的树木,来回地去撞击装满菜籽的木油桶。那矫健的身影,不断晃动幻化的树木,一阵又一阵撞击木板的沉闷声,使我呼吸急促,头晕目眩,给我一种生硬野蛮的感觉,令人有恍然隔世之想。而此时,一声断喝,又猛生生地把你从幻化冥想中拉出来。当惊悸之心尚未平息下来时,随之而来的,便是空气中浮动的浓浓木榨菜籽油香,这香气慢慢地浸润了我的幼小身心,浸透了整个老油坊,飘逸并充盈在街道的每个角落。
现在,家乡已辟新址重新建造了油坊,采用机器榨油。老油坊犹如一个皓首的老人历尽了沧桑,终于闲置下来。这条街道业已听不到那沉雄的断喝声,闻不到浓浓的菜籽香,原本幽静的街道更加寂静了。
想一想,人的思想真是奇怪,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不免后悔童年对老油坊关注得实在太少,亲近太少,如同身边的亲朋好友一样亲近太少。如今,老油坊随着岁月的流逝失去了往昔风采,沉雄的断喝声已经永远平静地停了下来,怀念的思绪却慢慢打开,飘落在老油坊门前幽静的街道上,向四周弥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