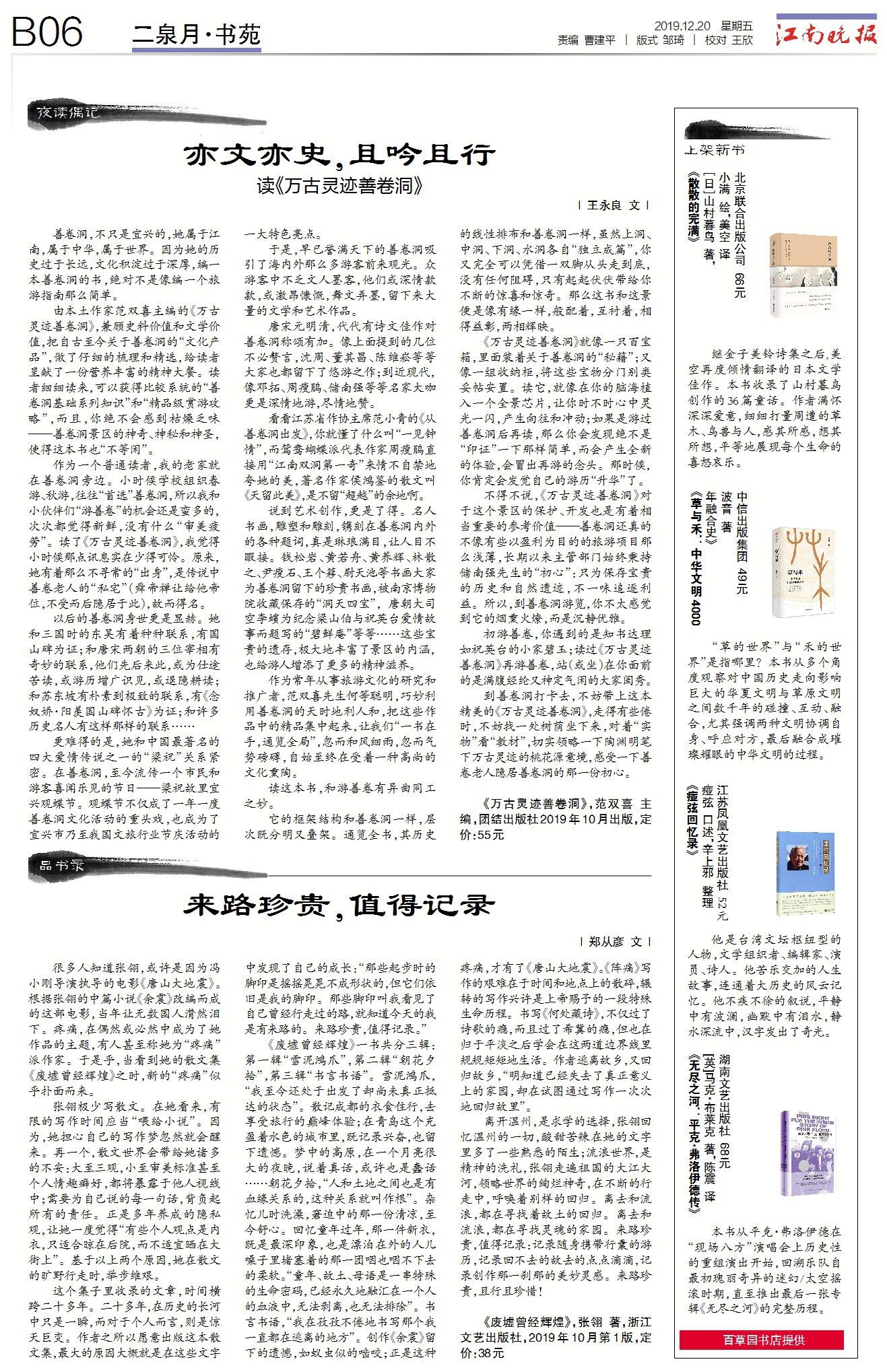| 郑从彦 文 |
很多人知道张翎,或许是因为冯小刚导演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根据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改编而成的这部电影,当年让无数国人潸然泪下。疼痛,在偶然或必然中成为了她作品的主题,有人甚至称她为“疼痛”派作家。于是乎,当看到她的散文集《废墟曾经辉煌》之时,新的“疼痛”似乎扑面而来。
张翎极少写散文。在她看来,有限的写作时间应当“喂给小说”。因为,她担心自己的写作梦忽然就会醒来。再一个,散文世界会带给她诸多的不安:大至三观,小至审美标准甚至个人情趣癖好,都将暴露于他人视线中;需要为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背负起所有的责任。正是多年养成的隐私观,让她一度觉得“有些个人观点是内衣,只适合晾在后院,而不适宜晒在大街上”。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她在散文的旷野行走时,举步维艰。
这个集子里收录的文章,时间横跨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而对于个人而言,则是惊天巨变。作者之所以愿意出版这本散文集,最大的原因大概就是在这些文字中发现了自己的成长:“那些起步时的脚印是摇摇晃晃不成形状的,但它们依旧是我的脚印。那些脚印叫我看见了自己曾经行走过的路,就知道今天的我是有来路的。来路珍贵,值得记录。”
《废墟曾经辉煌》一书共分三辑:第一辑“雪泥鸿爪”,第二辑“朝花夕拾”,第三辑“书言书语”。雪泥鸿爪,“我至今还处于出发了却尚未真正抵达的状态”。散记成都的衣食住行,去享受旅行的巅峰体验;在青岛这个充盈着水色的城市里,既记录兴奋,也留下遗憾。梦中的高原,在一个月亮很大的夜晚,说着真话,或许也是蠢话……朝花夕拾,“人和土地之间也是有血缘关系的,这种关系就叫作根”。杂忆儿时洗澡,窘迫中的那一份清凉,至今舒心。回忆童年过年,那一件新衣,既是最深印象,也是漂泊在外的人儿嗓子里堵塞着的那一团咽也咽不下去的柔软。“童年、故土、母语是一串特殊的生命密码,已经永久地融汇在一个人的血液中,无法剥离,也无法排除”。书言书语,“我在孜孜不倦地书写那个我一直都在逃离的地方”。创作《余震》留下的遗憾,如蚁虫似的啮咬;正是这种疼痛,才有了《唐山大地震》。《阵痛》写作的艰难在于时间和地点上的散碎,辗转的写作兴许是上帝赐予的一段特殊生命历程。书写《何处藏诗》,不仅过了诗歌的瘾,而且过了希冀的瘾,但也在归于平淡之后学会在这两道边界线里规规矩矩地生活。作者逃离故乡,又回归故乡,“明知道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却在试图通过写作一次次地回归故里”。
离开温州,是求学的选择,张翎回忆温州的一切,酸甜苦辣在她的文字里多了一些熟悉的陌生;流浪世界,是精神的洗礼,张翎走遍祖国的大江大河,领略世界的绚烂神奇,在不断的行走中,呼唤着别样的回归。离去和流浪,都在寻找着故土的回归。离去和流浪,都在寻找灵魂的家园。来路珍贵,值得记录:记录随身携带行囊的游历,记录回不去的故去的点点滴滴,记录创作那一刹那的美妙灵感。来路珍贵,且行且珍惜!
《废墟曾经辉煌》,张翎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定价: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