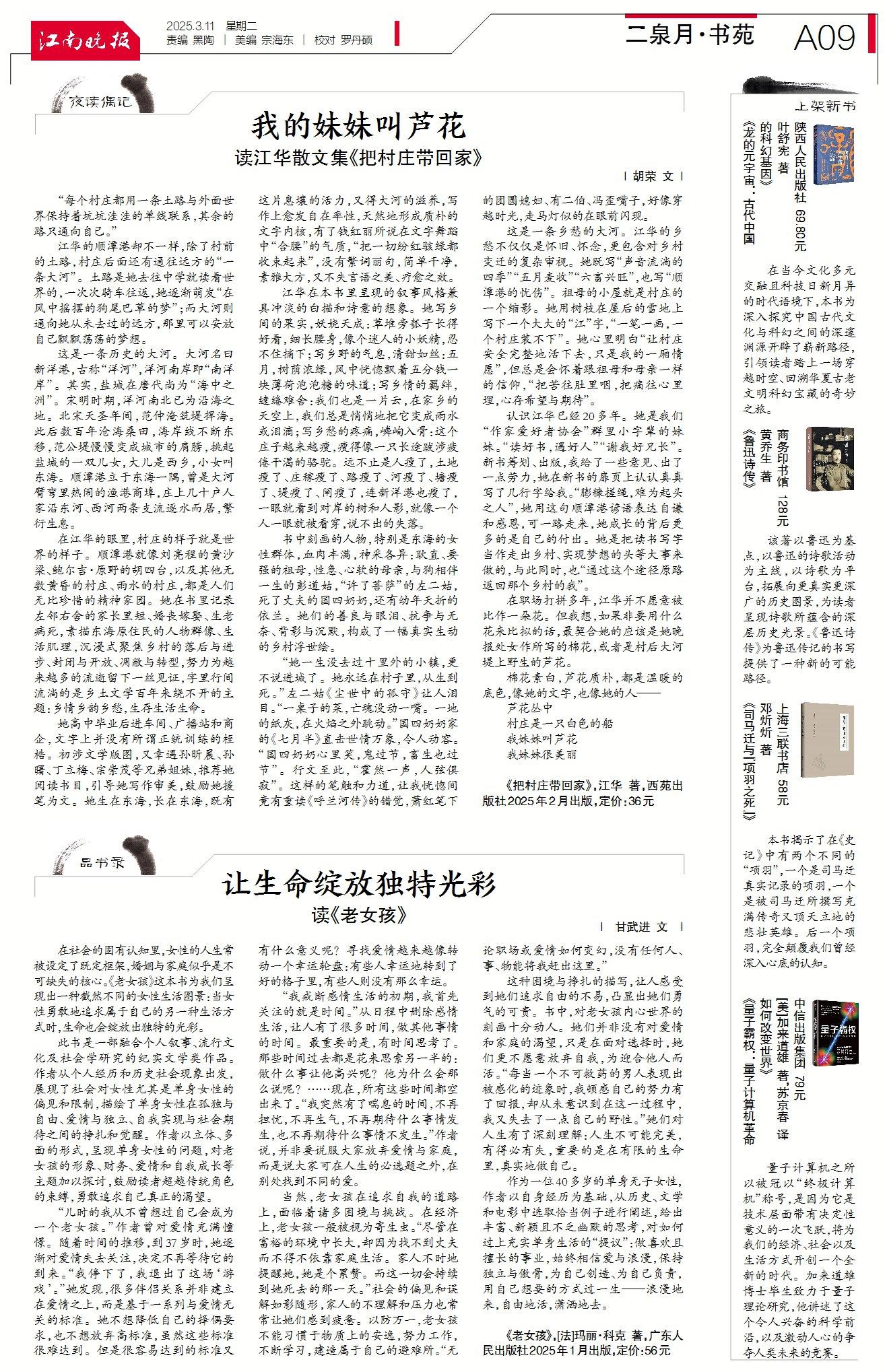| 胡荣 文 |
“每个村庄都用一条土路与外面世界保持着坑坑洼洼的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自己。”
江华的顺潭港却不一样,除了村前的土路,村庄后面还有通往远方的“一条大河”。土路是她去往中学就读看世界的,一次次骑车往返,她逐渐萌发“在风中摇摆的狗尾巴草的梦”;而大河则通向她从未去过的远方,那里可以安放自己飘飘荡荡的梦想。
这是一条历史的大河。大河名曰新洋港,古称“洋河”,洋河南岸即“南洋岸”。其实,盐城在唐代尚为“海中之洲”。宋明时期,洋河南北已为沿海之地。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筑堤捍海。此后数百年沧海桑田,海岸线不断东移,范公堤慢慢变成城市的肩膀,挑起盐城的一双儿女,大儿是西乡,小女叫东海。顺潭港立于东海一隅,曾是大河臂弯里热闹的渔港商埠,庄上几十户人家沿东河、西河两条支流逐水而居,繁衍生息。
在江华的眼里,村庄的样子就是世界的样子。顺潭港就像刘亮程的黄沙梁、鲍尔吉·原野的胡四台,以及其他无数黄昏的村庄、雨水的村庄,都是人们无比珍惜的精神家园。她在书里记录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素描东海原住民的人物群像、生活肌理,沉浸式聚焦乡村的落后与进步、封闭与开放、凋敝与转型,努力为越来越多的流逝留下一丝见证,字里行间流淌的是乡土文学百年来绕不开的主题:乡情乡韵乡愁,生存生活生命。
她高中毕业后进车间、广播站和商企,文字上并没有所谓正统训练的桎梏。初涉文学版图,又幸遇孙昕晨、孙曙、丁立梅、宗崇茂等兄弟姐妹,推荐她阅读书目,引导她写作审美,鼓励她援笔为文。她生在东海,长在东海,既有这片息壤的活力,又得大河的滋养,写作上愈发自在率性,天然地形成质朴的文字内核,有了钱红丽所说在文字舞蹈中“合腰”的气质,“把一切纷红骇绿都收束起来”,没有繁词丽句,简单干净,素雅大方,又不失言语之美、疗愈之效。
江华在本书里呈现的叙事风格兼具冲淡的白描和诗意的想象。她写乡间的果实,妖娆天成:草堆旁瓠子长得好看,细长腰身,像个迷人的小妖精,忍不住摘下;写乡野的气息,清甜如丝:五月,树荫浓绿,风中恍惚飘着五分钱一块薄荷泡泡糖的味道;写乡情的羁绊,缱绻难舍:我们也是一片云,在家乡的天空上,我们总是悄悄地把它变成雨水或泪滴;写乡愁的疼痛,嶙峋入骨:这个庄子越来越瘦,瘦得像一只长途跋涉疲倦干渴的骆驼。远不止是人瘦了,土地瘦了、庄稼瘦了、路瘦了、河瘦了、塘瘦了、堤瘦了、闸瘦了,连新洋港也瘦了,一眼就看到对岸的树和人影,就像一个人一眼就被看穿,说不出的失落。
书中刻画的人物,特别是东海的女性群体,血肉丰满,神采各异:耿直、要强的祖母,性急、心软的母亲,与狗相伴一生的彭道姑,“许了菩萨”的左二姑,死了丈夫的国四奶奶,还有幼年夭折的依兰。她们的善良与眼泪、抗争与无奈、背影与沉默,构成了一幅真实生动的乡村浮世绘。
“她一生没去过十里外的小镇,更不说进城了。她永远在村子里,从生到死。”左二姑《尘世中的孤守》让人泪目。“一桌子的菜,亡魂没动一嘴。一地的纸灰,在火焰之外跳动。”国四奶奶家的《七月半》直击世情万象,令人动容。“国四奶奶心里笑,鬼过节,畜生也过节”。行文至此,“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样的笔触和力道,让我恍惚间竟有重读《呼兰河传》的错觉,萧红笔下的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好像穿越时光,走马灯似的在眼前闪现。
这是一条乡愁的大河。江华的乡愁不仅仅是怀旧、怀念,更包含对乡村变迁的复杂审视。她既写“声音流淌的四季”“五月麦收”“六畜兴旺”,也写“顺潭港的忧伤”。祖母的小屋就是村庄的一个缩影。她用树枝在屋后的雪地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江”字,“一笔一画,一个村庄装不下”。她心里明白“让村庄安全完整地活下去,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总是会怀着跟祖母和母亲一样的信仰,“把苦往肚里咽,把痛往心里埋,心存希望与期待”。
认识江华已经20多年。她是我们“作家爱好者协会”群里小字辈的妹妹。“读好书,遇好人”“谢我好兄长”。新书筹划、出版,我给了一些意见、出了一点劳力,她在新书的扉页上认认真真写了几行字给我。“膨糠搓绳,难为起头之人”,她用这句顺潭港谚语表达自谦和感恩,可一路走来,她成长的背后更多的是自己的付出。她是把读书写字当作走出乡村、实现梦想的头等大事来做的,与此同时,也“通过这个途径原路返回那个乡村的我”。
在职场打拼多年,江华并不愿意被比作一朵花。但我想,如果非要用什么花来比拟的话,最契合她的应该是她晚报处女作所写的棉花,或者是村后大河堤上野生的芦花。
棉花素白,芦花质朴,都是温暖的底色,像她的文字,也像她的人——
芦花丛中
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
我妹妹叫芦花
我妹妹很美丽
《把村庄带回家》,江华 著,西苑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定价: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