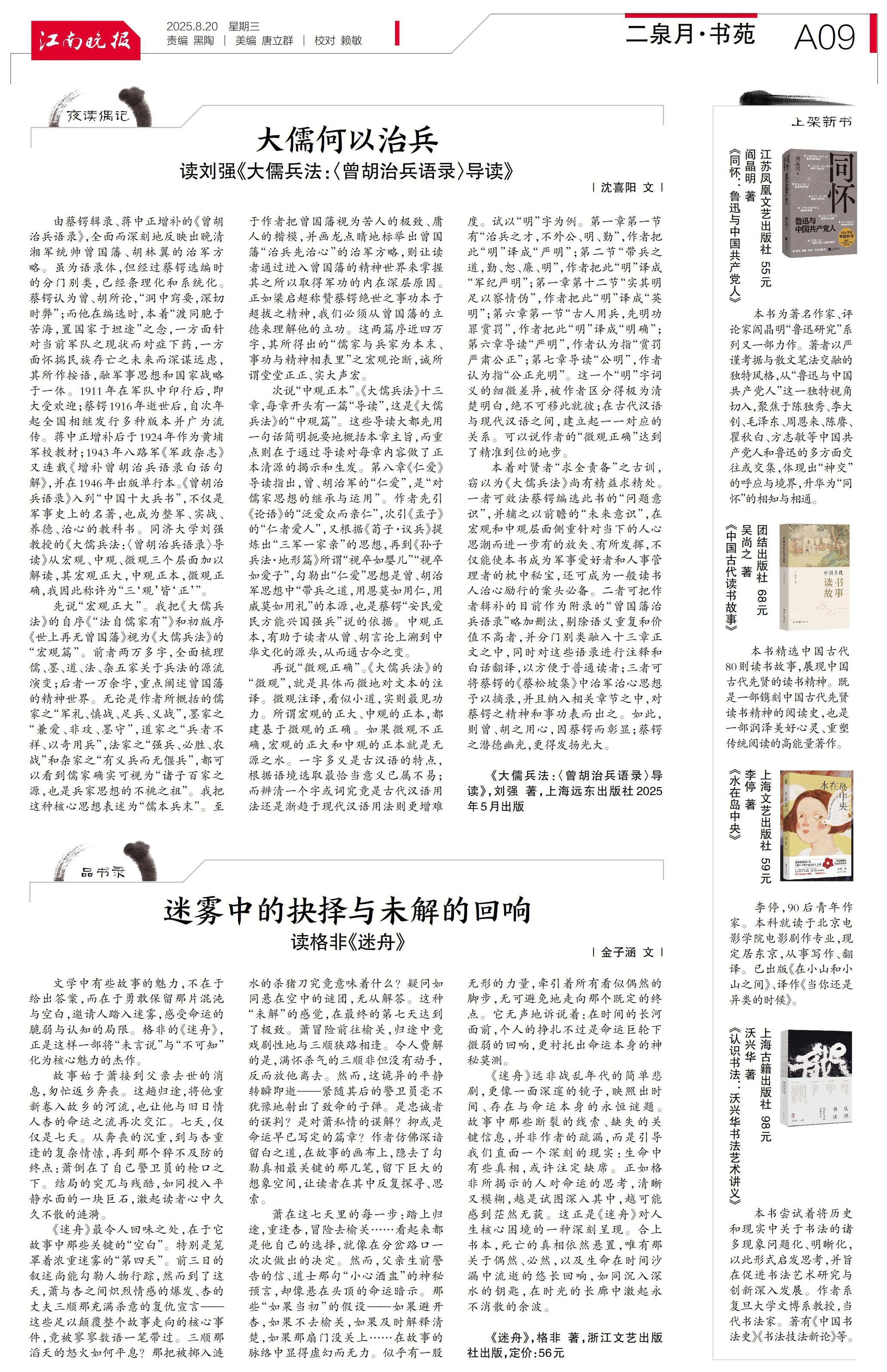| 沈喜阳 文 |
由蔡锷辑录、蒋中正增补的《曾胡治兵语录》,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晚清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方略。虽为语录体,但经过蔡锷选编时的分门别类,已经条理化和系统化。蔡锷认为曾、胡所论,“洞中窍要,深切时弊”;而他在编选时,本着“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之念,一方面针对当前军队之现状而对症下药,一方面怀揣民族存亡之未来而深谋远虑,其所作按语,融军事思想和国家战略于一体。1911年在军队中印行后,即大受欢迎;蔡锷1916年逝世后,自次年起全国相继发行多种版本并广为流传。蒋中正增补后于1924年作为黄埔军校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又连载《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并在1946年出版单行本。《曾胡治兵语录》入列“中国十大兵书”,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名著,也成为整军、实战、养德、治心的教科书。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导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加以解读,其宏观正大,中观正本,微观正确,我因此称许为“三‘观’皆‘正’”。
先说“宏观正大”。我把《大儒兵法》的自序《“法自儒家有”》和初版序《世上再无曾国藩》视为《大儒兵法》的“宏观篇”。前者两万多字,全面梳理儒、墨、道、法、杂五家关于兵法的源流演变;后者一万余字,重点阐述曾国藩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作者所概括的儒家之“军礼、慎战、足兵、义战”,墨家之“兼爱、非攻、墨守”,道家之“兵者不祥、以奇用兵”,法家之“强兵、必胜、农战”和杂家之“有义兵而无偃兵”,都可以看到儒家确实可视为“诸子百家之源,也是兵家思想的不祧之祖”。我把这种核心思想表述为“儒本兵末”。至于作者把曾国藩视为苦人的极致、庸人的楷模,并画龙点睛地标举出曾国藩“治兵先治心”的治军方略,则让读者通过进入曾国藩的精神世界来掌握其之所以取得军功的内在深层原因。正如梁启超称赞蔡锷绝世之事功本于超拔之精神,我们必须从曾国藩的立德来理解他的立功。这两篇序近四万字,其所得出的“儒家与兵家为本末、事功与精神相表里”之宏观论断,诚所谓堂堂正正、实大声宏。
次说“中观正本”。《大儒兵法》十三章,每章开头有一篇“导读”,这是《大儒兵法》的“中观篇”。这些导读大都先用一句话简明扼要地概括本章主旨,而重点则在于通过导读对每章内容做了正本清源的揭示和生发。第八章《仁爱》导读指出,曾、胡治军的“仁爱”,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运用”。作者先引《论语》的“泛爱众而亲仁”,次引《孟子》的“仁者爱人”,又根据《荀子·议兵》提炼出“三军一家亲”的思想,再到《孙子兵法·地形篇》所谓“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勾勒出“仁爱”思想是曾、胡治军思想中“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的本源,也是蔡锷“安民爱民方能兴国强兵”说的依据。中观正本,有助于读者从曾、胡言论上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从而通古今之变。
再说“微观正确”。《大儒兵法》的“微观”,就是具体而微地对文本的注译。微观注译,看似小道,实则最见功力。所谓宏观的正大、中观的正本,都建基于微观的正确。如果微观不正确,宏观的正大和中观的正本就是无源之水。一字多义是古汉语的特点,根据语境选取最恰当意义已属不易;而辨清一个字或词究竟是古代汉语用法还是渐趋于现代汉语用法则更增难度。试以“明”字为例。第一章第一节有“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作者把此“明”译成“严明”;第二节“带兵之道,勤、恕、廉、明”,作者把此“明”译成“军纪严明”;第一章第十二节“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作者把此“明”译成“英明”;第六章第一节“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作者把此“明”译成“明确”;第六章导读“严明”,作者认为指“赏罚严肃公正”;第七章导读“公明”,作者认为指“公正光明”。这一个“明”字词义的细微差异,被作者区分得极为清楚明白,绝不可移此就彼;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说作者的“微观正确”达到了精准到位的地步。
本着对贤者“求全责备”之古训,窃以为《大儒兵法》尚有精益求精处。一者可效法蔡锷编选此书的“问题意识”,并辅之以前瞻的“未来意识”,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侧重针对当下的人心思潮而进一步有的放矢、有所发挥,不仅能使本书成为军事爱好者和人事管理者的枕中秘宝,还可成为一般读书人治心励行的案头必备。二者可把作者辑补的目前作为附录的“曾国藩治兵语录”略加删汰,剔除语义重复和价值不高者,并分门别类融入十三章正文之中,同时对这些语录进行注释和白话翻译,以方便于普通读者;三者可将蔡锷的《蔡松坡集》中治军治心思想予以摘录,并且纳入相关章节之中,对蔡锷之精神和事功表而出之。如此,则曾、胡之用心,因蔡锷而彰显;蔡锷之潜德幽光,更得发扬光大。
《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导读》,刘强 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