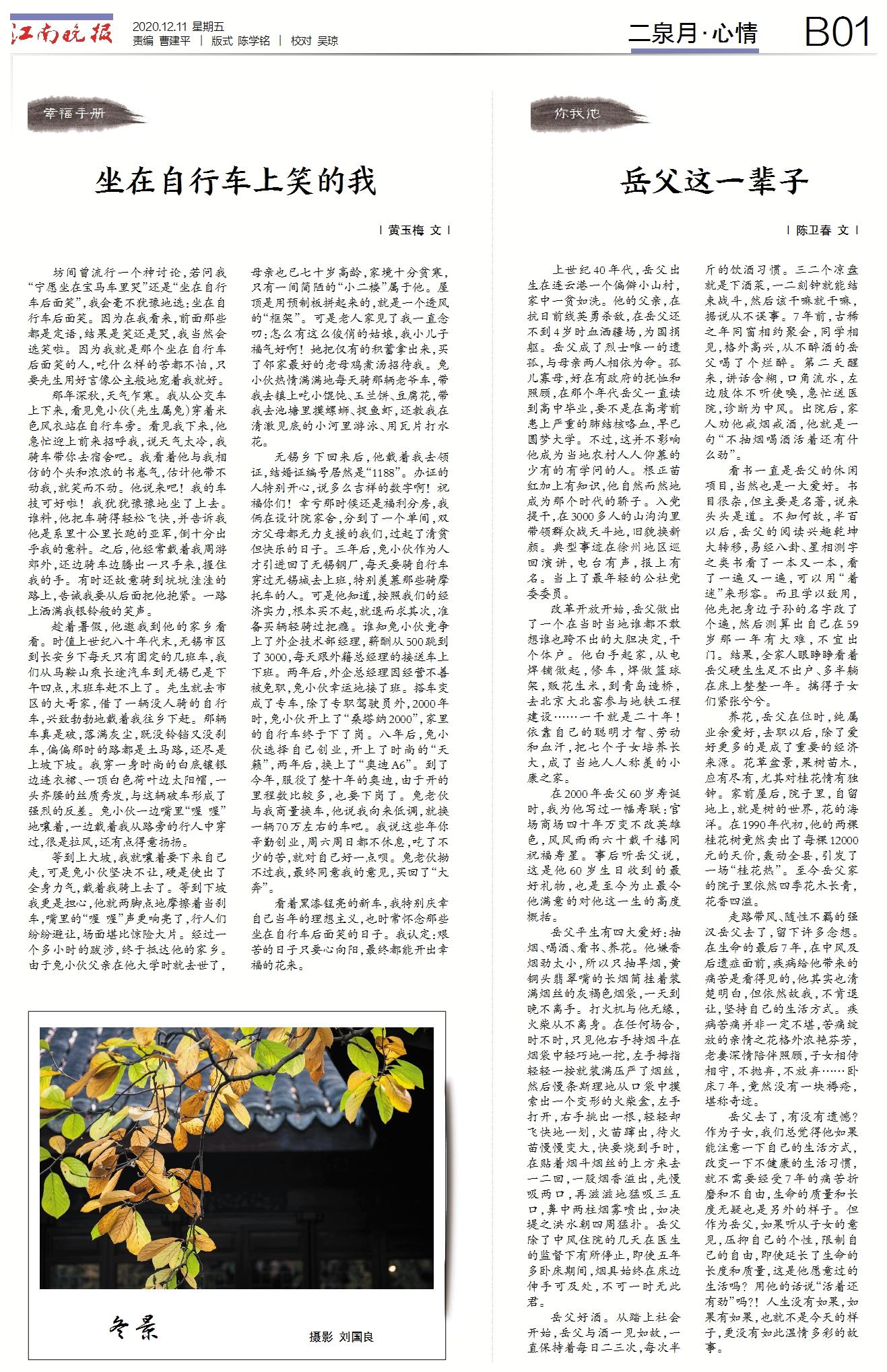| 陈卫春 文 |
上世纪40年代,岳父出生在连云港一个偏僻小山村,家中一贫如洗。他的父亲,在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在岳父还不到4岁时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岳父成了烈士唯一的遗孤,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好在有政府的抚恤和照顾,在那个年代岳父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要不是在高考前患上严重的肺结核咯血,早已圆梦大学。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当地农村人人仰慕的少有的有学问的人。根正苗红加上有知识,他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子。入党提干,在3000多人的山沟沟里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旧貌换新颜。典型事迹在徐州地区巡回演讲,电台有声,报上有名。当上了最年轻的公社党委委员。
改革开放开始,岳父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当地谁都不敢想谁也跨不出的大胆决定,干个体户。他白手起家,从电焊铺做起,修车,焊做篮球架,贩花生米,到青岛造桥,去北京大北窑参与地铁工程建设……一干就是二十年!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劳动和血汗,把七个子女培养长大,成了当地人人称羡的小康之家。
在2000年岳父60岁寿诞时,我为他写过一幅寿联:官场商场四十年万变不改英雄色,风风雨雨六十载千禧同祝福寿星。事后听岳父说,这是他60岁生日收到的最好礼物,也是至今为止最令他满意的对他这一生的高度概括。
岳父平生有四大爱好:抽烟、喝酒、看书、养花。他嫌香烟劲太小,所以只抽旱烟,黄铜头翡翠嘴的长烟筒挂着装满烟丝的灰褐色烟袋,一天到晚不离手。打火机与他无缘,火柴从不离身。在任何场合,时不时,只见他右手持烟斗在烟袋中轻巧地一挖,左手拇指轻轻一按就装满压严了烟丝,然后慢条斯理地从口袋中摸索出一个变形的火柴盒,左手打开,右手挑出一根,轻轻却飞快地一划,火苗蹿出,待火苗慢慢变大,快要烧到手时,在贴着烟斗烟丝的上方来去一二回,一股烟香溢出,先慢吸两口,再滋滋地猛吸三五口,鼻中两柱烟雾喷出,如决堤之洪水朝四周猛扑。岳父除了中风住院的几天在医生的监督下有所停止,即使五年多卧床期间,烟具始终在床边伸手可及处,不可一时无此君。
岳父好酒。从踏上社会开始,岳父与酒一见如故,一直保持着每日二三次,每次半斤的饮酒习惯。三二个凉盘就是下酒菜,一二刻钟就能结束战斗,然后该干嘛就干嘛,据说从不误事。7年前,古稀之年同窗相约聚会,同学相见,格外高兴,从不醉酒的岳父喝了个烂醉。第二天醒来,讲话含糊,口角流水,左边肢体不听使唤,急忙送医院,诊断为中风。出院后,家人劝他戒烟戒酒,他就是一句“不抽烟喝酒活着还有什么劲”。
看书一直是岳父的休闲项目,当然也是一大爱好。书目很杂,但主要是名著,说来头头是道。不知何故,半百以后,岳父的阅读兴趣乾坤大转移,易经八卦、星相测字之类书看了一本又一本,看了一遍又一遍,可以用“着迷”来形容。而且学以致用,他先把身边子孙的名字改了个遍,然后测算出自己在59岁那一年有大难,不宜出门。结果,全家人眼睁睁看着岳父硬生生足不出户、多半躺在床上整整一年。搞得子女们紧张兮兮。
养花,岳父在位时,纯属业余爱好,去职以后,除了爱好更多的是成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花草盆景,果树苗木,应有尽有,尤其对桂花情有独钟。家前屋后,院子里,自留地上,就是树的世界,花的海洋。在1990年代初,他的两棵桂花树竟然卖出了每棵12000元的天价,轰动全县,引发了一场“桂花热”。至今岳父家的院子里依然四季花木长青,花香四溢。
走路带风、随性不羁的强汉岳父去了,留下许多念想。在生命的最后7年,在中风及后遗症面前,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是看得见的,他其实也清楚明白,但依然故我,不肯退让,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疾病苦痛并非一定不堪,苦痛绽放的亲情之花格外浓艳芬芳,老妻深情陪伴照顾,子女相侍相守,不抛弃,不放弃……卧床7年,竟然没有一块褥疮,堪称奇迹。
岳父去了,有没有遗憾?作为子女,我们总觉得他如果能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下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就不需要经受7年的痛苦折磨和不自由,生命的质量和长度无疑也是另外的样子。但作为岳父,如果听从子女的意见,压抑自己的个性,限制自己的自由,即使延长了生命的长度和质量,这是他愿意过的生活吗?用他的话说“活着还有劲”吗?!人生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更没有如此温情多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