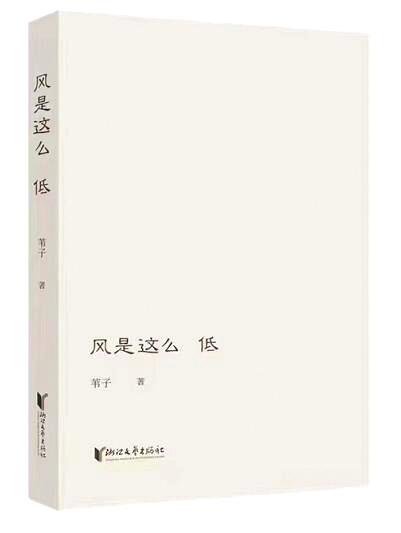| 苇子 文 |
诗的“在”是“远在”,它不是眼前,不是“近在”,也不仅仅是庸俗的浅薄诗意的远方,而是那种在身边的“远”,居于内心的“远”。以及处于另一个非地理空间的“远”。它因此拒斥当下与眼前,更拒斥熙熙攘攘来来往往,拒斥圈子与近朋,哪怕好友。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诗是孤独的“在”,此亦为一种“远”。我宁愿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也不愿在众多的废话之中存在所谓的诗。
一个诗人应该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当更多的诗人重视在场的时候,我们恰恰要退到诗坛以外。一些人其实是把“场”弄错了,它不应与圈子画等号,更不该是整天飞来飞去参加各种活动,到处发声。这个“场”其实是诗的气场,在与不在是一个人与诗歌本身达成的契约,而不是与其他人达成的契约。我们在场,就是从未离开过诗歌本质,在各种诗潮中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存在,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随声附和。我们冷静地处理我们与诗歌发生的关系,那是一种身在其中与之融为一体的愉悦。我们可能从不参加任何诗会、活动,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结交诗歌权贵、广发作品,而是静下心来感悟诗歌的静水深流,每一次真正的交流,也必将是回归到核心时的心领神会。
诗于我,早早地成为了一种心灵方式,它的重量感、建筑感,从质到形,内在地塑造着我,一如故乡的永安溪,从童年到成年一直贯穿着我的生命,有时会使我不再孤独,有时会愈加孤独,但这是大孤独,有了诗之后的向高处而升起的孤独。我着迷于这种孤独。这是真正的诗之远。
当初夏来临,万物欣欣向荣,而我却越发孤独,我被自己抛往心灵的远方,我在那里发现未明的诗,未明的事物,未明的自我……
《风是这么低》,苇子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定价:38元